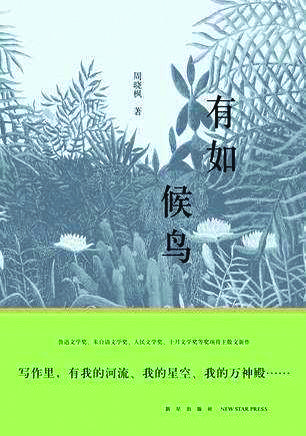“如果想要读懂周晓枫,你似乎得先读一些有关哲学的书籍。”2020年1月30日的清晨,我打开了周晓枫的《有如候鸟》,看了一会,我在扉页写下这行字。她是如此地热爱着写作,以至于她觉得“天堂的大门长得最像作协办公楼”。另一句,深得我心,她说:“由于不勤奋,我一直没有磨损对创作的热爱。”
多么有趣而勇敢的一句话,“由于不勤奋”,“不勤奋”的后面,往往刻印着作者大量地阅读和对生命、生活的各种体验。“因为散文写作的耗材大,拿缓生的树当速燃的柴,烧不了多久,黑暗和寒冷就来了。”在我理解,散文不同于虚构文体,写一篇少一篇。散文需要更多的情感反应和体验,注定了这种“易耗品”式的特质。当然,散文持续写下去的可能,是逃离仅以情感为依托的创作,而进入多角度地书写,譬如于坚,譬如余秋雨,譬如李娟。
在周晓枫的散文里,我们看不到一派春光灿烂的“颂歌”,有的是对人性小心翼翼地鞭笞和直面灵魂深处的诘问。同时,她践行了她对散文的想法,即“可以用叙事的牙把整个故事嚼碎了吃进肚子里”。所以在《有如候鸟》里,我看到了譬如《布偶猫》《离歌》这样散发小说气质的章节。这给了我足够的理由相信,如果周晓枫哪天心意一动,改写小说,必定是高手。
尤其是《离歌》,周晓枫以极其冷静的笔调和叙述角度的多变,从心理学、社会学各方面进行几乎无死角的探究,有着外科手术般的镇定,从一个“朋友”的死亡开始,从事件到逻辑分析,丝丝入扣;像一个有经验的刑警,层层剥开时光的迷雾,由一个平常的猝死事件开始,将一个男人和他的家庭呈现得纤毫毕现。一个尖酸刻薄、势利的市井小女子,一个文艺、清高的男人,是如何画上的等号,并且,甚至拥有了一种似乎生死不渝的质感?周晓枫带着我们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在《布偶猫》中,她给我们描绘了一对年轻情侣,在他们之间,充斥的是暴力和血腥。可是被送往医院抢救的女主却还偷偷给男朋友发信息,嘱他躲好,免得被警方找到。张爱玲也曾经写过,男人在大街上打老婆,旁人看不过去阻止,女人反倒骂起旁人的多管闲事,并且对男人说别打了别打了,回家去给你打。周晓枫层剥缕析,见骨见血见病灶,不留情面,只依稀听见她内心传来的叹息。
在《禽兽》里,我惊讶于周晓枫对动物的熟稔,承此书所惠,我也知道了很多让我瞠目结舌、目瞪口呆的知识。严格来说,周晓枫写了不少关于“杀戮”和“死亡”的事件,在我的阅读经历里,关于这方面的描写功力,莫言似乎最为“拔尖”。但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就在于两者书写同一件事时,屏幕后的那张面孔,表情是不一样的。看着莫言活色生香充满动词的表述,我几乎可以感受他那一刻的亢奋,如果不是键盘或者纸笔困住了他的手,或许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周晓枫,仍然是那个冷静得近乎残忍的、老练的外科手术大夫。
关于善恶,周晓枫的论断绝妙:
“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从来不是两个被封存的固体名词。它们有时就像比重相似的液体,交融得密不可分,人类的智慧尚不能够提炼两者,并使之保持在各自的纯度里——我们终生需要警惕其中的化学配方,却又被迫饮鸩止渴。”
周晓枫遣词用句的精准,通篇随处可见的珠玑字句,便几乎成了一篇摘抄手记。读完此书,对周晓枫充满尊敬。她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