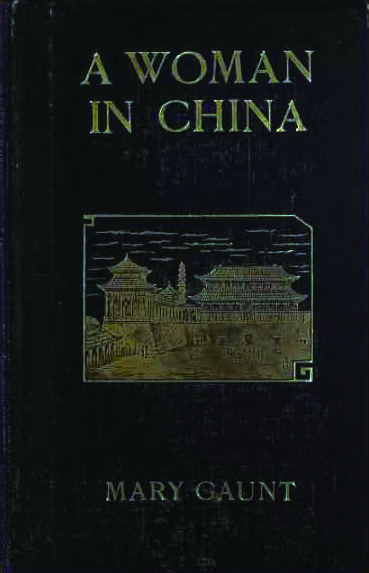
1798年,乔治·斯丹顿爵士记录了第一任英国驻华大使在华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他写道:“几年前,广东出了一件大事,差点儿中断了我们对中国的贸易。凡是有这种倾向的恶行,都应当引起忧虑,加以防范,特别是对于商业国家。有一天,英国印度殖民地和广东之间的海面上行驶着几条船——不是东印度公司雇用的。其中一艘船上的船员拿枪玩儿,结果打死附近一条小船上的两个中国人。谋杀罪在中国永远不会被原谅。两广总督义愤填膺,认为这是刻意为之的暴行,要求严惩凶手,追查下令行凶的长官。英方抗议,说这件事纯属偶然,但总督坚称他们是出于恶意,坚持一查到底,为了达到目的,还扣押了一位重要的管理人员。其他国家受到惊吓,为了共同的目标,与英国人联合起来,抵制总督。总督不肯善罢甘休,沿河岸部署了军队,迫使英方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最后,为了顾全大局,作为权宜之计,只好交出开枪的那个人,明知道,生还的希望不大。” 后来,他在文章的注解里写道,人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个被迫交出去的倒霉的家伙不久就被中国人处死。但愿,当时所谓权宜之计,不只是为了救被扣押的那位重要的管理人员。 在我看来,这件事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北京会有个使馆区。当然使馆区以今天的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应该归因于义和团运动。但是它的萌芽应该追溯到当年不得不牺牲那个因为粗心大意而打死中国人的枪手的“权宜之计”。一百二十年前,西方国家刚走出野蛮,其文明程度中国人在两三千年前即已达到。但西方人前进的脚步不曾停歇,他们觉得如果继续和这个富庶的国家做生意,同时保护自己的臣民和货物不受损失,就必须团结一致。他们也确实团结在了一起。外国人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建立了一种奇妙的“外交关系”。而这种已经延续了许多年的关系,在别的国家却从未有过。北京的使馆区就是这种关系的结晶和具体表现。 假设在伦敦,地球上所有大国都在这里拥有一块土地,从大理石拱门到海德公园角,从公园巷到邦德街,不但占领,还重兵把守,制定种种条令,禁止当地居民靠近,那简直不可想象。但这正是北京发生的事情!从鞑靼城城墙,到前门,哈德门,这些国家占据了一块面积为一平方英里、呈平行四边形的土地。这块土地他们不但日夜守卫,而且占领了使馆区三面广阔的“缓冲地带”。这些地方任何人不得建造房屋,只能由他们在那里驻军。这支“多国部队”即使占领不了整个北京城,但也起到某种威慑作用。 没有人知道这里有多少日本人,但假如和其他国家一样,至少有二千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在使馆区耀武扬威。住在那儿就像住在兵营里。出出进进,堡垒和炮台是你的必经之地。门前的大街上,你会遇到弹药车、行李车、红十字会的车。每一个路口都有士兵把守:欧洲列强的士兵,美国的士兵,日本的士兵。他们在各自使馆前站岗,操练,一天到晚都在练习步伐、射击。英国公使馆的一个角落保留着一截1900年留下的断壁残垣,上面写着几个大字:“不要忘记”。提醒人们——如果这些国家需要提醒的话——不要忘记1900年可怕的日子,不要忘记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随时都可能再次爆发排外的运动。 我本来想说,这几乎是对中国人的侮辱。可是,现在我要说,这就是一种侮辱!事实上,这个武装到牙齿的使馆区一定是残酷折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的心头之痛。他们一定渴望驱除这些来自西方的狂傲的洋人和来自东方的邻居。在自己城市的中心被外国人辖制那是何等的耻辱!就连长城,忽必烈第一次建造、明朝征服者完成的伟大的长城,从哈德门到前门这一段也在外国人的统治之下。尽管哈德门的城楼仍在中国人手中,但像中国许多惨遭炮火损坏的建筑一样,它也尚未修复。廊柱上的红漆早已开裂,金黄色的图案褪尽华彩,屋顶琉璃瓦的缝隙中杂草丛生,冬天枯黄,夏天暗绿,尽管还由中国士兵守望,但满目荒凉,威严不再,一切都是久远的过去。一百码左右,是德国人的岗亭。一天二十四小时,总有全副武装的士兵守卫在那里,荷枪实弹的哨兵走来走去,头盔上的鹰冷冷地注视着东方古老的都市。其实,他们不太需要守卫哈德门。这座古老的城门早已在他们的枪炮控制之下。城楼下面,法国人小心翼翼地守卫着使馆区东侧的防御工事。那道围墙中部被日本人占据,他们在那里又增设了一道铁栅栏。听说,这道铁栅栏叫“护墙”。“护墙”里面还有一扇门。走过通向那扇门的小路,有堵一人高的砖墙,“九曲十八弯”,要想进去,没那么容易。夏天,绿草如茵,大门和铁栅栏上爬满了牵牛花。日本人不像高效的德国人或精明的美国人那么张扬,但听说他们非常热心,如果其他国家允许的话,巴不得去把守整堵围墙。在前门,一英里长的围墙西端是美国人的天下。他们身材高大、瘦削、聪明、能干,穿着卡其布衣服,头上的帽子翻着边儿,脸刮得干干净净,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英语仿佛是另外一种语言。 ——李尧译《中国游记》(节选)(第四章 北京使馆区 选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