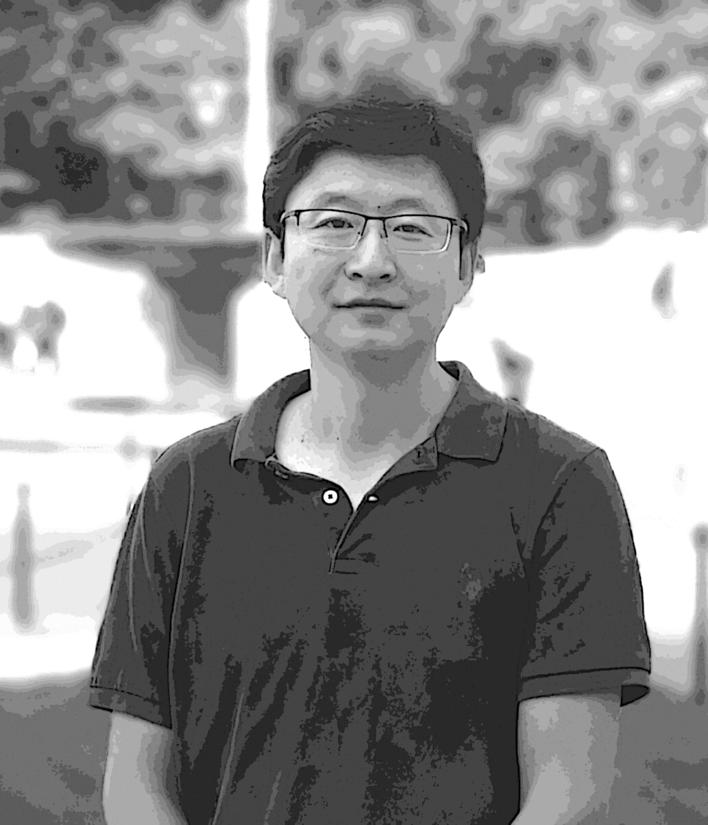当人们仍然在传统文学框架内以娱乐、猎奇、质疑、批判和否定的心态面对人工智能写作时,人工智能写作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常态,从1805年瑞士工程师梅拉德特研制出能够写诗、绘画、编曲的智能机器至今,在虚构和非虚构写作领域已经涌现出众多智能写作机器,并以强劲的态势介入到传统文学写作,对文学写作主体、写作方式、叙述策略、语言修辞、传播渠道、接受机制、消费心理等多个层面产生剧烈冲击。尤其是,智能机器“微软小冰”接连推出《阳光失去了玻璃窗》《花是绿水的沉默》两部诗集,以及智能机器“小封”的诗歌写作实践所引发的轰动效应,更是将人工智能写作置于舆情中心。在这种历史情境和时代趋势下,以文学的异化、作者的消失、文学经典的终结、文学的工具性退化、文学审美的裂变、文学人文精神的衰落为支撑点和内驱力,不断排挤、打压人工智能写作空间和地位,显得有些激进和偏颇。认知人工智能写作的正确方式不是将人与智能机器、人的文学与智能机器的文学置于事物的两极,而是找出关于人工智能写作的内部细节和过程及其现实效用。因此,我们应该将关注焦点聚集在人工智能写作本体,以学理方式去分析几个关键问题及其内在逻辑:人工智能写作是否具有主体性;如果具有主体性,意识、意愿、情感、心灵等主体性内在要素能否通过“计算”的方式实现;如果可以实现,能否通过对已有文学数据的模仿和再造表述内在的主体性;在认同人工智能写作主体性基础上,人工智能文学存在哪些限度?
一
人工智能写作论争的核心是智能写作机器及其文学实践是否具有主体性,或者说,智能写作机器具有自我主体建构能力是人工智能写作成立的必备前提条件,“智能计算机自主体既是人工智能的最初目标,也是人工智能的最终目标。”一般意义上,人工智能写作机器主体性确立标准是以人的主体性特征为参照,而人的主体性基本特征在于人的外在社会实践和内在自我反思,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确证。具体而言,人在自我意愿的驱动下,通过实践活动使自我与外在世界发生关联,在此过程中对自我与外在世界关系进行调整,并根据外在世界的新变化重建自我意愿和行为,自主性、映射性、意向性、能动性、持续性、反思性等要素构成了人的主体性的多重维度。在此逻辑推演下,文学的主体性在于写作者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文学叙述表征自我主体诉求,在对外在世界的审美建构中重塑自我主体意识,以此实现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以及人的主体能动性。也就是说,文学的主体性存在两个重要基点:“身体实践”,以文学写作介入和塑造现实世界;“精神实践”在“身体实践”反馈的信息中重构自我主体。那么,只要人工智能写作机器能够实现这两个重要基点,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写作具有了主体性。或者说,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赋予人工智能写作机器“身体实践”和“精神实践”的路径和能力,那么人工智能写作的主体性问题将不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符号主义代表人物约翰·麦卡锡、纽厄尔和西蒙提出“物理符号系统假说”理论,认为外在世界可以用系列物理实体符号表述。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就是符号,符号就是世界。“物理符号系统假说”为人工智能写作机器的“身体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符号作为智能写作机器认知现实世界的基元,智能写作机器通过对符号的操控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因为符号可以指称现实世界中的任何物理实体和任何表达方式,如果符号与指称对象和表达式之间的关系被确定下来,符号就具有“稳定性和强制性”。因此,智能写作机器对现实世界的表述就转化为符号表述、符号逻辑延展和符号应用的过程。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研究团队开发的智能写作机器Shelley AI以英国作家玛丽·雪莱的恐怖小说《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和从社交网站Reddit上整理的恐怖故事蓝本,创作了同名恐怖小说《弗兰肯斯坦》和《镜子》。从表象上看,小说只是对现有文学数据的简单重组,但实际上是从文学数据背后发现关于恐怖的知识,然后将相关知识信息转化为对应的符号,再根据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对符号进行调整、修正和再造,最终形成新的文本。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写作描述外在世界的过程呈现为“数据——知识——符号”的表示和推理过程。同样,1977年美国数学家米翰开发的智能写作程序“Tale-Spin”,1990年美国科学家特纳研发的智能写作程序“吟游诗人”,2000年美国科学家林斯约德与费鲁齐设计了智能写故事软件“Brutus”和2007年俄罗斯科学家和语言学家联合开发智能写作程序“Pcwrite2008”都是建立在对知识的处理基础上。
二
根据“物理符号系统假说”理论,智能写作机器可以实现“身体实践”,在呈现外在物理实体上有着相对完善的实践策略和技术路径。但人的主体性除了“身体实践”,还包括“精神实践”,或者说,智能写作机器是否拥有信念、愿望、情感、意图、心灵等精神性要素,以及自我反思和自我重塑能力,成为判定人工智能写作主体性不可或缺的标准。20世纪末期,以深度神经网络和联想神经网络为基础的联结主义,为智能机器实现主体性提供了可能性。联结主义认为神经元是智能的基本元素,人对外在世界的认知过程是各种神经信息和神经系统并行分布处理的过程,并呈现为一种整体性。在理论上而言,只要为智能写作机器输入神经元模型和神经计算算法就可以模拟人的精神活动。在时间上,从20世纪40年代麦克洛克、皮茨提出M-P神经网络模型开始,霍普菲尔德、鲁梅尔哈特、塞杰诺斯克、霍根、延森、斯莫伦斯基等人相继提出了离散和连续的Hopfield神经网络模型、多层神经网络的误差反向传播算法、NETtalk神经网络学习系统等多种神经网络模型和算法。例如,1988年Ortony,Clore和Collins在《情感的认知结构》中提出了情感认知评价模型“OCC”模型,模型总结了高兴、生气、愤怒、冷静、厌恶等22种人类情感的基本类型,这些情感的生成源于在不同语境中外界正面和负面信息对神经元的刺激,不同类型的情感呈现为相应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而这一过程遵循固定的规则,并可以通过计算的方式复现出来。同时,认知科学、信息科学、心理学、哲学、生物学等多种学科与人工神经网络的融合,以及图像识别、语言处理、目标识别等超导、光学技术在人工神经网络中的运用,使人工神经网络逐渐变得完善。这为智能写作机器“精神实践”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和技术支撑。
人工神经网络技术可以复现人的认知过程,那么,智能写作机器如何具有自我反思和重塑能力?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是使人工神经网络拥有自我学习的能力。联结主义认为,通过对人工神经网络连续权值做出调整,可以实现神经网络的自我学习能力,并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在神经网络中输入某种记忆模型,在相关外界信息的刺激下,记忆模型被激活,以此产生相关学习内容;二、在神经网络中输入某种规则编码,根据规则调整连续权值,从而使神经网络进入有序的学习状态,借此实现无监督学习和自主学习。据此,智能写作机器可以不断对已有经验进行重构,完成自我反思和重塑。例如,“微软小冰”出版的诗集《阳光失去了玻璃窗》是用“层次递归神经元模型”,通过对徐志摩、胡适、戴望舒等519位中国现代诗人的诗歌语言的学习而完成的,而这种语言学习不仅仅是对诗歌词汇、韵律、节奏等写作规则的学习,更是对诗歌语言蕴含的人的情感的学习和再造。
三
虽然人工智能写作在理论和技术上可以实现“身体实践”和“精神实践”,并在现实应用过程中确认人工智能写作的有效性,但人工智能写作仍然存在限度。从上述论述可以发现,人工智能写作与人工智能技术迭代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会导致文学创作的固态化、统一化和脸谱化,作品中的主题、人物、故事、情节、语言等个性化的文学创作演化为大规模的技术生产,因此形成文学创新思维的匮乏,人们不再执著于对文学审美要素的构思、体验、锤炼、打磨过程,不再追求文学的个性化、独特性、差异性和惟一性,长期以往文学将失去鲜活的生命力和存在的意义。同时,由于人工智能写作只发生在人——智能机器——数据之间,因此可以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精神诉求、时代发展导向等各种外在限制,个体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和要求来“创作”文学,可以肆意宣泄任何欲望和情绪,也可以毫无目的地将文学创作变成一场人与机器之间的语言游戏。这样就形成一种“异化”情境:文学写作从问题的解决过程演变为答案生成过程,人不需要思考任何解决文学创作及其过程中产生的任何问题,智能写作机器代替人来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人无法获取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产生的喜怒哀乐等情绪体验,也无法与文学产生精神共鸣,人与文学始终处于隔离状态,人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形成人在失去劳动机会和劳动价值之后的异化情境。加之,在人工智能写作过程中智能机器具有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身份:在文学生产环节智能机器对文学数据分析、筛选、重组过程同时也是已有文学作品阅读过程;在文学接受环节,智能机器可以依据文学批评标准数据对自己写作的文本进行阐释和解读,在两个环节中智能机器同时具有作者和读者双重身份。这样,传统意义上“作家”和“读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作家和读者完全处于失衡状态,但未来的文学和文学的未来本身就是在突破限度中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