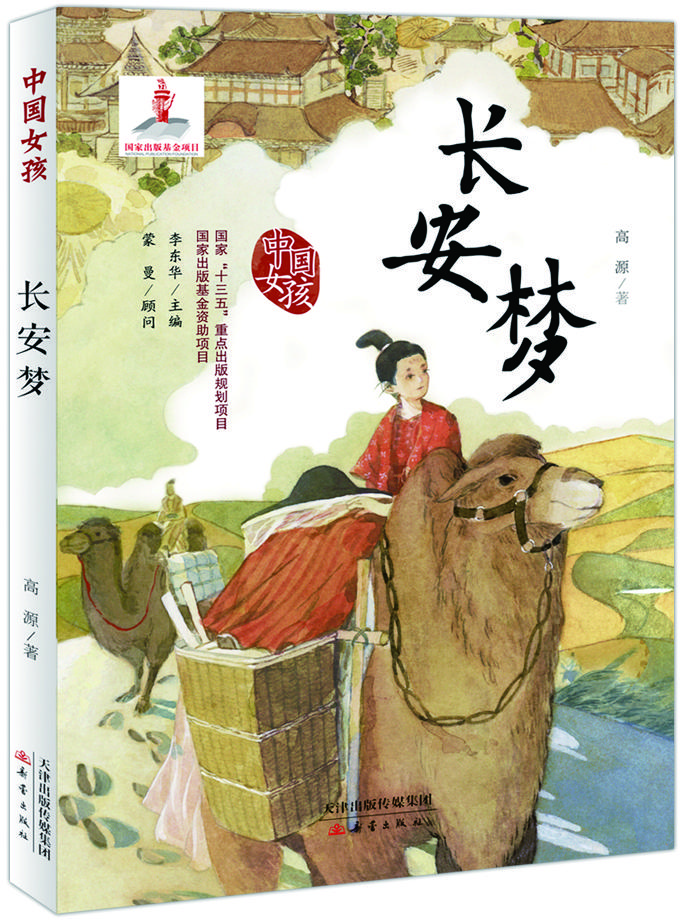在中外文学长廊中,长安是一个具有流动性和生产性的词语,它引诱着作家们一次次重返大唐文化的精神血脉。在那种自信、大度、包容、浪漫的时代精神里,作家们抚摸着大唐的文化肌理,沐浴着大唐文明的荣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长安梦》是高源对长安的一次文学想象,作者以一个名叫康斯贝儿的女孩的视角,讲述了“去长安”的艰辛之路,并再现了大唐的时代精神风貌。那么,这部儿童历史题材的小说,在历史叙事方面做出了哪些有效的尝试和突破呢?
不可否认的是,《长安梦》是一部极具历史感的儿童小说,不论是小说中人物之间的称呼方式,还是食物的命名和烹饪方法,抑或人物的服饰特点和语言风格,甚至地名以及器物的名称变化等,作者都能做到言之有据,在叙述中毫无违和感。“刺糖”“西市”“坐床”“花钿”“面靥”“素秋”等词散发出浓烈的唐代气息,它们紧紧依附在“长安”这一地理和精神场域中,为《长安梦》提供了叙述时空上的信服力。除此之外,大唐文明最著名的两张名片——李白和张旭,在《长安梦》里也得到了呈现。李白的酒与诗、张旭的草书,是大唐文化的杰出艺术瑰宝。在《长安梦》中,李白是作者倾注笔墨较多的人物形象,他与康斯贝儿相识于西州,又于37年后重逢于长安。种“刺糖”的经历成为二人相识并最终得以相认的记忆符号,这是一段颇具浪漫色彩的情感经历。在作者的笔下,二人的情感互动并没有落入言情小说的窠臼,反而平添了一丝纯真与执著。
在我看来,《长安梦》在叙事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类似纪年的形式,为小说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但可切换的小说时空。具体说来,作者选取了“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天宝三载(公元744年)”这4个年份作为叙述的重心,在处理方式上将“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置于“景云元年(公元710年)”之前,并在小说后半部分再述了“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天宝三载(公元744年)”两个年份发生的故事,打破了小说的线性叙事常规,增加了小说叙事节奏的跌宕起伏。这种处理方式在叙事线索上“兵分两路”,康斯贝儿去长安是一条成长线,康二娘在长安的生活是另一条线,两条线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因康二娘与李白的重新相认而汇合,进而在叙事上形成了闭合,小说的情节发展至此达到高潮。从叙事上来看,作者更多采用的是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写作技巧,重在叙事上的跳跃性。也就是说,《长安梦》呈现的故事形态虽然是古典的、中国式的,但在叙事形态上看,它更多汲取的是西方小说的叙事策略。
需要指出的是,《长安梦》在主题上也具有某种解构的意味。在小说中,长安是一处充满梦想的繁华富庶之地,人们穷其一生也要抵达长安:康斯贝儿费尽心思以偷换身份的方式,代替哥哥继芬去了长安;婴兰自幼向往大唐之繁华,甘愿去长安做舞伎;僧人们去长安为了传教;读书人去长安为了考取功名,谋个一官半职。长安像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吸附着小说中的人物。但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借康二娘和李白之口,道出了去长安后的心境:于康二娘而言,无非是“一个梦醒了,另一个梦又开始了”,奔赴长安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再度相遇,然后再度相忘于江湖;于李白而言,长安走了一遭,结交了挚友,看清了现实,也看清了自己。倘若说“去长安”是小说中人物克服千难万险奔赴长安的“内驱力”,那么“在长安”则是他们面对现实处境萌生离意的“外引力”。“在长安”消解了“去长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改了“长安”作为一种梦想存在的坚固性,这就是长安的宿命,也是芸芸众生难以规避的“围城心理”。
毫无疑问,《长安梦》在艺术上与它们是有所分野的,《长安梦》代表了一种重述历史的写作姿态:远离当下,回到相对遥远的时空,以一个孩童的视角重返历史的现场,表达古今人类相通的情感经验。《长安梦》这本书最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作者的叙事探索和重述历史的勇气,这无疑是一个有追求的小说家难得的艺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