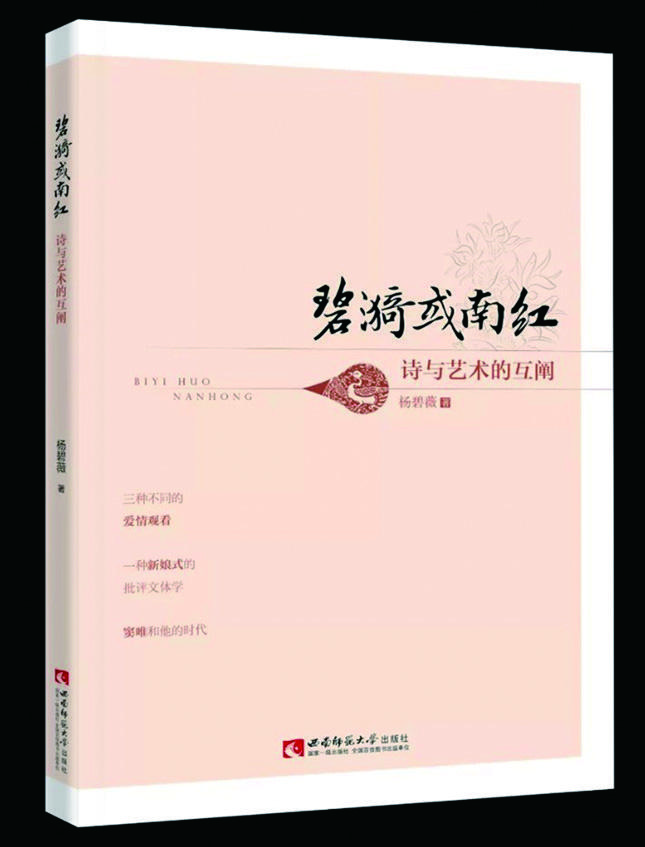苏珊·桑塔格也许并非学术思想大师,也并非伟大作家。但对这位美国女性,我却素有偏爱:她工小说,也论诗、论小说,谈摄影、说星座,点评各路文化大神却不将他们当作大神,几乎无所不谈,无所不能。在专家盛行的年月,她驰骋于各个领域;在崇尚解释学的时代,她反对阐释。中国人常说,文如其人,即使是透过翻译,我也能从汉语中读出谁是桑塔格。
杨碧薇似乎在以实际行动,向桑塔格遥致敬意:她写诗,做摇滚歌手,研究新诗,研究与诗有关的中外电影,写乐评,谈摄影和当代艺术,甚至有过做模特儿的体验。她认识得很清楚,她必须要朝向一种大文化观的批评而努力。所谓大文化观的批评活动,既指跨领域的批评行为,也指以诗学的基本精髓为原点,投射到其他批评领域。可以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唯有诗性才是一切形式的艺术的魂魄。杨碧薇的诗人身份和她研究诗学的科班经历,为她心目中的大文化观的批评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新近出版的《碧漪或南红》,是杨碧薇近几年除博士论文外一些谈诗、论艺的文字的结集。读她的文字,称得上是一种很舒心的体验:她因为诗人身份,文字漂亮,但从不大红大紫,更不屑于涂脂抹粉;也因为诗人身份,使她在面对具体的作品(比如诗、小说、乐曲、电影、甚至绘画和摄影)时,有艺术上的高度敏感,往往能在常人不经意的地方,迅速发现蛛丝马迹,经她剖析顿然生辉。比如她这样谈诗:“如果说诗歌的产生过程是一根手链,那么物感就是链条上的搭扣,链条的一端自这个搭扣而始,然后渐次拉长;拉到一定的时候,拉出去的另一端也须回到拉扣上,才能确保链条的完整性。”用诗人最常用的比喻方法,便将一个原本抽象的问题很形象地解决了,优雅、体面、但朴素和不动声色。这正是桑塔格擅长的方法:把事物呈现出来,但不解释事物;把问题说清楚,但仅止于说清楚,再多一点,便是僭越。
杨碧薇的文字有很多值得指出的特点,但疾速更愿意为这个短文所谈论。随手从她的文章中随便摘录一段(笔者确实做到了“随手”和“随便”),即可见出何为疾速:“时至今日,摄影与生活的亲密关系已不言而喻;这一关系的广泛性、深入性远远超过了其他艺术门类。一个人或许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阅读文学作品,不听音乐,也不看电影,但他无法脱离照片的包围。”行文的疾速不仅是一种文字风格(风格据说是一种心境的蜕变),更是判断的迅速、坚决,不给狐疑、游弋、犹豫留下空间,但也不独断、不急躁、不偏执、不极端;疾速就是直入问题或事物的核心,尽量不做外部纠缠,视节约为美德,类似于禅宗的“直指本心”。《碧漪或南红》中谈诗论艺的诸多文章可以表明:疾速在杨碧薇那里已经从思维方式,上升为生存方式。正是得益于这至关重要的一点,杨碧薇才有能力周旋于诗、电影、音乐等行当,既乐此不疲、一往情深,又不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将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重叠在一起,用汉语观察、写作、思考,暗含着一个基本的伦理:让生活丰满,让德行完善,让境界高迈,让宅心醇厚。“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伟大的汉语因高度赞美诚,直至将诚内化为汉语的本质;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须听命于诚,方不负这种语言的重托。《孟子》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动”可以解释为感动,但也可以结合《中庸》所谓“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而将“动”解释为行动。果如是言,则疾速行动、疾速思考、疾速观察,就可以很好地回应诚发出的指令。值得庆幸的是,杨碧薇如今确实在通往这条道路的途中,《碧漪或南红》中的文章可以为此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