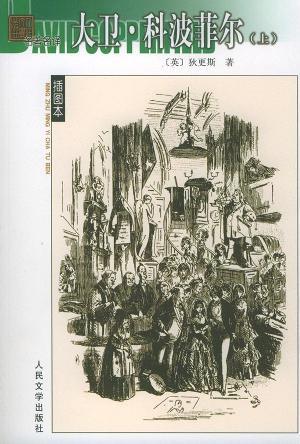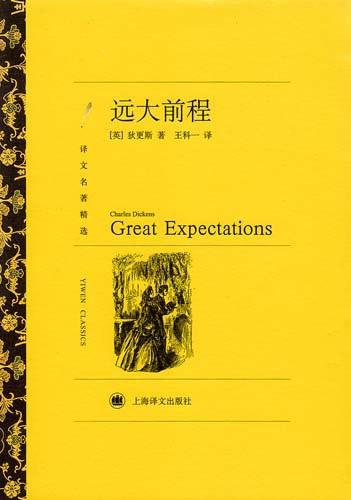狄更斯与他笔下那个灰蒙蒙、黑糊糊,每个毛孔都散发罪恶的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已经远去?答案是,他的主题关切、典型形象不但没有老旧,反而延伸在如今消费社会的每个细胞里。因为人们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依旧没太多“长进”,还是基于金钱关系的表达。狄更斯的遗产就像品种齐全的矿藏,让后辈作家可以反复开采。底层写作、黑幕小说、历史书写、阶层分析、两性婚恋、成长小说,这些类型几乎包孕了现实主义所能探索的方方面面、边边角角。换言之,狄更斯和巴尔扎克一样,都属于“提供世界”的作家。而20世纪以来的后辈大师们,则逐渐远离了对宏大、全面和体系化书写的热衷。他们不是转向内在性的意识探索,就是对差异化、个体化生存抱有更大兴趣。如果说狄更斯这样的现实主义大师提供了一个世界,那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则更多是体会、解释这个世界。
狄更斯的现实主义究竟是何种层面的现实?它是反映论、再现论还是镜子论的延续吗?我们从《艰难时世》这部作品里,似乎能揣摩到作家的态度。小说里那个扼杀一切幻想的葛擂硬,用一套“事实哲学”禁锢残害子女,还办了一所学校,毒害更多学生。他认为世界只有事实,生活只有实际,除了事实之外,不要教给男孩和女孩任何东西。根除一切想象、情感和幻想,有用性才是惟一根本,任何与事实抵触的东西都应被消灭。
抛开作家身份,我更愿意用“社会观察家”、“情感教育家”看待狄更斯的潜在贡献。狄更斯和那些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小说家,最大的不同是他写的几乎全是“有婚无恋”。无论是《艰难时世》里50岁的庞得贝娶20岁的露意莎,还是《董贝父子》里董贝续娶伊迪丝,究其本质都是金钱买卖和人身依附。金钱和年轻美貌是看似“公平”的资源互换、理想交易。这不仅在维多利亚时代,即使如今,依旧是广泛的现实。我们与庞得贝的虚伪相比,或许不过半斤八两。区别只是,我们能用“自由选择”和“主动追求”的幌子掩饰动机上的虚伪。狄更斯看破人性“古今一也”,令后人也可检视自我。他的文学洞察和恩格斯有关家庭、婚姻和私有制的论文一样深刻。
有意味的是,作家在作品中经常关注“儿童教育”。然而,这些所谓教育大多是毒害、摧残和施虐。董贝把儿子交给皮普钦夫人,生性敏感脆弱的小保罗终被摧残夭折。这大抵和葛擂硬把儿子搞废、将女儿露意莎洗脑成“空心傀儡”一样,是奴役压制、奠定威权的隐秘手段。《艰难时世》有系统化批判的全局视野,这是孤立的散点式讥讽所不及的。葛擂硬和庞得贝,一个在意识形态,一个在物质生产;一个在教育,一个在实业。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形成利益勾结的同盟。家庭、学校、工厂和议会生活高度同构,彻底形成“焦煤镇”摧残人性的“工业世界”。这种嘲讽深入到资本主义意识层面,是认识论的批判。从源头上培养资本家的驯顺奴隶,控制其思维方式,用机械论取代生机论,用实利的金钱关系取代情感关系,是狄更斯抽象概括后的文学表达。
由此可见,作家对机械的、无生命、无情感的现实极端憎恶。换言之,他笔下的“现实”不只是事实,而是具有符号化提炼、观念化重塑,以及整体性象征。你会发现狄更斯与契诃夫的互通。那就是在现实上的夸张变形,基于固有轮廓的“漫画”塑造。与“套中人”一样,狄更斯的葛擂硬也有一整套凸显性格的“行为设计”。他的口袋里经常装着尺子、天平和乘法表,随时准备对任何事物量一量。在他看来,世上一切问题,都是数字和计算问题。这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典型化”。事实上,现实人物并不会出现这些极致的夸大。
在我看来,狄更斯将人物性格“集群化”、“阵营化”与“结构化”,成为其写作的一种惯性。他的长篇作品几乎都有对立的两套人物序列,分别归属两个价值世界。狄更斯几乎把穷困贫弱的底层平民同美与善天然联系在一起;而上层豪绅和大资产阶级,基本都成了罪恶丑陋的浓缩。换言之,作品中的人性冲突常有超稳定性,它的流动和变易性则往往被压抑。《远大前程》里的匹普或许是人性历经堕落、受到冲击、回归醒悟的“成长变化”,但这种书写在狄更斯那里并非主流。
《远大前程》是狄更斯晚期最为成熟的作品之一。这种成熟究其本质更加复杂深沉。作家用一种反题反语说明主人公匹普跻身上层梦的破灭。匹普的理想竟然靠罪犯的赞助扶持。罪犯报答匹普的方式是用金钱包装这位“恩主”。主人公的绅士前程、逐爱之旅都建立在这编织的幻象上。匹普和姐夫乔的关系是小说里罕有的真挚情感:他们既如父子兄弟,又像师徒朋友。迷失背离,最终知返,让小说窥探到社会现实对人心的塑造,可能是涤荡,也可能是污化。
作家让我们意识到,底层小人物不止是单向度的被压迫,还有一种意欲跻身上层,渴望“被同化”的“自我憎恨”。人物幻灭,或许是现实主义“落地”和“戳破”的两大兴趣。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幻灭》,皆如此。甚至它还延伸到菲茨杰拉德的“美国梦”破碎。那么,狄更斯的不同在于何处?我想,在于他的通俗小说家作派。在狄更斯那个年代,小说家并没什么严肃和通俗的分别。所谓通俗文学和纯文学,不过是晚近批评家的发明。那么,狄更斯的通俗气息在哪里呢?在于他有大多数连载作家的“习惯”:善于倾听,接收反馈,改变原有计划。
《远大前程》的原有结局与如今完全不同,场景更为凄凉。狄更斯在听从学者的建议后,把结尾改得易被读者接受。他是“听人劝,吃饱饭”的作家。这或许是如今“严肃作家”最不屑的行为:一个大作家怎么能迎合取悦读者?然而,狄更斯在悲剧性、残酷性的主调上,并没有偏离妥协。匹普和艾丝黛拉的青春已经葬送于郝薇香的报复心理,他们始终未能结合,只留下人生的残景:沧桑的匹普再见寡居的艾丝黛拉,在晨雾中走出废墟。我们要从反面看狄更斯给我们的教谕。他显然把接受心理、读者反应纳入到创作疆域里。或许在他看来,从个体私人情感上升到情感共同体的历程,是作家获得不朽的要素。
“孤儿的成长”是作家最用心经营的题材。这与狄更斯创作内蕴的自传性密不可分。在他那些第一人称作品里,大多有自己成长的创伤经历。狄更斯父亲约翰供职海军军需处,常年债台高筑,无力偿还,终于入狱。这拖累妻子住进监狱,狄更斯也早早当起了鞋油作坊的童工。这种童年可谓“不是孤儿,胜似孤儿”。家贫辍学虽属不幸,但也给未来文豪无限广阔的空间,他以社会为大学,以阅历为师。他15岁进律师事务所成为学徒,勤学速记,成为审案记录员。随后的记者生涯为他走向写作做了奠基准备。他夜以继日的勤奋自学,天才的观察弥补了不足四年的受教育水平。《大卫·科波菲尔》正是作家对自己人生艺术性的悲辛总结。“在所有我写的书里,我最喜欢这一本……我和许多疼爱孩子的父母一样,在我内心深处有一个孩子最得宠,他的名字就是《大卫·科波菲尔》。”
这个名字的缩写D.C正是作家名字缩写C.D的倒置。与《匹克威克外传》这类早期作品多以松散的故事连缀不同,《大卫·科波菲尔》更注重结构布局和技巧经营。这是作家走向自觉圆熟的标志。狄更斯的“经验化想象”成为创作的金法则。所谓经验与想象糅合为一,是以实事为骨,重塑虚构“肉身”的艺术。作家把自己想象成孤儿大卫,幼年经历基本投射在大卫身上。他还把父母形象分散移植在米考伯夫妇身上。从而,小说既有笔笔到肉的纪实,依稀可辨的原型底子,又有戏剧化、传奇性的跳脱。狄更斯实现了儿童视角和“移情投射”的统一,同情和自怜两种态度的合一。“一位作者当他头脑里生出的无数人物永远向他告别的时候,怎样觉得好像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投进了那朦胧的世界。”
人道主义和宽恕博爱成为作家创作的内在伦理。和《双城记》里搭救情敌,不惜牺牲的情节类似,《大卫·科波菲尔》中哈姆冒死去救诱拐自己妻子的斯蒂福,双双淹死。这种不可思议的“以德报怨”,或许是狄更斯“理想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的特异性。米考伯的乐天通达,贝西姨奶奶“永不卑贱,永不虚伪,永不残忍”的劝导,都成了小说的观念输出。在我看来,这种“不止现实”的现实主义,把应然的价值悬于已然的世界之上,说明作家对文学训诫、净化功用,始终怀有信念。
狄更斯让人生所有经历都“各尽其用”,把经验素材发挥到极致。他长期在监狱、法院、媒体等环境中,搜集寻访的见闻、轶事与黑幕,使其对社会时代的认知,深入到骨髓和血管里。善恶的分化对立表面看是作家为了小说冲突更加激烈集中、人物场景更加典型,采取的简化手段。但它还有一个深层根源: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本身的分裂,贫富的极端分化。一面是殖民扩张掠夺海外财富,一面是工商寡头盘剥,造成无数城市贫民。贫民窟成了《雾都孤儿》里的都市“异托邦”,完全是边缘化的“他者空间”。狄更斯用肮脏小巷组成的“迷宫”来形容这种都市景象。《雾都孤儿》把贫穷和罪恶划归起来,“穷本身是一种罪”这种荒谬逻辑是小说的根基。“贫民习艺所”代表的救济机制,让人联想到福柯所描摹的收容所本质:以慈善外衣剥削,以救济之名规训。狄更斯写出了贫民的真实处境,他们不过是在死亡和死缓间做出选择(“待在习艺所里缓慢的饿死”与不进习艺所“立即饿死”)。
社会现实促使狄更斯用强有力的“对立性”,概括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同情和批判是现实主义内蕴的两种情感态度。狄更斯的超越处是他介入并改造社会的文学信念。描写现实、批判现实只是第一步,作家相信文学还能走第二步,那就是“反作用”于社会,倒逼改革。仅这一点,就堪称伟大。马克思曾说,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以往所有社会财富的总和。他对狄更斯这类英国杰出现代小说家,也有类似锐评:“(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所揭示的加在一起还要多。”
狄更斯和他的小说世界让人重思传统现实主义与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它们并不能用表面与深刻、老旧与先进来界定区分,它们只是不同创作心理和志趣的分别。我们不应忽视,时代特征对作家心理类型的潜在塑形。狄更斯的写作就像产业革命下的机器化大生产一样,有着广角记录般的恢弘感,整体性环境往往占据极重要地位。而如今的作家,大多更像工作室里的设计师,只在微观视角里把握属于自己的精细,对社会的整全深广保持了一种退守和让渡。狄更斯是和巴尔扎克一样“重现人间”的作家,他们的雄心和天才,未来也难有复现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