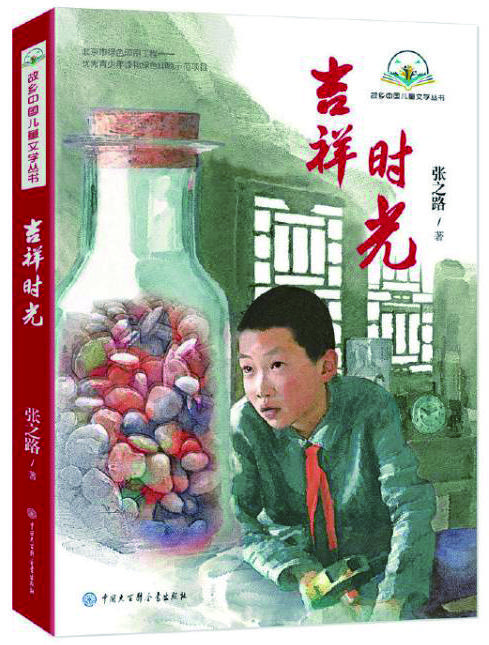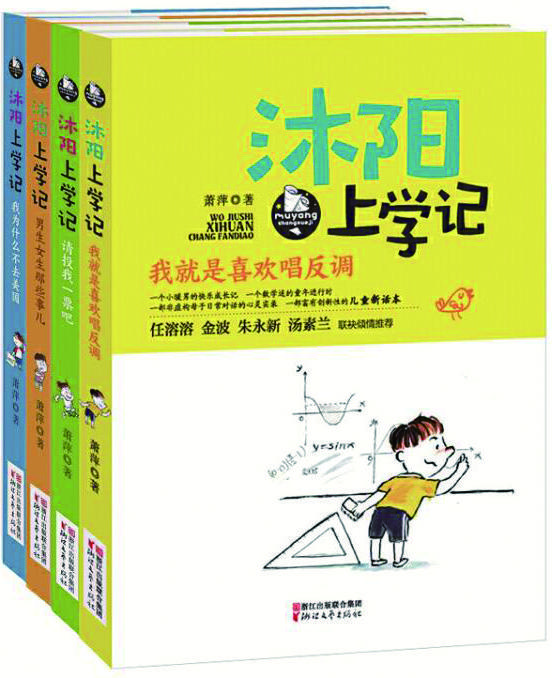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黄金十年,已经是有目共睹的空前繁荣,但此繁荣更多地体现在创作和出版的数量上,作品的总体质量并未能与作品的数量并驾齐驱。从现实主义书写的维度观察,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还明显存在着几个问题:
题材开掘的路径依赖
在这方面最极端的情形就是跟风模仿,一些作品在市场上火了、吸引了读者眼球之后,大批跟风摹仿之作便会涌现,这背后固然存在某些不够光彩的商业操作,而部分作者的投机取巧也是不争的事实。此种写作貌似现实主义书写,其实是建立在概念上的“仿真”书写,是臆想中的现实。而更多的实际情形是,作者固然有独立创作的愿望,却由于生活阅历的不足、创作经验的匮乏与创作的急切心态,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创作题材的路径依赖,即以过去发表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题材类型及其审美走向作为自己创作的蓝本。无论是跟风写作,还是路径依赖,都不是对现实生活真正的深入认知与开掘,其结果都会造成儿童文学创作题材的狭窄、主题的重复,以及故事情节、人物刻画乃至文字呈现的千篇一律,是真正现实主义书写的严重阻碍。
突破路径依赖的现实主义书写,首先要有现实认知能力。现实认知包括两方面:其一是从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表象中找到属于作者的题材敏感域。现实生活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变化中的,只有敏锐的观察和感知才能找到下笔的独特质感。其二是对时代本质的思考与把握,这点其实更重要,作者透过生活表象深入触摸到所处时代脉搏的跳动,把握变迁中的新观念新人物及其新生活方式,这是写作者从独特的题材敏感域中发掘主题、塑造人物、构建审美走向的基点。我们看到近年来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在追随时代的脚步、感受时代的脉动、思考现实与未来方面做出的种种努力,譬如,董宏猷的长篇小说《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是对儿童现实生活广度的描绘;舒辉波的报告文学《梦想是生命里的光》是对儿童现实生存的深度追踪和思考;萧萍的小说《沐阳上学记》,与10年前描写校园生活题材的儿童小说相比,在生活呈现、人物刻画和主题开拓等方面也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差异性。
突破路径依赖的现实主义书写,还需要走出儿童文学传统的自闭小圈子,儿童生活不是孤立的存在,儿童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是成长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现实书写也应将儿童放在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观察和呈现。近几年在这方面颇有一些亮眼的作品,比如张之路的小说《吉祥时光》,小主人公从与院子里各色大人小孩的接触交往中认识社会、感受老北京文化的熏陶,绘制了一幅成年人并未缺席的丰富多彩的童年历史长卷;刘海栖的小说《有鸽子的夏天》,让故事在“山水街”这个阔大的舞台上演出,演员除了儿童还有形形色色的成年人,充满人世间的嘈杂烟火气;叶广芩的小说《耗子大爷起晚了》将一段自由自在的童年放养在颐和园中,红墙内古老的皇家园林与红墙外鲜活的北京市井人文气息在小主人公的生活中交融,共同塑造着一个“北京小妞”的文化精魂。又譬如朱奎的童话《约克先生》,描写的虽然是幻想世界,却活脱脱就是整个人类社区生活的缩影,各种各样的动物分明是人类社会中的芸芸众生,和谐中包容着不和谐,处处是悲喜交融的戏剧性。
打破路径依赖的现实主义书写,更需要提升创作的思想格局,思想格局决定了创作的艺术高度。儿童文学是讲究浅语表达的艺术,而不是肤浅幼稚的代名词,童心童趣是儿童文学审美放飞的翅膀,而不是儿童文学格局降维的依据。儿童的天真与人类更高阶梯上的真实之间存在着无数至简大道,等待儿童文学写作者去探寻。《其实我是一条鱼》在短小简洁的篇幅中,将传统幼儿文学特有的叙事趣味和经典技巧,与诗性高格的审美境界完美交融,散发出哲思悠远的诗意。幻想小说《大熊的女儿》中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关系被给予了颠覆性的重构,前者可以看做代表着高度异化充满焦虑的社会,后者则可看做是单纯而强大的人性净化力量,这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去认识人性弱点与救赎的本质。这些作品表明,儿童文学的题材和文体特征与文学的艺术高度之间没有本质的冲突。
刻画人物的标签依赖
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能立起丰满人物的作品才是一流的作品。
但是长久以来,我们的儿童文学人物刻画普遍存在着某种“儿童腔”,不少作家在有意无意地追求一种拿捏的天真态、儿童气,就像我们成年人哄小朋友的时候那种故意装嫩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路径依赖的延伸,写作者缺乏对儿童的热爱与深入观察的耐心,对童心童真缺乏深刻的审美共鸣,把儿童的特质归纳为若干标签:幼稚、可爱、淘气……缺乏对儿童在复杂现实关系中的鲜活呈现,屈从于对儿童的某些刻板印象,更难以透过人物形象去表现时代精神。
过去儿童文学界曾流行一句格言式的话,大意是“儿童文学作家应该蹲下来和儿童讲话”,但是我们对于“蹲下来”还是有一些误解的,小孩子有的时候希望大人蹲下来和他说话,那是希望获得平等交流的感觉,但是我们往往把“蹲下来讲话”理解成一种模仿和表演,就形成了不自然的姿态。“蹲下来”不应该是对儿童态的简单模仿,而是与他们平视,看进儿童的眼睛里、心里去,看懂他们想什么要什么,看懂真正的童真。儿童文学作家应该从儿童的生命中去感受真正自然天籁的单纯气息,让那种气息渗透到自己的笔下,写出站着的童年,而不是给出塑料花一样的东西。
摆脱刻画人物的标签依赖,需要写作者对于人物所生活的时代、环境有深刻的认知。譬如上文提到的《大熊的女儿》,塑造了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少女形象,令人耳目一新。这部作品的小主人公是一个叫老豆的12岁女孩,与我们过去在儿童文学作品中经常看到的类型很不相似,是带有鲜明的青春叛逆和时尚色彩的当代少女,外表很酷、桀骜不驯(以前这类孩子往往被写成问题儿童、需要矫正),但是内心渴望温情、坚强勇敢。老豆身上散发出一种强烈的属于当下年轻一代那种渴望独立自由、乐观进取、张扬个性的精神气息,具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又如叶广芩的儿童小说《耗子大爷起晚了》和《花猫三丫上房了》,塑造了一个性格突出且独具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北京小妞”形象,在这个人物的身上,儿童的心理年龄特征,与一种大大咧咧又精明爽利的性格特征,以及言语行事中浓郁的老北京市井文化色彩,完美结合、水乳交融,是儿童文学发展迄今并不多见的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特色的儿童人物形象。
摆脱刻画人物的标签依赖,还需要写作者对所描写的对象有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理解,才能用最精到的细节刻画出“这一个”人物的独特性格特征。《吉祥时光》中写到胡同里一些老北京人物,都着墨不多,但是各自的特点,寥寥几笔就很鲜明,很有辨识度。比如写小祥爸爸每天进门,有一个习惯性动作是用一个掸子把衣服掸干净。人物的身世背景家教修养和性格气度精气神儿,就全出来了。送来压箱底貂皮救急的豪爽郑大爷,必须有三个以上听众才肯讲故事的摆谱董大爷,“把好儿放在窗台上”的淳朴李大爷等,都是如此。现实主义书写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刻画人物最见功力之处就是细节,正如泰戈尔赞美丰子恺的绘画:“用寥寥几笔,写出人物个性。脸上没有眼睛,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看什么;没有耳朵,可以看出他在听什么。高度艺术所表现的境地,就是这样。”这是写作者应该追求的境地。
艺术表达的模式依赖
这是关于儿童文学的美学呈现问题。我们强调了很多年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将对儿童读者的接受心理的考量融入到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准则之中,却始料未及地在儿童文学写作者的心中形成了某些约定俗成的“儿童化”表达模式,当我们说某些作品似乎溢出了儿童文学的范围,或者与一般的儿童文学不一样的时候,恰恰证明了这个模式的存在。儿童文学艺术表达的模式依赖,无疑是大量儿童文学作品千篇一律和平庸无奇的重要原因,并掩盖了一些儿童文学写作者文学修养和艺术才华的不足。
儿童文学是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为文学的本质决定了其应与其他文学门类站在同一条艺术准则起跑线上。人们在论及儿童文学创作题材禁忌时,曾有句话“儿童文学没有禁区,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此处我要谈的是,在儿童文学的艺术表达上,“怎么写”也是永远的命题,写作者必须根据自己对艺术准则的悟性,去求解儿童接受心理与艺术独创性之间的每一次有机交融,写作者不同的艺术个性、艺术创造能力决定了每一部作品不同的美学呈现。
《耗子大爷起晚了》《花猫三丫上房了》,从儿童形象塑造到文学语言,都与模式依赖下的儿童文学大相径庭,尤其是作者那极具辨识度的文学语言魅力,既充满浓郁的老北京风味,又融入了叙述主体小丫丫鲜明的性格色彩,同时,整个作品的叙述宛如中国书画的“骨法用笔”,遒劲、入木三分,只用简单的对话、动作,就能呈现立体鲜活的画面感。无独有偶,刘海栖的小说《有鸽子的夏天》《小兵雄赳赳》,也展示了其富于辨识度的叙述风格,作品用淳朴得近乎木讷的“人物的语言”,对小主人公们的日常做简洁而颇具工匠精神的叙述,在一派毫无修饰的原生态气息中,透出某种“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幽默感。这些作品中,约定俗成的“儿童化”表达模式不见了,极简、空灵而准确的叙述与丰富的生活内容相得益彰,作家以真情实感和去除矫饰的文字所迸发的力量,建构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艺术表达的独特美感。
如何让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不再有“路径依赖”“标签依赖”“模式依赖”,不让轻车熟路成为阻断思想和艺术腾飞的桎梏,不让作品成为时代更替中艺术生命短暂的过客,需要写作者有透视生活本质的能力、深入诠释人性的能力、与童真共情的能力和艺术创新的能力,当写作者用崭新的目光和思考面对各个时代现实生活的时候,便能书写出全新的、有更长久生命力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