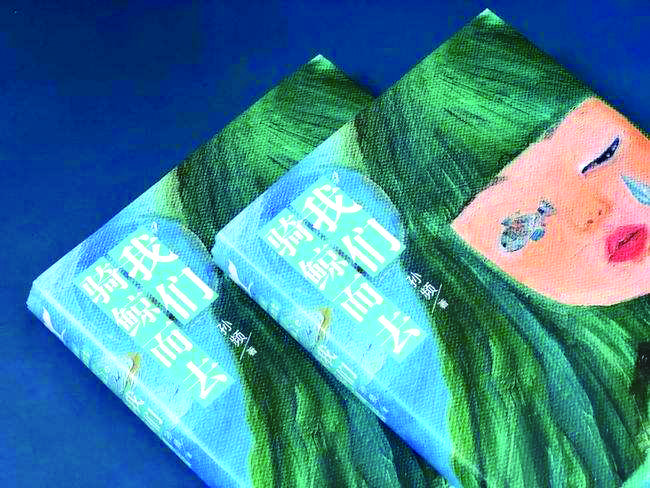何 平:《我们骑鲸而去》是孙频最新的“大中篇”,是思想容量和本身体量都很大的一部小说。这本书涉及到今天这个时代里每一个生命的个体,每一个人在生活、生存、生命中所涉及的困境,以及遭遇这样的困境后,又如何重新设计和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先来问问孙频,为什么要写这样的小说?
孙 频:最初的原因是因为我对岛屿的好奇。从我踏上小岛的那一刻起,我觉得小岛与大陆有非常大的不同,完全不同于大陆的生态。小岛有可能会从恐龙时代一步跨到今天(现代),中间没有种种人类繁衍出的文明,所以小岛有着迥异于大陆的气质。而且孤岛是在大洋中间,虽然看起来周围茫茫皆大海,人可以自由来往不受拘束,而事实上正因为四周都是海洋,它其实变成了“牢笼”,是非常孤独的地方,这也是我很有兴趣探索的地方。我就想,在孤零零的小岛上和在大陆上究竟有什么不同,生活在这里的人和大陆上的人又有什么不同。
何 平:孙频首先讲到了大陆和岛屿之间的关系,她所讲的大陆是人类文明化的空间、社区,我们在大陆有盘根错节的人类关系网络。而岛屿上只有稀薄的人类文明(近几十年人类文明),只有三个人在岛上重新组成了社区。
项 静:何老师刚才说到当小说里一个故事出现的时候,会牵连着许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际关系等关系和构造。很多小说都可以按照这样的概念、脉络去分解、梳理,人物形象的出现、主要矛盾的出现,都可以由此得到解释,甚至很多小说完全依赖于这样的社会结构。但孤岛给你带来了提问,当你把这些原因去除的时候,人如何为人?如何成为自己?如何确立自我?孤岛的环境就打开了文学上升的一个空间。我们常常依赖的那些概念、框架对小说家提出了疑问,同时孙频为自己前期的写作拓展了新的空间,文学没有面对那个空间也是很大的缺憾。
何 平:一个作家为什么在今天火热的时代反而把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社会”挪移到了一座孤岛上?刚才项静讲了一个词“依赖”,作家特别依赖貌似复杂的社会关系,批评家也依赖这样的社会关系。离开了这样的社会关系,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默契好像就没有了。我们谈一个东西往往要借助大的历史场景、大的社会事件来确定活动意义。孙频却在小说《我们骑鲸而去》中“做减法”,她让人离开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社会,到了孤立的岛屿上,一定意义上,她是在重建小社区。
孙 频:其实小说的故事是非常简单的,我想开拓一种新的叙事空间,在小说的形式上,也希望把小说的空间打开,所以我会在里面加入一些东西,比如说加入一些副文本,把小说空间从“一个面向”变成“两个面向”。希望它变得深邃一点、深沉一点。
何 平:小说中的三个人在大陆上的日常生活中都有一个职业,有固定的收入,到了岛屿上要重新回到类似原始的状态——农耕、渔猎,要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关系,就有可能出现不平衡的关系,其实就是资源分配的问题。中国也好、西方也好,从来都有发生在荒岛上的故事,但你写荒岛,他也写荒岛,你的荒岛和人家的荒岛有什么不同?孙频笔下的老周和鲁滨逊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荒岛上的人和你读的小说中那些岛屿上的人,又有什么区别?
项 静:我倒是没有联想到那些小说,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是有隐喻性的,也有殖民时期野心勃勃的部分,尤其是康拉德小说一开头有非常宏大的气势,那些小说当然非常好看,现在看的话也可以重新感受。但孙频的小说,我刚好是在疫情期间这样的特殊时期读到,还是蛮符合我们的心境。之前,在没有疫情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感受到“岛”的感觉。
何 平:每个人戴口罩,就是把自己隔离成岛屿。
项 静:疫情期间,一男一女在房间里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两个人两三个月朝夕相对,该怎样处理彼此的关系?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在正常逻辑里完全不会出现的问题。这就像孙频小说中,三个人放在孤岛上所产生的内部的张力一样,这三个人无法避免遇见,就要在一起生活。
何 平:然后,原来现实的逻辑不适用了。
项 静:要重新创造逻辑,要重新创造公共文化。这是很打动我的。孙频小说给我很大的启示,每个人上来演自己的故事,这有点像话剧,而不是跌宕起伏的小说。小说里的三个人是迥异的,每个人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关注的点是什么,都很清楚。小说的核心还是要寻找自我,到底我何以成为自己,过去和现在怎样界定“我”,对自己有交代过去的意义,就像王文兰一样,她对世界有自己固定的理解、固定的看法。
孙 频:我有一点想补充的,什么叫剧场感?每一个上岛的人,每一个在大陆上很平凡、很普通的人,当你上了岛,忽然就变得像个演员,这是因为孤岛与世隔绝,过分的孤独会导致把一切无限放大,这种放大本身就会产生一种戏剧性,你本来是普通人,但一登上海岛就会有演员的效果。
老周在自己的破屋子里自己演木偶戏,目的是为了打发时间,心灵也有所寄托,每个人都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来度过此生。没有人,他就给木偶人编剧本,最有趣的是他在自己的桌子上把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海岛全搬过来,每一座海岛都存在他的脑子里,他可以把每一座海岛的故事都在一张桌子上上演。在那么小、那么孤独的一座海岛上,居然可以容纳全世界的海岛,所以他把自己的桌子叫做“世界剧场”,如此封闭狭小又如此巨大辽阔,碰撞在一起会形成比较奇怪的张力,这种张力会给人剧场感。而小说中的那些小话剧本身就是对即将上岛的人日后可能的生活和精神状况的暗示。
何 平:刚才孙频说到了在小说里如何构成张力。人一旦到了岛屿上,好像自己的人生就有一种戏剧感,大家都成为了演员。计量单位发生了变化,你在岛屿上的生活和你在大陆复杂人际关系中的生活,对时间的感受、对生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空间感受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孙 频:就像一个人在地球上和月球上对时间的计量单位是不同的。
何 平:所有的时间被压缩到岛屿上,所以人对外界的感受、对世界的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小说中一个备受磨难的女性到了岛屿上忽然有了一种自信,因为她认为她的世界就这么大。所以说,这个小说里人到岛屿之前和之后的感受是有变化的。
孙 频:上岛之后她反而有了自信,因为没有了复杂的社会背景。
何 平:老周想象的生活是“节花自如”,有老庄精神,说到老庄,我想到“骑鲸”这个词在中国的古典诗歌里跟老庄的东西是有勾连的。我们现在读很多小说,还有些读者不愿意读小说,但其实读小说是有附加值的,小说提供了对人、对世界的思考。换句话说,小说家不只是讲故事,还要有思考社会的能力。
项 静:何老师这点说得很对,小说家一定要提供除了故事之外其他的东西,但仅仅就小说来讲,有时候我们确实面对现实的、真实的、物质的世界,同时,也一定要有空间打开小说的世界,这才是小说存在的理由。小说不仅是对世人作出什么样的启示,也要有游戏精神,譬如你为什么要写孤岛的作品。
何 平:游戏精神特别好,这个小说里有很多游戏精神,把莎士比亚很经典的话剧与老周在孤岛上创造的“世界剧场”相呼应。
项 静:写作者自己也是有“游戏精神”的,想把文本做成对自己来说的挑战。一马平川从小说的世界穿行没留下什么,就有空落落的感觉,这就是小说的游戏精神。孙频小说看起来有很多进入的途径,这也是写作者很理想的状态。看一本小说会联想到无数小说,这也是小说生产力的表现。
何 平:近几年里孙频对自己的小说做出了有意的突破,她有一种自觉地对自己进行挑战的感觉,不愿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为什么从2016年开始,你不走自己特别熟悉的道路了,究竟是什么使你对人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发生了变化?
孙 频:我的小说从2016年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确实如此。因为对早期写作的那些题材、素材,我已经没有写它的动力了。一个作家的写作必须要有真正的内在动力,不迎合任何人、不讨巧、不依靠外在的东西,为了迎合的写作会脆弱而短暂,最可怕的是你在这种写作中可能会失去一种真正的兴趣和热爱,这是非常恐怖的。那写作真正好的状态是什么?我觉得是,哪怕你写得再辛苦,你都觉得是充满乐趣的,是带一点“游戏精神”的,不停地探索新形式、不停地探索未知的领域。无论是“游戏精神”还是“自我挑战”都是为了保持自己内在的动力,写作中保持真正的动力特别重要。
何 平:刚才孙频谈到了她写作理念的内核,写作中有她自己各个阶段对世界的“人性实验场”,如果一个作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当成“人性实验场”是可疑的。孙频早期的写作通过少年经验来推动,但现在这个阶段显然她变得内敛、平静。刚才孙频讲到的热爱以及那种探索的欲望,也是打动我的东西。现在我们有一种看法,认为一个作家的写作要抛开自己的个人经验是比较可疑的。
项 静:刚才孙频讲她创作的心理经验,确实是很打动人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文学如果跟个人经验完全没有关系、跟个人好恶没有关系的话确实很难。写作一定要跟自己内心的成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每一代作家都有自己的当下性,如何体现当下性?就是个人跟社会的连结感。一定要把自己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你是在世界中穿行的,有很多社会经验覆盖在你个人的身上,以自己的方式讲述出来,所以我非常欣赏孙频不断反思自己的过程。
何 平:保持一种警惕。所有的艺术都会战胜自己保守的东西,一个新东西出来的时候接下来就会产生自己的保守性,写作之所以有先锋性以及引领人的思考,就是在这个部分对自我进行过否定,对我们所从事职业的保守性做出过一点反思。《我们骑鲸而去》特别好的部分就是抛弃了现实运行逻辑的所谓权力,进到岛屿之后,成为了更微妙的“微权力”,是真正影响人心走向的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