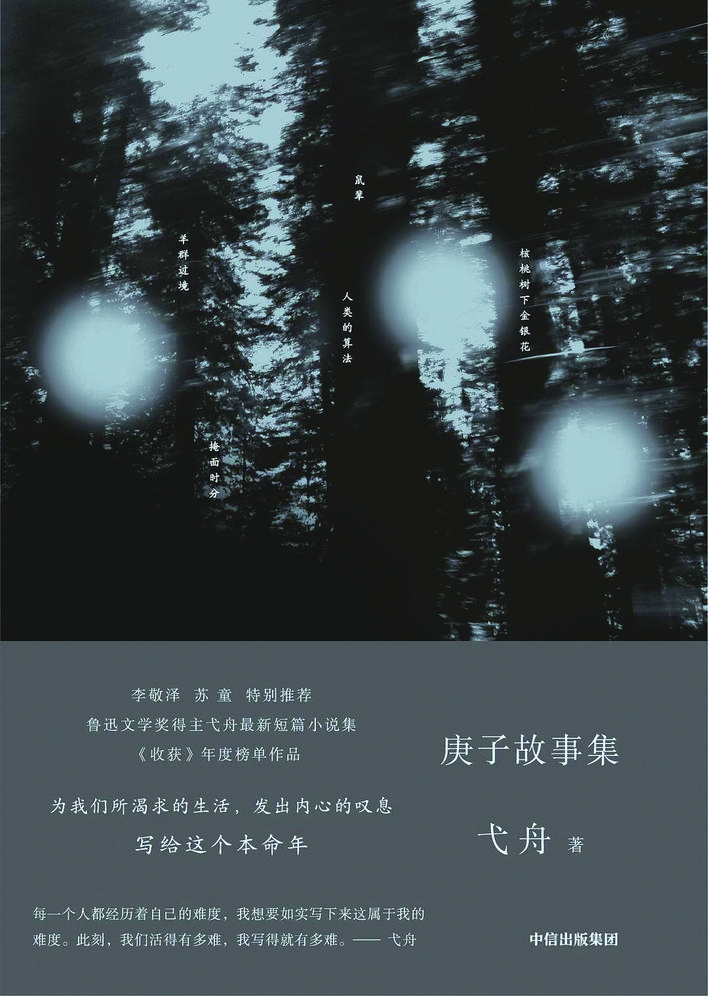线性时间与空间渗入
田雪菲:读完《庚子故事集》后,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去记忆故事,“空间”显然可以作为一种记忆术,提供叙事“定格”的艺术效果。与时间的流动性不同,空间可以“悬置”时间的飞逝,激活我们的记忆。利用这些被定格的空间,我们能够轻易回想起彼时彼地人物的矛盾处境和复杂情绪,如《核桃树下金银花》中,“我”游走在玉林街上期望与“胖天使”重逢;《鼠辈》中,北京城无数“炫灿”大楼的灯光与落单的鼠辈们构成呼应;《人类的算法》中,女主人公在国外、家、酒店这三个空间中切换身份;《掩面时分》中,人物关系场景也无非是露天餐吧、医院和办公楼;以及《羊群过境》中不断被唤起的甘南场景。人物既属于时间,也同样属于空间,如果不考虑空间因素,可能会忽略掉文本本身的某种复杂性。
赵志军:《丁酉故事集》叙事时间和空间还是统一的,而在《庚子故事集》中,身体实在的空间与记忆或者情感牵系的空间是割裂的。尤其是《羊群过境》,“我”被禁锢在家中,与蒙古捐赠的羊群过境甘南的开阔幻想,无疑通过这种幻想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张力,而幻境越开阔,越显得疫情之中人被束缚在有限现实空间中的煎熬。
战玉冰:从《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到《庚子故事集》,弋舟这几本小说集在命名上明显呈现出某种“编年史”的创作意图。“时间”既构成了他这几本小说集的名字,也深深内嵌入其中每篇小说的深层肌理。他这几本小说集中大多数的作品,都可以借助弋舟在《丙申故事集》“代后记”中的说法来加以总结和理解:“与过去重逢,回溯与检索,不就是时光的题中应有之意吗?”而弋舟这几本小说集中的空间表现,相对而言则比较分散,并不是统一的“约克纳帕塔法”式的整体构思,但依旧各有其特点。比如《核桃树下金银花》中,“我”去送快递而后在街巷中迷了路,街巷在这里成为了某种迷惑性的空间,更可以视为主人公当时心境的象征性外显,而“胖女孩”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则是对“我”的指引与解救,有一种迷惑之中获得希望的意味,这种街巷之中的迷惑感让我想到莫迪亚诺的《暗店街》,是一种很迷人的都市空间书写。
李博权:如果严格看待小说题目“庚子”的时间性,无论是作者的写作时间还是叙述的故事时间都呈现出逃离这一“总体”时间的框定。因此如果讨论小说的时间性,主要体现在读者阅读时的时间感——小说的直接叙述以及小说内容涉及时间的空间形式表现。即作者在尽量避免对时间的“确定”,而是通过小说场景-空间的叙述形式来表现“此刻”的时间。但正如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中所说:“空间的现场性把人和事变得具有时间的现场性”,不过这里面作者有意调停的痕迹就会很重,一种出离于叙述的“刻意行为”让这种“现场性”变得“虚假”,于是,叙述时间、故事时间、现实时间在空间里“欢聚一堂”。那么这种不被确定的“时间”却又表现出强烈的时间感就在阅读的过程中互相冲突,最后会落实在哪里就取决于一种阅读的“选择”,这也是一种开放性吧。
情节破碎与瞬间凝固
田雪菲:“破碎”是我阅读这部小说集最先生发出的感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故事场景的跳跃与转换,每篇故事至少包含三个及以上的场景,而场景之间的转换常常倚靠人物的回忆或联想,这往往造成“出其不意”的阅读效果;二是作者在小说叙事中表现出强烈的“意识书写”姿态,小说人物的意识告白不断敲击故事主干,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小说的叙事节奏,使读者阅读起来并不容易把握叙事的进程与方向,因此也就不那么感到“舒适”;三是场景的转换与人物自白的打断使故事情节发生支离,整体呈现出拼接、碎片化的感受。但我想指出的是,虽然作品带有破碎的色彩,但每篇故事的结尾似乎都在寻求一种“和解”,仔细体味的话,这些充满深意的结尾大都传递出和谐、温情与希望,这正构成了作者写作的另一种诗意存在。
赵志军:我接触最早的弋舟小说是《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最直接的阅读感受,这是一篇关于人在关系系统中存在状态的寓言,可以直接与《圣经》巴别塔故事进行对应阅读。巴别塔讲的是大地上的人们联合起来建筑一个伸向天空的通天塔,去验证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打乱了人们的语言使之无法沟通,通天塔的工程便终结了。我个人更愿意把天通苑视为通天塔坍塌之后,在大地上遗留的庞大而破碎的废墟。其中的人们正是处于一种无法沟通的后巴别塔境遇。对应来说,如果说弋舟创作中确实存在一种破碎感的话,作为其对应物存在的整体,应该是一种人与人沟通顺畅、和谐共生并真正作为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境遇,关涉的始终是人的生存状态。
战玉冰:“破碎”其实并不只是弋舟一个作家的特点,而是“70后”“80后”乃至更年轻一批作家的共同书写特征,与“50后”作家们更加渴望从整体上把握时代和历史的创作“野心”有很大不同。年轻一辈作家们小说中的这种“破碎”,一方面对应的是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表现,似乎通过这种破碎的书写方式,就可以更好地抓住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尽管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明显的距离;另一方面,也许弋舟有意通过这种“破碎”的方式来试图逃逸某种生活的“宰制”。比如他常常通过插入一些令人意外的情节与情绪营造出陌生感和惊奇感,或者是通过突如其来的时间、事件与人物来打断之前的叙事进程,进而营造出一种诗意。这种“破碎”所形成的人物内心张力也是很微妙的,这种微妙可以说正是弋舟最善于捕捉和表达的内心感觉。
建立与坍塌仅关乎自身
赵志军:如果留心《鼠疫》的插图,诡谲的画面中清楚地立着一个十字架,这种浓厚的宗教意蕴,是我读弋舟作品时主要的进入路径。“失败的胖子”“落单了的家伙”被禁锢在庸常与破碎之中,像快递一样被“下单”“运输”,然后放置于某种规定的情境。当他们试图通过记忆或幻想突破这种禁锢时,寻找“应许之地”这一宗教过程便被激活,于是“漫山遍野的壮丽的花海”以及“炫灿”的城市之夜在漠然的叙事中温暖地凸显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幻想被粉碎,记忆被证明虚无,一种强烈的荒原感就此而生。正如《核桃树》的插画,人在追寻途中坠落,被嶙峋的大地永久地固定为破碎的形式。这种比较缥缈的宗教意蕴,漫溢于弋舟多数的独语小说中。它们虽然语涉灵肉关系,但没有严肃地构建宗教精神体系,不在人性神性的谱系中寻找人物位置,而是努力呈现那些能够审视自身存在、能够鼓起勇气追寻应许之地却最终失败了的人物其内在的,一种无关乎神亦无关乎他人与环境的极孤立的宗教情感世界。如同思绪起落,其建立与坍塌都与外在无涉,仅关乎自身。
田雪菲:我所理解的荒原感,有另一种面相,类似于个体置身于“无物之阵”中的自我搏斗。五篇故事中的主人公几乎都有这样的“荒原”体验,实质上这是现代都市人普遍的精神荒原处境。那么,作者如何来处理这一荒原感。很明显,弋舟通过加入大量的宗教元素,来召唤精神的“原始强力”,趋向于人的自我拯救。如《核桃树》中,“不过区区二十斤”代表了“我”的生命限度,“我”不断与这二十斤搏斗,也是在与生活博弈。以及《人类的算法》中,数字“150”代表的是人类认知能力被允许承载的极限,当超过这一极限后,生活就会重新洗牌。在类似种种上帝视角的审视与指引之下,“我”不断接近甚至获得了近乎神旨般的精神感悟,与自己、与世界达成和解。
李 杨:《羊群过境》中,“羊”出现过三次。一次是在标题中,一次是“我”和父亲讨论去甘南吃羊肉,一次是结尾处“我”脑海中看到高原的地平线上有羊群越境而来。在小说中,正是吃羊肉的欲望让“我”得以劝服父亲前往甘南,而出现在幻觉中的羊群过境让“我”得以爬出黑暗的天空。除此之外,融合物质作用与精神表现于一体的“羊”的形象,帮助弋舟思考满足物质需求与探查精神困境,提供了绝佳的符号载体。
李博权:正如弋舟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在医护之外还有很多人正默默维持这个世界的生活秩序,在口罩之下还有很多隐忍不发或难以言说的心事与秘密,在疫情之外人类还有很多‘轰轰烈烈’的平庸困境,以及孤独与爱。”这里我们不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凝视“庚子”这个时间整体时,我们究竟在看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