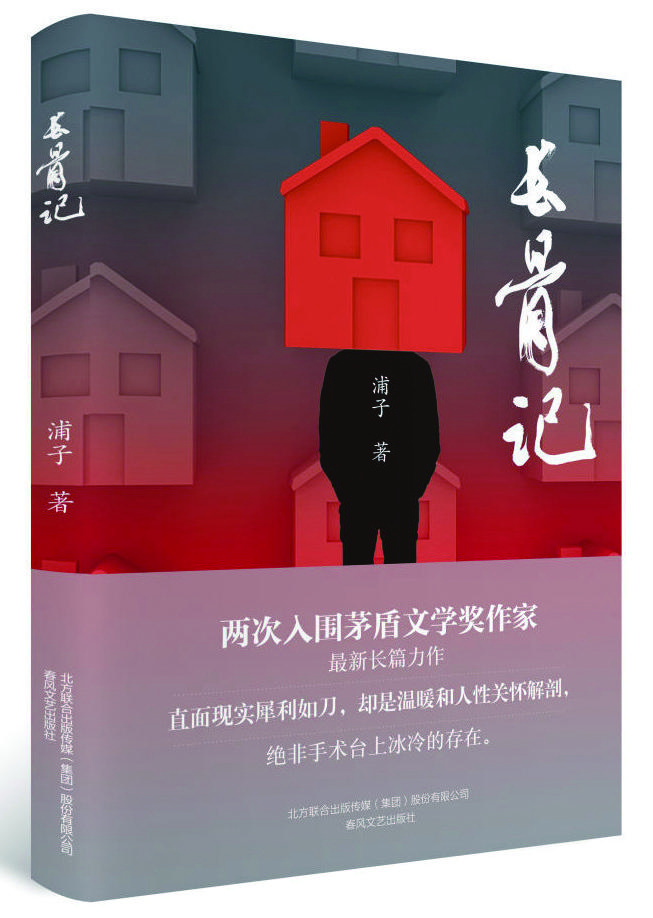紧扣时代脉搏,倾情书写家乡浙东人民的时代精神图式,展现大历史奔流中浙东人民的传统、现实、文化与人性底色,是浦子一贯坚持的文学策略。他的创作总是能够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捕捉鲜活的社会生活,探入历史文化生命的深层,将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对浙东父老的乡情与文学的生动追求熔铸在一起,深耕细作,力拔千钧,开创了一幅以厚重的历史感、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鲜艳的浙东现实色泽而独树一帜的文学景观。浙东的传统与现实、文化与人性、生命与图腾等都是他文学抒怀的对象,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浦子是一个痴迷于浙东历史与文化的作家,他坚持不懈地解剖着家乡浙东土地上的文化人格,书写着浙东芸芸众生的精神操守和饮食生活。他的“王庄三部曲”、《桥墩不是桥》都以其特有的浙东文化底色和人性解剖广受关注,新著《长骨记》是继此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作品以H市德富炒货公司董事长施德富与祖籍浙东山海县的上海商人方靖北之间的一间商铺产权归属的纷争为主线,书写了施德富女儿H市人大代表、先进青年企业家典型施大男与方靖北之间围绕商铺产权之争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折射了在商品经济大潮下某些基层法制工作者沦为“司法掮客”的变异人生与扭曲人性,深入思考了中国社会在法制进程中的痛点以及需要突破的深层着力点。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行法难之病象在中国个别基层政治、司法系统中近乎一种常态,某些地方领导和司法干部违法违规干预案件,以各种手段干扰、破坏司法公正,个别基层司法干部知法犯法,忘记初心,出卖灵魂,用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谋私利,热衷于权力寻租,甘为司法败类,这种病象已经成为严重阻碍我国推进法制文明进程的毒瘤。《长骨记》直面现实问题,将现代基层社会中的治理难点糅合在一起,为当下中国基层法制文明建设探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和时代感。在基层的社会网络中,权大于法在某些官员的内心根深蒂固,甚至一些司法工作者自甘将法律拱手出让给权力。H市某区区委书记江枫玩弄权力于掌中,权力的欲望甚至让他觉得封建时代的县官“拍桌就能定案来得舒坦”。以法院院长王正中之流为代表的H市的司法干部口口声声代表人民,其实,在他们心中,人民二字早已经变了味道,他们已经忘掉了自己的初心,王正中父亲临死前交代他:“正中,你心里得有党性,得有良心。”但党性和良心早被他出卖给了个人欲望和对更高一级权力的奴颜婢膝。某些基层司法工作者心中无“法”,个别地方官员用权力干涉司法公正,这些丑陋的存在都使得施大男和方靖北之间一场原本极其简单的商铺产权官司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对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是浦子创作的一贯优点。从《龙窑》开始,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在不断地走向现实,挑战世俗,这是浦子寄予现代女性的一种新希望。如果说《龙窑》中的寡妇翠香、玲娣只是一种遥远的存在,那么,在《大中》中的女大学生婴婴,《桥墩不是桥》中的律师薛家丽、社会学专家薛敏,乃至《长骨记》中的H市人大代表、先进青年企业家典型施大男这些女性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浦子寄予理想女性的特殊素质,她们越来越被赋予知性的品质,但她们身上那种原始勃发的乡土芬芳却依然没有丝毫改变。正是这种原始的勃发力,使得浦子笔下的人物更显得真实,女性的刻画也更加深刻,形象的塑造更加接地气。例如薛家丽,她与几任村长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围绕着她对桃花庄的美好明天展开,这种看似放浪的行为,既显示了乡村治理中现实的窘境,另一方面也闪耀着圣洁的色泽。而施大男,她的看似玩弄各色权力场的主导者于掌中的行为似乎可以给她贴上“欲女”的标签,但反过来,在个别基层司法腐败的现实中,你又不得不佩服她才是一个“真汉子”。
任何成熟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精神地理和不懈编织的文学空间,浦子亦如是。多年来,他的创作立足于浙东,无论是王庄,还是桃花庄,这些都有其家乡的影子,《长骨记》虽然不再局限于浙东山海县一隅,而是将中国内陆的H市与上海带入了叙事的空间布局,给我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叙事空间架构,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和浦子的故土情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充分体现在他对方靖北这一形象所寄予的深厚情感上。方靖北是浦子的山海县同乡,他们同样接受着浙东深厚历史和优秀文化血脉的滋养,住着一样的道地,一样把道地大门称作阊门、管巷道叫墙弄,这里有盖仓山摩天柱、伍山石窟、下洋涂、前童古镇、潘天寿故居、柔石故居、徐霞客大道……这是浦子和方靖北的精神故园。方靖北虽然叱咤上海滩,成为浙商的典范,但他真正的精神地理依然是养育了他的山海县方庄。这种文学空间上的走出家乡写家乡,使浦子作品的精神格局在广度上有了更进一步的伸延,而在其深度上也有了相当大的提升,这喻示着浦子正努力尝试在一个更大的、更具有时代性的视野中来审视中国的社会现实,思考文明中国的出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长骨记》于浦子而言,是一种大的自我突破和超越、一种文学空间的再出发和精神家园的还乡。
浦子的作品,总是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温暖,这与他对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虔诚的敬畏休戚相关。这种敬畏深植于其文学的冲动之中,进而转化为他的创作中的一种自觉的审美实践和文学记忆。可以说,浦子的创作不是在进行着各种文化寻根的尝试,而是在他的文学情感深处,始终有一个巍然不动的文化之根,它不需要去寻找,需要的是表达,这个根就是浦子对于浙东敦贤儒雅的传统文化的敬畏。无论是“王庄三部曲”、《桥墩不是桥》,抑或新作《长骨记》,我们始终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在浦子的作品中蓬勃地流淌。方靖北身上敦厚儒雅的儒商精神隐隐有着《独山》中王传达的宽容温良,也有着《大中》中王德青的隐忍敦厚,而他心里装着“这世上的人都不要了”的祖先和孔圣人则更是浙东的文化精髓。浦子塑造方靖北这一形象体现了他对于浙东文化精神和人格人性的礼赞,展示了浙东人在历史激流中的拼搏血性与温良中和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浦子带着浓郁的浙东传统和地域特色的文化理想。
浦子是一个具有内心深度的作家。别林斯基曾说,“如果艺术作品只是为了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任何发自时代的主导思想的强有力的主观冲动,如果它不是苦难的哀歌或热情的赞美,如果它不提出问题或者回答问题,那么,这样的艺术作品就是僵死的东西。”浦子的创作是有着鲜活的生命力的,它让我们更多地感受到一个优秀作家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身处的时代、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善良美好人性的真诚以及对国家兴亡深沉的忧患情结。浦子曾自喻自己是一把中国乡村社会的解剖刀,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他是一把带着现实的温暖和人性的关怀的解剖刀,而绝非只是那种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的一个冰冷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