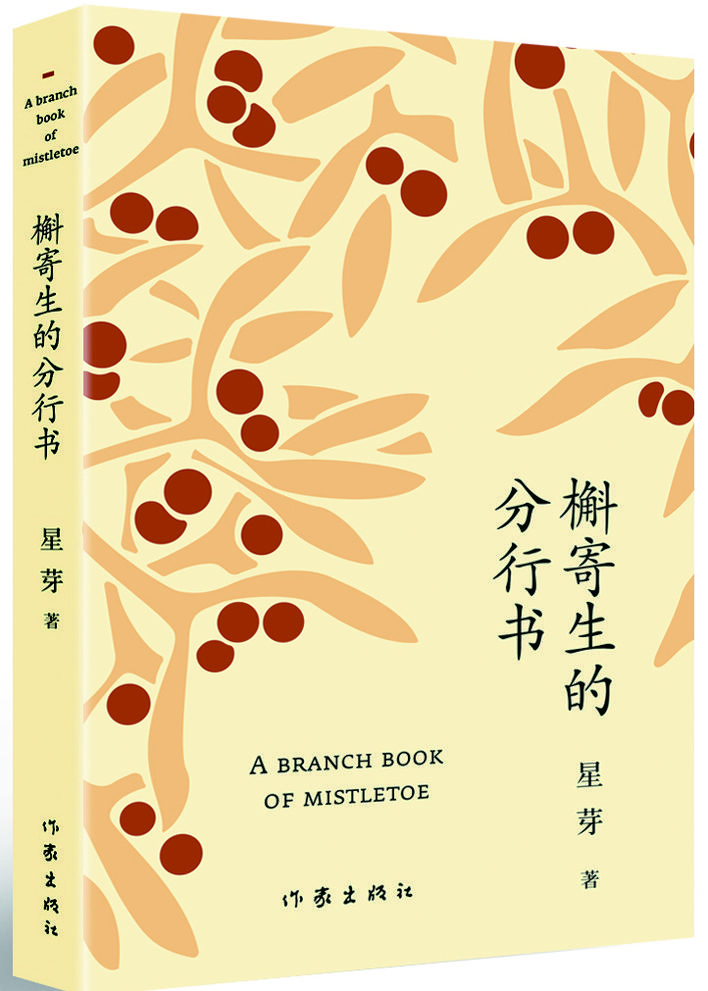星芽在大学一年级即开始诗歌写作,应该说起点是比较高的,甚至透露出较同龄人“诗歌早熟”的迹象。作为起点的写作,星芽的诗几乎都是在图书馆完成的,这投射出写作的初级阶段阅读经验不可或缺的影响,比如“就听见手臂里的树枝在生长/那一定是一些导火索/它们还会长出绿叶 甚至开花”(《树》)让我想到的是当年狄兰·托马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由此,青年、阅读、写作构成了典型意义上的青春期写作的精神面孔。
作为起步阶段的一些诗也更近于碎片,还未构成整体、有效意义上的“诗”,它们的更大效应在于对应了写作者的一些基本能力或才能。同许多人一样,星芽在写作的最初阶段都试图寻找诗歌的“深度”,由此我们在她的文本中会发现一些“大词”,比如《失踪的蜗牛》中的“制度”、“人本”、“理性”、“智识”、“人群”、“废墟”、“永恒”等等。她的诗并未完全局限于成长期的个人经验,而是加入了大量的智性、心象、幻觉和超验的元素,较为可贵地发现了那些不可见的或反日常的部分。
如果从经验和记忆层面来看,在星芽的诗中我们能够看到空间经验,目睹乡村几代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命运,比如厨房中的祖母和母亲,这构成的近乎是潮湿阴冷的黑色精神刻度以及浓重的异乡感。童年和记忆往往是从胃部和味觉开始的。《城市里的苦菜苗》《空心菜》这些诗作中所深度描摹的蔬菜让我们看到了日常乡村世界的褶皱和静水流深式的波澜,它们是日常的滋养也是日常的苦难。值得注意的是,几乎从最初阶段开始星芽的诗歌就显现出“理性”“智识”对感性和性感的平衡或压制,因此她的诗歌几乎从一开始就不是“滥情易感”的,而是带有节制和知性的诗歌品质,这既是形式上的也是语言层面的。一个写作技巧和细节在星芽这里比较明显,她在一行诗的内部予以划分、停顿或延长的时候几乎从来不使用标点而是使用空格的形式。
也许是学习过绘画的缘故,星芽诗歌的视觉和质感是比较突出的,甚至可以称之为“物象诗”。值得注意的是星芽有很多诗歌深度注视于那些动物景观,比如蜗牛、牛、喜鹊、乌鸦、孔雀、刺猬、蜥蜴、青蛙、鹦鹉、黄鹂、红嘴鸥、长颈鹿……这些“物象诗”无疑是诗人予以深度凝视的结果,物象从日常情境中转化为精神现象,从而具备了象征功能和个体精神寓言的质素,如《刺猬的生日》《樱花木》中的画面、场景和细节,当其与生命化的精神象征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那些既真实又虚幻的形象,它们位于日常和想象的边界之间,诗歌也因此获得了额外的精神载力和心理势能。
星芽的诗总有逸出日常经验边界的冲动。由此,“词与物”在她这里往往呈现为“反常”的状态,超验和散漫的幻象总会程度不同地参与到日常之物和经验化情境。2015年,年仅20岁的星芽,她的诗中已开始闪现“失眠”“梦游”和“死亡”的黑色碎片和变形的失重感,而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诗人近乎天生的沉暗的精神面孔。诗歌《撒旦曲》带有“自传”和精神剖析的色彩。这既是对自我的理解也是对他者的审视,而二者往往是同时开始的。星芽的诗不乏戏剧化的戏谑和反讽,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在黑夜的舞台上做出各种表情但也不致于失控,“发出戏剧化的哭声与笑声”(《蜗牛的光圈》),她的诗中还有着特殊的角色意识和身份辨认,这使得我们的阅读也带有了特异的感觉,比如《租赁时光》《梁祝启示录》这样的诗,“我的女朋友曾经是这里九楼的租户”(《租赁时光》)。与此相应,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自白”和更为私密化的诗句……
需要提及或提醒的是,一个人的诗歌起点过高的话也会对此后的诗歌形成不小的桎梏,如果不予以及时地纠正和自我辨认,诗歌的惯性或“自我风格化”也会越来越强。读近期星芽的诗,我总是有些不尽满意之处,比如“说理”和“自辩”的成分越来越重,也许这正是我对一个年轻写作者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