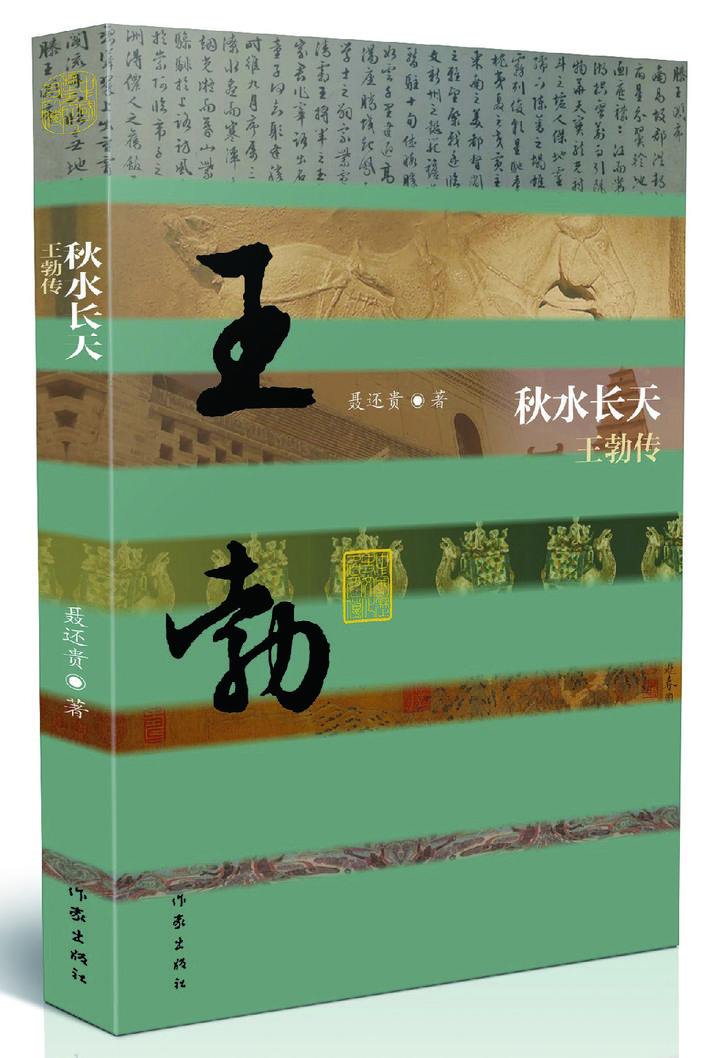□聂还贵
不止是诗人,名冠“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更是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其被列为中国作家协会组织撰写的《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传主之一。
因敬畏古人,敬畏王勃,敬畏历史文化人物传记写作,遂迟迟不敢命笔《王勃传》。自搜集史料、田野调查,至开笔、至杀青,晃然便是六载:月光下,拾起一枚枚历史碎片,夜深人静时分,聆弦外之音,摩象影之形,艰辛作一番拼风接月的劳作,让远逝的历史氤氲然复活生机,冰冷脉搏跳动温暖与激情……
传记文学,既类别于史学范畴的传记,亦迥异于可以大张旗鼓虚构的文学比如小说。其以花动一山春色的娇美,风景在传记与史学中间过渡地带。
“传记文学”以真实为魂,与“传记”高度默契。因其闪耀历史原真性之光,遂被作为史料引鉴与考量。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的命题我保留警惕的态度。秦汉史就是秦汉史,明清史就是明清史。王勃只能是初唐的王勃,绝非当代的王勃。一百个读者可以心画一百个王勃肖像,但历史的王勃、真相的王勃只有一个,且只能是一个。我注六经,属我之读书心得;六经注我,证我之见,属学术论作;以六经注六经,可谓因史见史,还原历史。
擦亮历史唯物主义的目光,力避拿实用主义的剪刀裁剪作者主观及其时代印迹。传记作者为历史执笔,是历史的眼睛。深入钩沉历史碎片,织成一个历史人物相对完整的世界。刘知几《史通》说:“夫《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又引子夏云:“《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扬雄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春秋》既为经书,亦可谓文学色彩一抹的“传记”。其“春秋笔法”,简言大义,每个句子皆弹性有褒贬之意,遂有“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之阐释。《春秋》《左传》《国语》史耶?传耶?记耶?
“传记文学”本于史实,辅以文学。此处的“文学”拒绝演义与小说。其意义在于,一是焕然可读色彩,二是翼然合理想象。所谓合理想象,即沿着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努力发现事件的可能性,并将可能性真切地呈现出来,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交融的层面,还原并鲜活人物。
培根《论学术的进展》更早在明确将传记学归入史学的同时,满怀期望“传记的写作”,要使人物“获得更加真实、更加自然、更加生动的表现”。“作家不仅仅反映和诠释生活,他们也丰富并且塑造着生活”。亮明这一观点之后,怀特又作深入补充道:“我们只有通过与想象对照或者将它比作想象才能认识事实。”
诚然,合理想象也须节制,不可脱缰牧马。比如王勃“擅杀官奴”一事,史载语焉不详,放飞自己的想象,可以虚构一段故事,而且相信会写得美丽而感人,可是不,我选择了沉默。后来我读到维特根斯坦的话:“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这是尊重与敬畏事物的一种态度。
任何作者都不可能是现场目击者,但必须心灵在场。这颗心灵,承载着历史的目光,承载着无数读者的眼睛,那眼睛像满天星辰,像阔博的海洋。以心灵目击之状,历历在目之述,抵达让读者身临其境的效果彼岸。传记毕竟不是解说词,作者不能扮演讲解员的角色。而复活所传人物,让其穿越时空,走近读者,绽放音容笑貌,是传记文学的金标准。曹丕《典论·论文》:“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文心雕龙·总术》:“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当为所有传记文学作品所悟鉴。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史通》:“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返,百遍无致。”北周·庾信《燕射歌辞·角调曲》:“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义而无立,勤则无成。”词采美韵,是传记文学的性灵。乘着文学的翅膀,传记作品飞栖读者期待的梅枝竹梢。《史记》如“史”道来,“史”情并茂,故有“史家之绝唱”评赞;以诗记史,化史为诗,遂有“无韵之离骚”美誉。
时间是最伟大的读者。王力说过,对于古人,“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语言去了解他的思想;我们不能反过来,先主观地认为他必然有这种思想,从而引出结论说,他既然有这种思想,他这一句话也只能作这种解释了。后一种做法有陷于主观臆测的危险。”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杨逢彬(祖父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堂伯父语言学家杨伯峻)说:“进行任何一种东西研究,不管是数理化也好,总要在系统内部找程序,语言内部的证据是主要的,自足的;语言外部的证据是次要的,非自足的。语言外部的证据决不能作为主要的唯一的证据。”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三不朽”追求。王勃以作品立命,以文章传世,好像是王勃就是为写作而生,王勃就是一支笔,受上帝之托来书写人间奇迹。干脆说,王勃就是一本书,以年为页,薄薄27页写满了神妙与奇美,其创作之丰,令人惊疑,令人叹异。王勃不朽在哪里?就在他的作品中。作品是王勃生命与情感驿动的坐标,是王勃复活的灵魂。本书所有文学“合理想象”,均以王勃作品为蓝本为生发源。沉潜入王勃作品里面,触摸王勃丰富多变的内心世界,千年王子安模糊不清的影子渐渐清晰,声息吐纳的质感层次分明起来。
清末著名学者蒋清翊,春秋十二载,三易其稿,完成王勃别集《王子安集笺注》权威之著,其“笺注”有云:唐燕太公(宰相张说)读到王勃《夫子学堂碑颂》“帝车男指,遁七曜于中阶;华盖西临,藏五云於太甲”,去求教于一行(张遂,僧一行),一行只解释了上句,下句“卒不可悉”。燕太公与一行乃饱学之士,“虽古人不尽知,亦不讳其不知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谦谦君子,治学严谨;胸襟敞亮,若万里山河。《王勃传》虽非严格学术研究文献,却也常在学术湖边漫步,管窥蠡测,浅陋之见,还望读者纠错归正。
(摘自《秋水长天——王勃传》,聂还贵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