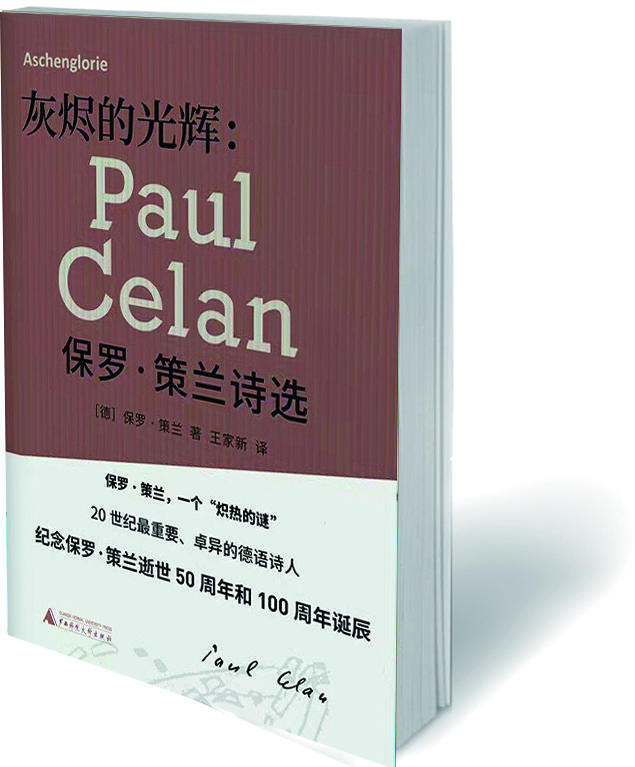在《不来梅文学奖获奖致辞》中,德语犹太诗人保罗·策兰曾抱以这样的希望:“一首诗,是一个语言的例证,因此对话是本质性的,它可以作为一个‘瓶中信’被投向海中,带着一种希望——当然并不总是那么强烈:它可能什么时候被冲到什么地方,也许那正是心灵的陆地。”如今,这些“一路跋涉的嘴巴们”(《白色声音》)终于在诗人诞辰百年之际抵达到汉语的陆地。它的译者、诗人王家新经由30年的倾心翻译,将它们承接在汉语降生的阵痛和光辉之中。这是一个痛苦而卓越的诗魂在另一种诗性语言中的再度生还,带着“船夫”也即一个诗歌摆渡人的“嚓嚓回声”。
《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王家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辑录了诗人360首诗篇,选自诗人一生十余部诗集,并附录有策兰重要文论与书信选。500多页诗文,一页页将黑暗历史间灵魂痛苦的呼吸重又置于我们之间,让我们在“屈身之中”又迎来了那“飘游的光”(“光柱,把我们吹打在一起。/我们忍受着这明亮、疼痛和名字”,《白与轻》)。这无疑是一场生命劫毁后的歌哭、相遇和对话,它发自诗人策兰的心茎,而经由王家新赋予了汉语筋骨般的质地和光泽。它们是奥斯维辛之后“可吟唱的残余”,而又献给了我们这个时代。
保罗·策兰(Paul Celan,1920—1970),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最广泛、重要影响的德语犹太诗人。纳粹占领时期,策兰父母惨死于集中营,他本人也经历了“强光统治”下的苦役和逃亡。1952年,辗转流亡、定居在巴黎的策兰在西德出版诗集《罂粟与记忆》,其中《死亡赋格》一诗在德语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成为具有纪念碑性质的时代之诗”(见王家新“译序”)。
《死亡赋格》自问世以来,一直被人们广泛谈论,“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傍晚喝”到现在仍在到处传诵,正如美国诗人罗伯特·哈斯所说,它是“20世纪最不可磨灭的一首诗”。王家新是第一个策兰作品中译本《保罗·策兰诗文选》(收诗103首,2002年出版)的主要译者,近20年后,在这部新出的策兰诗选中,他不仅对早期所译的《死亡赋格》等诗进行了修订,而且收入了大量策兰早期和后期未曾被译介的诗作,全面而又充分地展现了策兰作为诗人的一生。当然,不仅在于数量之多,王家新倾尽心血的目的,正如策兰翻译曼德尔施塔姆,是“使它存在”——在汉语中永久地存在。
策兰的早期抒情诗以其“超现实主义”式的奇异意象和抒情风格,至今读来依然十分动人,如“她从你的睫毛上梳理出盐,并与你分享,/她从你的时间里听出沙子,然后端在你的面前”(《睡眠和进餐》),如“他用红色的羽毛携来雪花,/喙中含着冰粒,飞越了整个夏天”(《我独自一人》)。但策兰真正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要以他的《死亡赋格》和他在后期进一步的创作发展为标志,王家新的“译序”和他对一部一部诗集的译介,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这种历程。他的翻译让一位来自历史暗夜的诗人在汉语中获得了真切的、甚至是历历在目的“辨认”。
的确,读这部诗选,我们会感到策兰不是那种表面意义上的历史见证人,他深入到了时代最为黑暗的核心和“内在的绞痛”之中,既有发自命运悲切的见证,又以语言的脊骨联结起了历史亡灵的歌哭和跋涉。在他的诗中,无尽深渊的灰烬与喑哑之音,灵魂淬砺的穿越与逼问,每每令人惊异,并为我们展现出何谓“后奥斯维辛的美学尺度”。《罂粟与记忆》之后的诗集《从门槛到门槛》(1955),诗人“躺在直立尸体的阴影间”(《挥动斧头》),他要更为坚决地去除庸饰的诗意化,在词语迸裂的黑暗缝隙中“把这种存在带入语言,被现实压迫并寻找着这现实”(《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在诗集《言语栅栏》(1959)中,我们可以感到诗人更痛切和孤绝的生命体认与领受,感到诗人是怎样由亡灵领路,书写着“无乡的还乡之诗”(见《在下面》译注)。对此,王家新在译序中引用的意大利诗人赞佐托的一段话,说出了我们很多人对策兰诗歌难言的感受:“他把那些似乎不可能的事物描绘得如此真切,不仅是在奥斯维辛之后继续写诗,而且是在它的灰烬中写作,屈从于那绝对的湮灭以抵达到另一种诗歌。策兰以他的力量穿过这些葬身之地,其柔软和坚硬无人可以比拟。”
《无人玫瑰》(1963)为策兰极具转折意义的一部诗集,它可能源于“戈尔事件”的伤害与战后反犹的梦魇现实。这无疑加重了策兰那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同时又激发了他“惊人的语言创造力”,该辑中的《赞美诗》《带着酒和丧失》《呼喝开花》等诗,在上帝的缺席中,策兰不仅朝向了“无人”,还执意于成为德语诗歌中的一个“偏词”,更为绝决地朝向“语言的异乡”。收入该辑最后的长诗《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堪称是一首伟大诗篇,它为策兰在读到茨维塔耶娃诗作后所作,依循于同一“子午线”的命运指向与契合,它是令人惊异的“创伤之展翅”。它以“被践踏的草茎”,以策兰式的融铸了多种语言文化的“混合诗韵”,“写入/时间的心隙”,“写入那/伟大的内韵”。
到了《无人玫瑰》前后,大概就是为王家新所极为重视的策兰的“晚期风格”了。他多年来对策兰的翻译,一直伴随着深入的研究。他对策兰“晚嘴”“晚词”“偏词”的诗学阐发,不仅为我们进入策兰的后期诗歌提供了确切的角度,对于国内诗歌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启示。同时,他也通过《雪的款待》等多篇解读文章,引导一般读者阅读策兰。策兰是一位在语言中攥出血泪的诗人,但他的后期创作对于一般读者,可能会像是一个“炽热的谜”。《无人玫瑰》中的重要诗作《卫墙》,初看上去犹如天书一样难解,但是细读了王家新的翻译及其一条条注释,我们就会感到:“《卫墙》是策兰一生的写照,而又用了一种看上去是高度‘密封’的方式。一道坚固的语言卫墙矗立在那里,既敞开又封闭,自成一个诗的世界。”学者孙郁在《词语书写的另一种标志》中就很称赞王家新对策兰的翻译,他引用了《卫墙》中的这一节诗:
经由克拉科夫
你到达,在安哈尔特——
火车站,
你遇见了一缕烟,
它已来自明天。
策兰早年在柏林安哈尔特遇见的那一缕烟,不仅是纳粹分子疯狂捣毁犹太人商店、焚烧犹太教堂的“水晶之夜”的烟,也来自于更可怕、更不祥的“明天”。读了这样的诗,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王家新称策兰为“先知般的诗人”。孙郁在文章中也惊讶于这种诗的“精确性”,他还这样感叹:“无论在什么时代,这样的存在都是一个异端。逆俗的文本穿越了词林,有了自己的所在。他们用一种本民族难以解释的词语写作的时候,诗才真的诞生了。”
语言的“异质性”、对“语言的异乡”的执意追求,这些也正是王家新翻译的取向和译介策兰的一个重心所在。他拒绝那种庸俗的美文化、抒情化翻译。他不仅要通过翻译从事自我命运的艰辛“辨认”,还要通过策兰的“晚期风格”,为中国诗人和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一种“特殊的成熟性”。他早些年的重头论文《阿多诺与策兰晚期诗歌》已引起诗歌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灰烬的光辉:保罗·策兰诗选》收入的大量策兰后期诗作,将我们更深地引入策兰独异的“晚词”的领域。策兰的这些后期诗作,不仅如阿多诺所说,重构出“从恐怖到沉默的轨道”,还像伽达默尔所描述的那样:“这地形是词的地形……在那里,更深的地层裂开了它的外表”,对现代诗歌的语言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诗集《换气》(1967)是策兰晚期风格形成的标志,显露出夺目而逼人的成熟光辉,据说著名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当年就是因为读到其中的《在这未来北方的河流里》等诗,从而被策兰的诗歌完全吸引住的。这是诗人“呼吸的转换”,是痛苦喂养的生命结晶(“一丛冰刺”),它属于寓居在语言肝脏内的闪电,属于永不可被剥蚀的精神见证。诗集《线太阳群》(1968)更是将诗性冥想的沉思,引向更为陌异化的无人畛域,“无名,就是那名字”,王家新特意将这首《无名》置于该辑之首,让我们看诗人是怎样以“本质的残骸”来迹写生命无言的明灭,“穿过叛逆和腐烂的骨髓/追逐着十二颂歌”(《可以看见》)。而在这之后的几部晚期诗集《光之逼迫》《雪部》《时间家园》,成为策兰生命尽头的最后光亮,“雪部,最后拱起,/在上升的引力里”(《雪部》),诗人“在黑暗的劈砍中”“把自己数进赭石”,以惊人的穿透力进入夜的腹腔呼吸,成为那“视听的残余”和生死灯标的收集者。令人感动的是,诗人又一直坚守他与他的苦难民族、与死去的母亲的神圣“誓约”(“孤单的孩子/在喉咙里带着/虚弱、荒沼的母亲气息”,《什么也没有》),读到诗人生前编定死后出版的《时间家园》中收录的耶路撒冷之诗,我们的耳边又响起了诗人早期名诗《数数杏仁》中的“让我变苦/把我数进杏仁”的声音,这种誓言般的声音伴随了策兰的一生,也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历史回音,用策兰自己的话讲,它把我们带入了“记忆和忠诚的语义学的领域”(《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
无疑,策兰的诗是极其难翻译的。笔者曾听过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的一个讲座,他说策兰的诗对德国人来说也很难懂,他是通过王家新的翻译和解读才进入到策兰的诗的。策兰的诗之所以难懂难译,不仅在于它们如同“骨灰瓮之沙”,如同“秘密纺出的线”,还如同王家新在译序中指出的那样:策兰的德语是一种流亡者的德语、非身份化的德语,它几乎是一种“幽灵般的语言”。策兰的诗是一种非主流化的“偏词”,是一种“接头暗号”般的语言。策兰的诗远远有别于一般的“大屠杀文学”,王家新给策兰的“定位”是“一位突入到现代诗歌最核心地带的诗人”,但又是“语言的生成他者……是占优势的谵妄,是逃离支配体系的魔线”(王家新在译序中引用了哲学家德勒兹的描述)。
像策兰这样的充满了颠覆力、创造力和“语言癫狂”的诗,妙就妙在它无法翻译和难以翻译。令人惊异的也在于王家新的翻译。许多中国诗人和读者都曾为此惊异。首先我们感到,王家新的译文具有高难度的精确性,他的译文不是飘忽的、模糊不清的,而是确凿到位的,如同“在现实的墙上和抗辩上打开一个缺口”。策兰的“诗的见证”,充满生与死的悖论、精神性的奇妙联结。他的诗往往有着令人惊异乃至震悚的意象呈现,这是独属于他的生命心象。王家新的翻译让我们感到一种深切的洞察和辨认,一种诗歌语言的“独一无二性”,比如策兰晚期诗作《马普斯伯里路》中的这一节:
整个
时间庭院围绕着
嵌入的子弹,那毗邻的,在颅侧。
王家新在译注中给出了一个重要说明:“策兰在阅读海德格尔时曾记下‘时间庭院’(Zeithof)这个词”。这一下子带出了诗本身所蕴含的反讽意义,道出了为海德格尔迷人的“哲学行话”所掩盖的恐怖现实。王家新的译语也十分精确:“嵌入”、“毗邻”、“在颅侧”,这也使我们更多地理解了策兰为什么爱用地质学、矿物学、解剖学的词语。
当然,翻译策兰这样一位诗人,如同王家新自己所说,还要求拥有“穿越巴别塔语言变乱的敏锐听力”。读他的一些译作,我们甚至感到译者拥有一双“以细线恰好穿过/歌唱的灰烬针的/金耳”(《你,这从嘴唇采来的》)。似乎他在一步步叩响词语的骨节与声息,逼近那一道道为死亡所收割的生命光影,他不仅“咬准”了原诗的发音,而且让它在汉语中“换气”,于此奇迹般重获了生命的节奏、活力和韵律:
——那时汲井的铰链,和你一起
哗哗在唱,不再是
内陆的合唱队——
那些灯标船也舞蹈而来了,
从远方,从敖德萨。
《港口》
垃圾管道的安魂合唱,如银:
出疹之热
围着墓坑飞奔,飞奔……
《垃圾管道的安魂合唱》
王家新曾称策兰的诗在出神入化之时和“语言的幽灵”结合到了一起,读他这样的译文,我们感到同样如此。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诗人的命运“再次为我们发生”,才能让策兰的诗魂得以“生还”,让逝去的亡灵之嘴于汉语中向我们重又蠕动。至于翻译的“创造性”,其例证在他的译文中也比比皆是,如我们很多读者都已知道的,他是怎样把原诗的“在尊敬之中”译为“在屈身之中”(《安息日》),把原诗的“你躺在巨大的倾听中”译为“你躺在巨大的耳廓中”(《你躺在》),我们认同这种“创造性”,因为它不属于译者的“任性”(王家新恰恰反对这样),而是使策兰成为了策兰。
“一条弓弦/把它的苦痛/张在你们之中”,王家新曾引用策兰《里昂,弓箭手》中的这句诗来谈翻译。也许,这道出了他的翻译的最深奥秘。策兰的诗作尤其是王家新的翻译已对当代众多诗人和读者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在译序中,王家新仍用“结成杏仁的你,只说一半,/依然因抽芽而颤抖”(《结成杏仁的你》)来表露他的心情。对他来说,这是一位需要用一生来阅读的诗人,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与策兰的诗初次相遇,这部策兰诗选是他历尽三十载持续的白发完成,仿佛他在践行一个命定的精神约定(“我把你归还给你,那是/雪白的安慰”,《极地》)。他怀着生命相惜的痛感和炽热的心力燃烧,以源自灵魂深层的密接与呼应,以精湛而力透纸背的译笔,以直抵本质的语言精确性,带给我们永久的震悚之力。
法国著名作家、哲学家齐奥朗称策兰是“一个视词语生死攸关的诗人”。王家新对策兰诗作的持续翻译和锻造,同样让我们感到了这一点。策兰晚期有一首极其感人的《以歌的桅杆驶向大地》,王家新在译序最后引用了这首诗。伽达默尔曾这样解读这首诗:“它从一开始就转变成另外一种事故。它是天国里的船只失事”,而这意味着“所有希望的粉碎”,所以诗人在经历了这样的致命重创之后,转而要“进入这支木头歌里”,并用牙齿“紧紧咬住”,诗人最后对自己说的是:“你是那系紧歌声的/三角旗。”王家新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是怎样的一位诗人!他要系紧的‘歌声’,我们在今天还要尽我们全部的生命去系”——
以歌的桅杆驶向大地
天国的残骸航行。
进入这支木头歌里
你用牙齿紧紧咬住。
你是那系紧歌声的
三角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