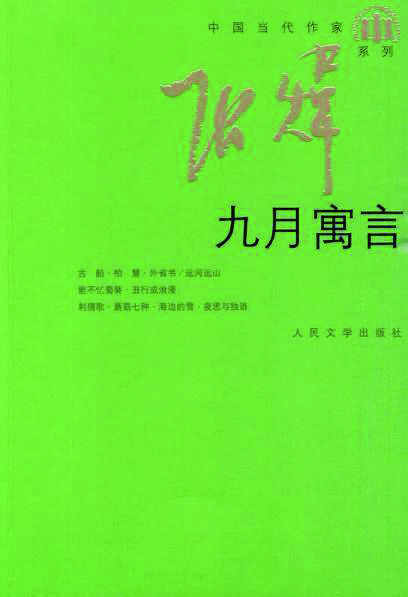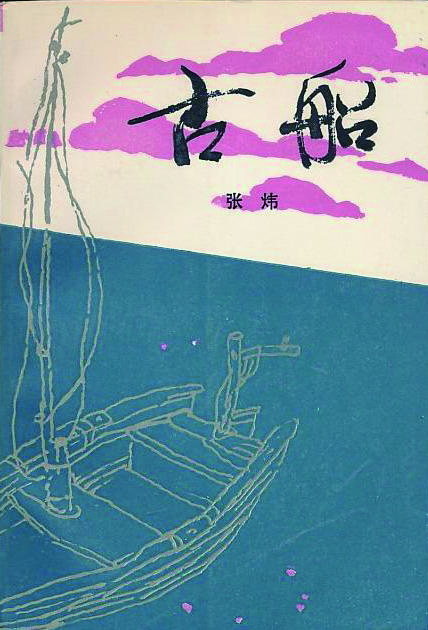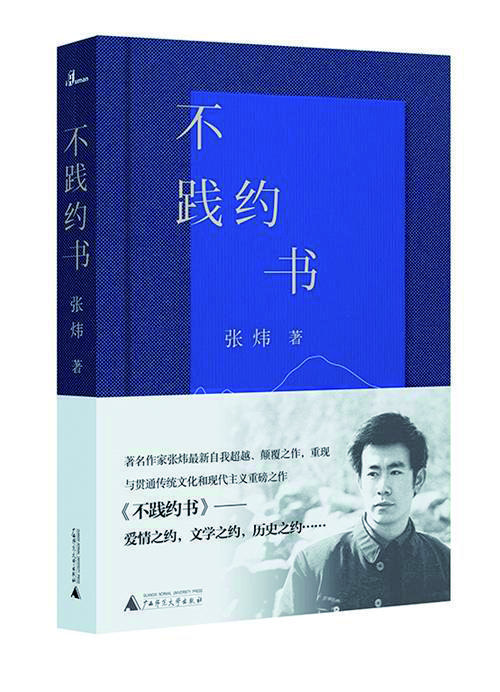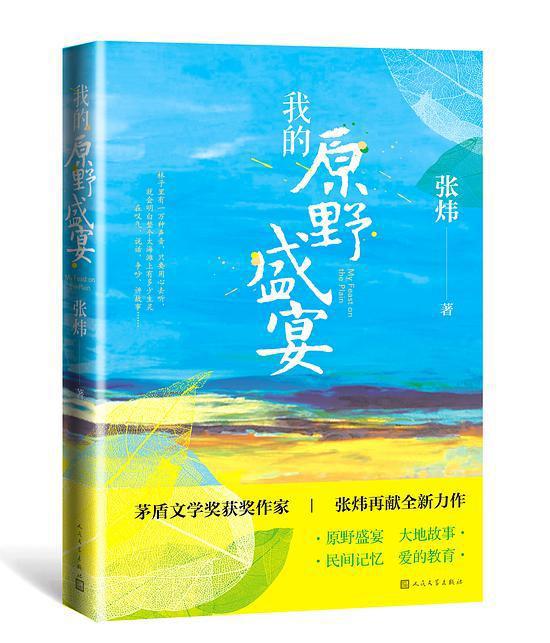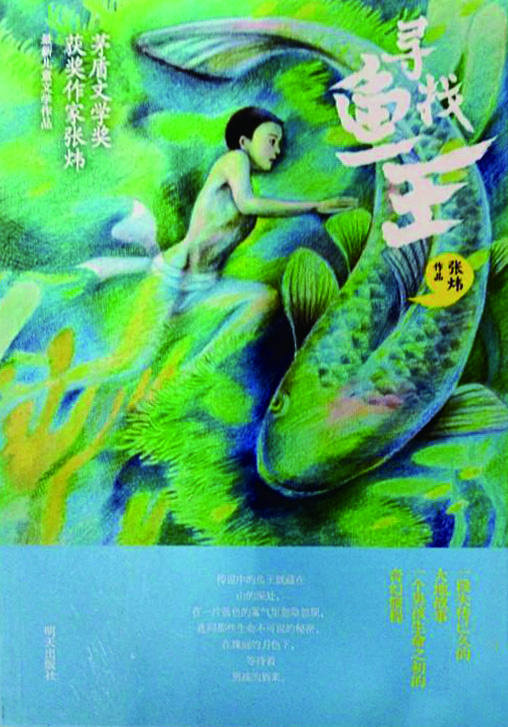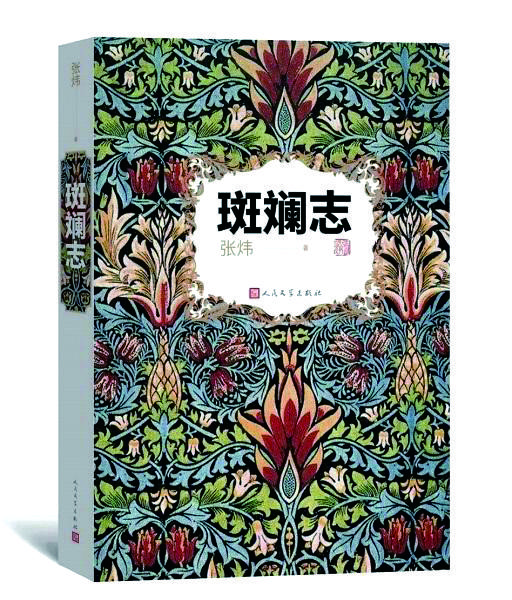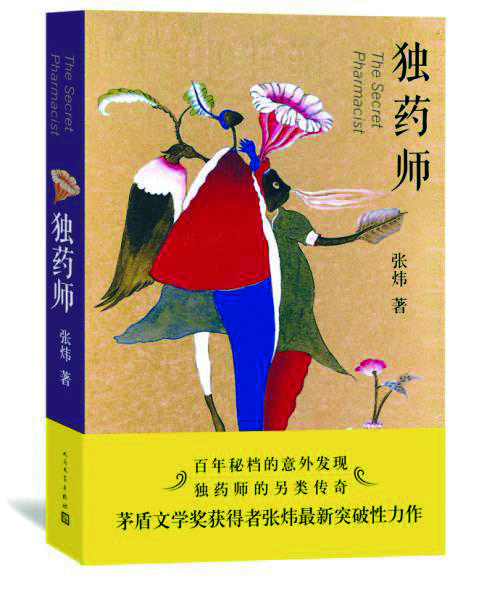赵月斌:张炜老师好,很高兴有机会和您进行这样的对话交流。您不到20岁就开始了小说创作,在新时期文学肇始之际崭露头角,以独具特色的“芦青河”登上了中国文坛,在流派纷呈、思潮跌宕的1980年代留下了浓重一笔。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中,您直接参与了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难能可贵的是,您似乎从来不受所谓文学“行情”的影响,一直保持着持久旺盛的创作势头。从1973年的小说《木头车》至今,您已发表作品2000余万字,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被译成英、德、日、法、韩等多种文字,在海内外出版单行本数百部,并且获奖无数,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重要文学奖项。从创作的“吨位”来看,您无疑是当前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您的创作实绩,就是贯穿了当代文学史的一条生命线。所以首先想请您谈谈,您的创作如何呼应时代变迁?您的作品有在大环境影响下的“变”,又有不变,您是如何处理这种“变”与“不变”的?
张 炜:我的创作其实一直处于艰辛的个人探索中,就这个话题,我曾在北师大的一次对话会上这样说过。回视近50年的创作,我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一再失败的诗人、难以为继的短篇小说尝试者、沉迷很久的长篇小说追求者、陷入枯竭的散文家,却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的儿童文学写作者。”也是在这次总结中,我还说:“从彼时到现时,已经走过了一条很长的路。生活足够艰辛,常有不同风景,有难以预料的崎岖和坎坷。文字生涯终能持续下去,如果说依靠了奖赏和鼓励,还不如说是一个接一个的困境,是设法怎样走出困境。它的耽搁让人喘息,也给人磨练和激发。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只有跋涉者自己才能更深地体味。那时候只有默默地将它磨碎,也不得不独自面对。这大概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困境的出现,对于大多数写作者都是必然的,他或许还应该感谢这困境。
写作者总要面对外部环境的一再变化,而他的文字恰好也在这种对应中表现和确立自己的品质。许久以后,正由于品质上的差异,时间将给予不同的鉴定。一个人的写作是这样,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是这样。就此看,已经走过了近50年的中国新时期文学,现在人们当然可以给出一些评判。我想说,这50年的文学既非一直向上,也绝不是一路颓败,而是在坎坷曲折中自然而然地向前。一个人和一个群体的道理相似,遭遇的困境越多,就越有可能退却或停顿,然后再出发。近50年里,疲惫不断地折磨生气勃勃的创造,好在其中的一些人仍旧没有屈服,他们还在坚持和坚守。某些个体在这个时期的超越,秉持的勇气和信念,才是最可期待的希望,这也许比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健硕和生猛的气象,更值得欣慰也更有说服力。
大自然的永恒性是不自觉中表露出来的,它在当时和以后将极大地援助我
赵月斌:您成名于1980年代初期。在新时期文学发轫之际,甫一出手就发表了《芦青河边》《声音》《拉拉谷》《一潭清水》等一系列格调清奇、立意深远的中短篇小说。评论家宋遂良在您的首部小说集《芦青河告诉我》的序言里写道:“初涉文坛的张炜不迎合时尚,也不追求重大题材,他铺开一张白纸,写出的是自己熟悉的动过感情的生活,描绘的是一个美好而多情的世界。”可以说,您一落笔就找准了写作的源头,后来更是从芦青河扬帆启航,开创了恢弘壮阔的文学地理空间。您是怎样创造“芦青河”的?当时有没有一个宏大的构想?后来又是如何拓展的?
张 炜:我出生在海边林子里,那里有一条河奔向大海,成为我生活中最难忘的一道印迹。我写它是自然而然的,最初没有什么宏大的构想,不过是一场慢慢展开的少年回忆。我写作中的时代局限也很明显,早期作品中有不少幼稚可笑的“火药味”,如1974年的中篇小说《狮子崖》等。我的生活环境比较有色彩,如大海和林子等。我也只能写这些场所和经历,所以其外部色彩就多少冲淡了一点当时的社会内容。大自然的永恒性是不自觉中表露出来的,它在当时和以后将极大地援助我。
我还得益于少年时代的阅读,因为当年除了读一些流行的阶级斗争小说,也还能在地下渠道得到一部分名著,它们的笔调是那样不同,这深深地诱惑和影响了我。随着社会进程的改变,终于迎来了思想解放,对外窗口一点点打开,当代文学的风格和内容都在丰富,自己笔下的那条河也就不断地拓宽。它似乎不再是原来林中的那条河了,而更像北方的某条大河,是一些河流的通称。这就自由了许多。
赵月斌:在您的文学地理中,“海边丛林”和“葡萄园”也很有辨识度,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葡萄园》《海边的风》《金米》等作品都是在这样的叙事背景中展开的。我特别看重《蘑菇七种》这部常常被人忽略的作品,这部用时半年写出的最长中篇,不但容量接近长篇,而且是您在写作上由“史诗”向“民间”过渡的重要“中间物”,所以这部小说不仅蕴藏了作家独有的文学酵母,还充分展现了您的叙事智慧和文体风格,完全可以看成您最具核心意义的代表作。您曾说过《蘑菇七种》可能是您最好的作品之一,现在去看它的写作是不是也有某种不可多得的机缘?《蘑菇七种》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的?如果现在去续写它的后传,您会怎样安排丛林中人和生灵的命运?
张 炜:《蘑菇七种》产生于自己最好的写作状态和生活状态。人这一生可能并无太多这样的机遇,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写作者的境界和技能,当然会决定作品的高下,但写作时具有的生命状态更重要。一个经验越来越丰富的作家并不能保证自己写得越来越好,因为他的生命状态不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就此来讲,这部中篇是时光给予我的一个恩惠,我对此不敢有过多的奢望和贪婪。类似的情形还有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和《丑行或浪漫》。那真是我过的一些好日子,这里指的是文学的日子。
我曾几次想要续写那一类生活场景,恢复那种蓬蓬勃勃的生气和烂漫的意趣,但最终没能成篇。这不是愿意与否的问题,而是时过境迁了,视点偏移了,心绪改变了。这时候只能产生另一些篇章。
赵月斌:截至目前您已出版长篇小说20余部,很多作品一经推出就成为长销不衰的文本,尤其像《古船》《九月寓言》,更是被翻译成十余种文字,还被国外大学列入推荐教材,出版了100多个版本,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大。《你在高原》这样的大部头也是一再重印。再如《外省书》《刺猬歌》《独药师》《艾约堡秘史》等等,每一部都让人眼前一亮,赢得了广泛关注。当然,谈到您的作品,大概每个读者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排行榜,有的作品看似不温不火,也可能拥有不少知音。据我所知,《丑行或浪漫》就是一部稍显冷门却又被不少专业读者叫好的作品。有人就认为它写出了生气勃勃的大地诗篇——主人公刘蜜蜡就像一位奔跑的女神。实际上,这部作品在当时男性视角几乎一统天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实属另类,因为刘蜜蜡不仅是小说的“女一号”,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大女主”——您塑造出了男权重负下作为女性人物的“这一个”。
张 炜:前边说过,这一部长篇(《丑行或浪漫》)同样是时光对我的恩惠。我常常想,如果我还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该有多好。很难了,那段时光已经像水一样流过去。我正在往前走,需要经历一段新旅途,但最新的却不一定是最好的。离我最近的长篇小说《独药师》《艾约堡秘史》,读者和业内给予诸多鼓励,也确为自己全力以赴之作,综合了几十年的文学与生活经验,其笔力绝非20多年前所能拥有。但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另一种气质和境界了。总之作品之间得失互见,不好简单类比。
赵月斌:我注意到刘蜜蜡和《刺猬歌》中的刺猬女、《艾约堡秘史》中的“蛹儿”的名字都与小动物有点关系,她们身上似乎都有一种反物化、反异化的天性和诗性,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有没有相关原型?歌德说“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您对刘蜜蜡们是不是也寄予了类似的情感和期许?
张 炜:这些书中的一些女性主人公,常常与动物有多多少少的关系。在一些天生多情率真的人那里,女性应该意味着更多的美好,像大作家曹雪芹作品中的名言:“女子是水做的”,就包含了对清纯的向往和赞美。就一个人来说,过于天真不利于现实中的生存,但对于文学写作而言却是一种优势。这种优势,会从一个年轻作家身上更多地显示出来,所以才会写出很多美好的女子形象。我的童年既孤单又喧哗,那时候动物们帮了我一个大忙,我接触它们最多,后来发现,少年时代比我认识动物更多、对它们的奥秘知道得更多的人并不多见。这成为我知识和情感的双重贮备,也在以后给予我不可估量的助力。事实上真的是这样,我把动物的一些不可言喻的美,乃至于性格,都赋予了笔下的女性人物。
动物没有伤害过我,它们有趣且更可信赖,也极美。野生动物在林子里多到数不胜数,大多是小动物,也包括昆虫和鸟类。我那时甚至能从小蚂蚱的眼睛里看出表情,想象它们的柔善。其他动物如一只鸟和一条狗一只猫,其神色已经接近人了,喜怒哀乐十分明显。
动物的眼睛很丰富也很美,而且主要是新奇不凡,可以读出无限的内容。女子生命中某些动物属性是美好的,这主要指她们的浪漫和单纯。比较男子,女子幻想和浪漫的气质总是更重一些,这些都很“文学”。有人会说女子也是各种各样的,当然是的;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赵月斌:在您的文集中散文作品大概占据了将近一半。无论是写实抒情还是考究思辨,“散文家”张炜更具态度,更显激情,也更为旷达深邃。无论是短章集束、系列讲章还是思想随笔、学术文论,集结在一起就像一部长长的出航志,既有其体系化的成熟通透,又不失其灵动形象,举重若轻。单说您的“古典五书”,从早年的《楚辞笔记》到近期的《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读诗经》《斑斓志》,就充分展示了您的诗学修为。您选择的阐释对象可以说都是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中的庞然大物,曾被无数人研究、固化,似乎很难出新,您为何要选择这种难啃的硬骨头?您最近出版的《斑斓志》是对苏轼的解读,与屈原、李杜、陶渊明比起来,苏东坡大概更像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您觉得跟谁更亲近些?
张 炜:我常常认为,也许自己的主要文字不是小说,而应该是诗,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广义的散文。我不太情愿做一个专业的小说家,这个身份无论多么好都不合本愿。我从一开始从事写作就是这样的认识,认为小说太靠近娱乐了,太依赖故事了。尽管后来小说的地位已经上升得比较高了,比如梁启超将它定位于一个民族性格最重要的塑造者,重要到关乎国家的未来。但我们也注意到,梁的界定虽然成为不刊之论,却毕竟是从事物功用的立场上谈的,而不是从精神品格的意义上谈的。就精神与人生的高贵追求来说,小说仍然有落魄气和末流气。诗最高,关于自然大地的言说也很高。
小说除了娱乐功能太强,还有进入商业时代之后的商品属性太强。我虽在心里疏远小说,却一直未能免俗,甚至就自己的几种体裁来说,小说的写作量和影响较其他更大一些。这就有些尴尬了。不过我深知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小说高超的蕴含和表达是多么令人神迷;另外,现代主义小说的边界已经大大不同于传统小说。就此来讲,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通常在文学性上很难足斤足两,所以凡优秀作品一定要具备当代文学的先锋性,当然不包括“伪先锋”。这也是我最终未能放弃小说的一个原因。
我对于古典的解读大致局限于诗的领域,就出于如上的认识。我面对古代大经的态度也说明了这些想法,认为诗人们才是了不起的。尽管中国古典诗作中的一大部分不属于现代诗的范畴,它们仍停留在言说和叙述的层面上,但这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代表作,最优秀者已经是纯诗了,比如诗经中的一些篇什,比如屈原和李白、杜甫,比如李商隐等。真正的诗,狭义的诗,其实是最接近于音乐的。我们在古诗学方面曾经有过一些不靠谱的论定,比如把某些诗人一个时段的代言或叙事作品,视为最了不起的“现实主义杰作”,可能就是诗学的误识。这严格来讲并不是最好的诗,也不能算诗史的代表,而是富于诗意的有韵文字。“诗意”与“诗”还不是同一种东西。“诗意”浓烈到一定程度,并赋予相应的形式,才会变成“诗”。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将“诗意”与“诗”混为一谈,这是审美和精神格局上的缺陷。
在一些古代诗人中,就人生的意象和境界来看,我最喜欢的还是陶渊明。他的农耕生活除了最后的穷困潦倒,总能深深地吸引我。他的酒和菊多么迷人,他的吟哦多么迷人。我们做一个陶渊明并取其畅悦的理想的一面,是多么好的人生设计,可惜这不过是一厢情愿。
我常常警惕和告诫自己,不要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蹑手蹑脚,尤其不要画地为牢
赵月斌:您还创作了大量老幼咸宜的少儿题材作品,比如《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寻找鱼王》等等。您自小长在“莽野林子”,生就了对大自然、小生灵的“爱力”,拥有了不变的童心、诗心。您作品的主要背景都是海边丛林,童年记忆也常会不知不觉地映现于笔端,而这些以“海边童话”行世的作品,无论是早期自传性的《远河远山》,还是奇幻玄妙的《海边妖怪小记》《兔子作家》,及至最近的非虚构作品《我的原野盛宴》,都是荒野记忆的真诚再现,是当年的林中赤子以近乎通灵的方式“重获童年”。有评论家说“回忆就是一种想象力”,您之所以能够“重获童年”,大概也得力于丰富的想象力。您是如何抵达一种“想象的真实”?如何像波德莱尔说的那样“凭记忆作画”?您的儿童文学作品并不是那种专写给小孩看的狭义的“童话”,《我的原野盛宴》甚至带有“神话”的维度,打通了“文学—童话—神话”的壁垒,那么,您又是如何超越童话边界,让它拥有了无限生长的可能?
张 炜:在最初开始写作的年纪,我甚至认为文学就是讲给孩子听的故事,或者主要是讲给他们听的。这当然是狭隘偏颇的认识。这一方面因为自小接受的文学熏陶,即看了大量的少儿作品;另一方面也说明儿童文学自身的纯粹性实在吸引了我。在我后来的其他作品中,包括那些复杂的长篇小说里,也有浓烈的儿童文学气息,如视角、人物构设、笔调等等。就体裁来说,我也一直没有离开儿童文学的写作,自上世纪70年代初至今都是如此。
作为一个写作者,在各类题材和体裁中自由穿行才是正常的,最好不必做某种专门家,那不是创造的自然。如果将不同的文学品类视为“内部食堂”,也是很可笑的。文学就是文学,它就像完整的生命体不能分割和肢解一样。至于一个人可以将什么表达得更好,则是另一回事。
充分考虑到不同年龄段的接受特征,以及审美差异,这应该属于写作者的基本能力。调动各种文学手段创造出一部理想的作品,这种企图心是不言而喻的。过分清晰地划分和界定儿童文学与非儿童文学,包括手法上的区别,也许是有害的。其实儿童文学的本质属性是更加靠近诗意和浪漫的,这正是所有好的文学向往的境界。我常常警惕和告诫自己,不要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变得蹑手蹑脚,尤其不要画地为牢,而要尽可能地广纳博采,让想象飞翔起来,让诗心舒展开来,运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和技能。但我做得并不好,从来没有令自己特别满意过。
写作者如果在本质上不是一个诗人,就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作家
赵月斌:您的语言雅致考究而又朴实生动,追求诗性亦不避方言俗语,这让您的文本大气厚重却不乏晓畅轻逸。不仅如此,在您以小说家、文章家名世的时候,其实还是一位妙手赋诗篇的诗人。不仅是因为您14岁就尝试作诗,最早发表的作品也是一首长诗,而且确实从未中断写诗,在50卷文集中,就包含了《皈依之路》《家住万松浦》等多部诗集。在前几年写出的长诗《归旅记》中,我们能遇到很多独属于登州海角的文学意象,也能看到您所眷恋的文化盛宴和精神先驱。最近您又出版了一部长诗《不践约书》,这部书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完成的,疫情肯定影响了您的思考和写作,您认为最大影响是什么?《不践约书》被您称为“心约之作”,是“饮过六十年的浊酒和粗劣的老砖茶”之后的心灵之约,此“约”或许就是半生的求索和记挂,这部长诗与《归旅记》有无关联?如果说它也是一位诗人作家对纷纭时代的正面回应,您觉得这个回应的重心应是什么?面对这个非诗的世界,一个写作者应该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如何战胜阿多诺所说的写诗之野蛮?
张 炜:生活的日益物质化,更有实际运行中的庸常化和世俗化,让人类与诗境越来越隔膜。也正是因为如此,诗和诗人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人类沿着彻底物化的方向愈走愈远,将是走向黑暗的一种悲哀,甚至会产生恐惧。精神的飞升,不绝的想象,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因素。思想紧紧缠绕于物质当然是可怕的,这将使我们陷入一次又一次的绝望。我们讲得最多的“精神文明”,其核心内容、主旨,其实不过是追求诗性的不断粹炼。
我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从未停止过诗的写作和探索,前后出版过多部诗集。如此勤勉和努力,仍然让自己大不满意,说明写诗太难了。但是再难也要把握瞬息万变的、微妙的诗意,用自己的诗螺丝把它固定住。我十分警惕诗路上的语言游戏,害怕演变成皇帝的新衣。因为一个操练了近50年文字的人,游戏文字当然不难,但一定是可悲的。我说过,自己对诗总是抱有一份庄敬的心情,这源于对文学本身的认知,而非其他。写作者如果在本质上不是一个诗人,就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作家。
《归旅记》是以前稍有分量的一部诗章,但我并不满意。《不践约书》可能是到现在为止,自己写得最用心力和最有深意的一部。它在疫情期沉闷和焦虑的时光中进行,当然是增加了色泽。我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做中国古诗学探究,这让我在现代自由诗的创作中获得了一份援助。
赵月斌:在此还想请您回顾一个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即19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当时一大批知识分子围绕人文精神的失落和重建展开了激烈交锋。您虽未直接参与正面的论战,却被冠以“道德理想主义”的代言人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即所谓“二张”(张炜、张承志)和“二王”(王蒙、王朔)之争。这场持续了两年的全国性大讨论虽只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精神阵痛,但对一个要为世道人心立言的作家来说,无疑会造成深刻的心理印记,现在去看当时的争论,其意义何在?还有那个“道德理想主义”的标签,现在看显然只是一种简单的以偏概全,您对此有何看法?当前许多作家感到一种表达的无力,同时也有一种表现的乏力,文学的力量似乎在不断削弱,您有没有这种困惑?一个作家又该如何突破时代的局限,在文字中抵抗流俗的惯性,在沉默的表达中抵达永恒?
张 炜:这场已经过去的大讨论对我是重要的,大概对整个文化界也绝非可有可无。我们现在回头去看,会找出这个文化事件中各种各样的不足甚至荒谬,但最好还是不要急于否定它。比如对我个人来说,自己不仅不是直接的参加者,而且还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简单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标签,让一些根本不读书的人造成了极大的误解。他们望文生义望词生义,或赞赏或批判,动辄“二元对立”、“道德理想”,真是“夫复何言”。在作家这里,不要说做一个直面人性与生活的勇者,即便是一个稍有觉悟和水准的写作者,要傻到什么程度才能让自己变得那么“二元”和“道德”?细读文本否?有人认为认真阅读评说对象并不重要,因为那样既很累又很麻烦。
那场讨论是一次冷静和追问。它实际上一直在进行中,所有醒着的人,更不要说写作者了,都终究不能得过且过,也不愿变成糊涂一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