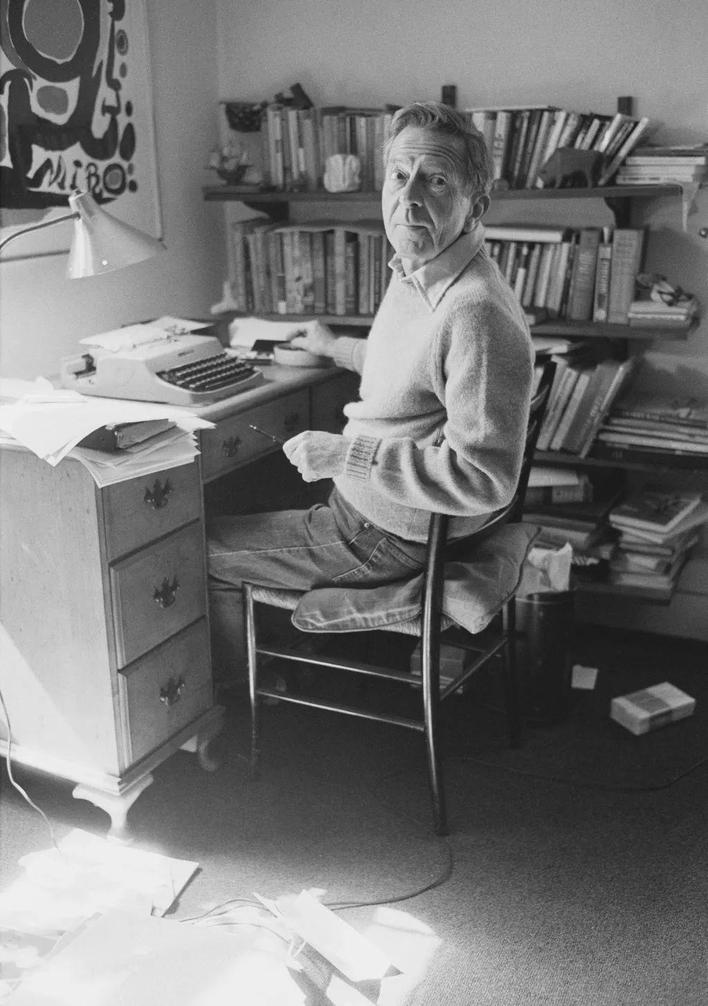《欢迎来到弹园村》也许是约翰·契弗颇为怪异、“难以理喻”的作品。但正如《纽约时报》所言:也是“契弗最深厚、最有挑战性的一本书。”这句评价没有假谦虚、装客套,它用了最高级形容,并没有加上“之一”。《纽约客》大作家、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并不缺这种赞誉,但它却给我们一个提醒:以往,契弗可能迷恋熟悉感,习惯在舒适区发挥,鲜有陌生的冒险。深厚与挑战从何而来?不在于这部长篇的题材(它仍是社区中产家庭日常纪事),根源则是叙事逻辑、心理推动及精神状态,一反常态。作家用混乱与崩溃构制人物病态生存的心理因、逻辑因。切近精神疾患叙事立场、视角,需要强大的共情同理,去理解反常。
这对阅读也是挑战,它产生错觉:到底是叙事者,还是作家的叙事有了异动?小说分为三部分,大约应了“正反合”的三段式结构,但细看又不如此。契弗大胆转换了叙事者,从一个统摄全知的第三人称,变为第一人称自述,最终重返第三人称的局外。俨然,小说成了契弗与人物哈默在争夺、让渡叙事权。这种设计大有功效。当哈默走向精神崩溃,他的自述更能演绎什么叫做“病态的常态”与“反常的正常”。这就类似一个酒鬼在说“我没醉”,反而更具现实感。以哈默为镜像,参校周围人,则他们都有病症的间歇式发作。他所关联的是精神疾患的“世界”。
内尔斯药物滥用成瘾,与哈默酗酒相对应;托尼的“单核细胞增多症”,不过是“抑郁症”的另一别名。哈默既复刻了内尔斯父子的精神困境,又“承受”着父母造成的记忆创伤。他为父亲充当模特而羞耻,看到各式建筑以父亲形象为柱头,深感痛苦。母亲的偷窃癖,靠做梦猜测房间入住者的疯话,也难以忍受。私生子的身份焦虑,被放逐的不幸,是哈默抑郁的根源。这与托尼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倒”。内尔斯对儿子近乎禁锢的爱,尼莉对儿子被寡妇引诱失贞,施加的精神审判,是托尼瘫倒无力的诱因。情感真空与情感窒息皆通往崩溃,小说写出了家庭关系的正反两极。
哈默与内尔斯,在姓氏谐音上(锤子和钉子),天然绑在一起。“多糟糕的组合啊,锤子家和钉子家!”他们成了一个玩笑,一种颠倒,是精神映像的倒置。从这一隐喻看,哈默最终杀人未遂,显得颇有暗示。它不止受到疯母亲想杀人献祭,唤醒世人的灵感,更有以自毁换解脱的动机。内尔斯父子有哈默的影子,锤子哪有不敲钉子的道理。契弗并没有孤立对个体进行剖析,而是在家庭关系、社区环境里审视人的变异。婚姻、性欲、教育是小说内置的几种观察变量。作家始终围绕“夫妇们”这个集合体。换言之,夫妻相互限定出生活模式。
“瑞德利夫妇进入神圣婚姻殿堂时,带着明确的商业色彩,仿佛双方结婚、怀孕、生养和教育,都是在生产和经销某种有用的产品,并和别的产商在竞争……给人的感觉,是他俩一定合伙成立了什么股份公司,还在柜台售卖他们命运的股份。”这或许是重商主义的遗产。我们仿佛看到无比贴切的当下现实。无数家庭都在这种“竞演”模式下,惨淡经营。原本物质的生产性、效率观念,被滥用到情感层面上。“他们把自己漂亮的孩子展示给客人看,那样子就像销售员在展示厅给人介绍某款新车的优点。平常婚姻中常有的私欲、悲伤、自得,以及鸡毛蒜皮的操心,似乎都未曾影响他们这个组织的效率。”
“维克维尔夫妇的星期一早晨没什么虚伪可言。”这也是有趣限定,在这个特殊时段,虚伪被性活动的赤裸状态延缓和搁浅。做爱需要勤恳,身体召唤诚实。“他滚到她的那一侧,两人开始勤勤恳恳地做起爱的功课来,一做就是20分钟,末了两个人的头都炸裂一般疼痛。他已经错过了8:11、8:22和8:30三班车。”契弗像是拿着钟表,靠计时来写性,如同一位医生的诊断报告。内尔斯夫妇则说明婚姻与性欲的分裂与错配。“在生儿育女方面,她觉得他已经过期作废了,可是性欲之痒不见消退,都会当着她的面抓这痒。”
性压抑假说,是小说潜藏的内在驱动。作家忍耐不住以性意识阐释生活的症结、人物的行动。生活充斥着游弋的、闪退的禁忌幻想。浓烈的精神分析趣味让作品带有心理小说色彩。在我看来,它可以归纳为:一种焦虑(贞洁与不洁)、一种分裂(放荡与禁欲)、一种伪饰(造成痛苦与崩溃)。内尔斯夫妇对宗教的虔敬、道德的洁癖,与他们的性压抑成正相关。尼莉观看戏剧,被演员的色情举止震惊。“她的廉耻心和易激动的本性轮番上阵,搅得她情绪迸发,浑身出汗。然而,她要“继续做她的尼莉·内尔斯或曰艾略特·内尔斯夫人,诚实,负责,聪明,贞洁,等等”。她的镇定,要靠回家关上门才能恢复。
同样,哈默在偏执寻找缓解抑郁的“安全屋”——刷有黄色墙壁的房子。只有依赖空间幻想的催眠术,才会起到情感暗示功能。“觉得过去这里没有发生过任何坏事,未来也不会发生。这种健康、圣洁的感觉,在我的经验之中,任何教会都没有产生过。”当他找到同样缺失父母的玛丽埃塔,又陷入爱的荒漠。“我的错误,在于我把爱情想成了一种令人眩晕的怀旧提取物,一种无法用神经机械学分析的记忆之力。我觉得,我们不会坠入爱河,我们只是重回爱河,我只是和记忆相爱。”
契弗把羞耻与负罪、放荡与净化、缺失与代偿的病理逻辑,通用并化约,形成了整套故事系统、人物序列。甚至它构成一种分析的目光、解释的方法论。玛丽埃塔在温和环境中,暴躁、易怒且冷淡;在恶劣、狂暴和动乱中,反而柔情蜜意。在内尔斯看来,“这女子优雅可人,一定是那非凡而长远的神圣婚姻给滋润出来的……她所有的角色肯定都扮演得很好——热忱、聪明、睿智、有爱心。婚姻似乎是给她这种人设计的;事实上,搞不好婚姻制度就是她这样的人插手设立的。”这当然是反讽,扮演伪饰,内外撕裂,徒有其表。
小说以“家庭批判”作为基础单元,延展到社会分析与症候观察的系统批判——对整套生活模式的质疑。与菲茨杰拉德这类醉心“美国梦”的作家不同,契弗不经意流露出对“美国病”的厌恶。他借人物之口对美国社会直接攻击,其力度是鲜有的。“如果美国资本主义继续抬举那些唯利是图的奸诈小人,整个经济会堕落,只能生产麻醉品和腐朽的生活方式,让一切反省——任何深度思考和情感——都变得不可能。”“我在咖啡馆看到美国杂志,大部分文字都是在给烟草、酒精和荒谬的汽车打广告……能让你忘记肮脏污秽,精神贫困和自私单调。在文明史上,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伟大的国家这般一心一意地在麻醉自己。”
当哈默随房产中介进入弹园村,“他们路过了豪斯顿家(7卧,5卫,65000美元)和韦尔奇家(3卧,1.5卫,31000美元)。”作家以数字化表象,取代可视化形象。小区本质不过是房产集合,家庭不过是一堆冰冷数据。这或许暗示,现代性背后是生产与消费的双重逻辑。一方面,它不断生产“空心人”(丧失情感灵韵向度);另一面,一切都是买卖关系。现代性批判就寄寓在闲笔里,漫不经心,入骨三分。契弗虽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却能透彻洞察,懂得用描摹叙事,实现批判的深度。
这无疑是一种自下而上归纳法的策略:看重日常、琐事、平庸背后的结构性力量。折射于语言情绪上,成就了一种轻描淡写,稀释简约的幽默,让人既不至于大笑,又生出些许自怜。反之,戏剧化、对峙性和观念冲突,并不属于契弗。回到小说提出的疑问:“弹园村这么多年轻人,为什么偏偏挑选托尼患上神秘的怪病?”这一病灶,就位于原生家庭、校园社会等背景中。换言之,精神疾患从不只是自然之物,它是矫治和压抑的副产品。
小说用“三次戒断”挖掘了规训的毒副作用。托尼电视成瘾,法语成绩差,和年轻寡妇过夜,算是三次“事件”。对应的三种解决方法却出奇地一致:父亲内尔斯扔掉电视,校长和女教师要求托尼放弃橄榄球,母亲尼莉用道德审判了托尼。这是反复与累加,既是人物压力的叠加,更是艺术效能之聚合。“打断”与“纠正”是造成病症的两种契因。它意味自我意识的连续性,主体性与同一性被粗暴破坏。如同强制纠正一个左撇子,打断一个梦游者,会造成严重后果。
《欢迎来到弹园村》显示契弗以短篇手法运筹长篇的惯性,它更像两部中篇的复合对话,两个中心家庭的参差对照。第二部中,哈默追述自己的身世,对父母、祖母进行印象式速写。虽然与第一部的内尔斯家庭琐事断了篇,却依然连着气。这种潜在统一如何可能?事实上,哈默的成长自述具备一种对折性的阐释功能。一方面,他在回应托尼的精神困厄;另一面,哈默父母与内尔斯夫妇又相反相成。他们都不懂父母的“功能”,区别只是后者仍在维系家庭框架,前者则根本放弃了拙劣表演。
让人纳罕的是,小说如何从现实主义一度滑向荒诞主义?在我看来,既然有“魔幻现实”的提法,那么,荒诞现实主义也未尝不可。它将现实主义奠基在荒诞的地表上,既非纯粹怪诞,亦非单纯写实,而是挖掘现实中“被压抑的”混乱、沮丧与非理性。作家一举囊括了各式精神疾患,甚至故事成了病例的汇演。哈默的酗酒、抑郁,内尔斯的强迫症,日益加深的暴露与恋腿癖……但契弗都按发展心理学的观念给出了成因、动机的线索。在持续的精神诊疗中,他终于完成了困难重重的叙事。他不只是个好作家,也是一个“治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