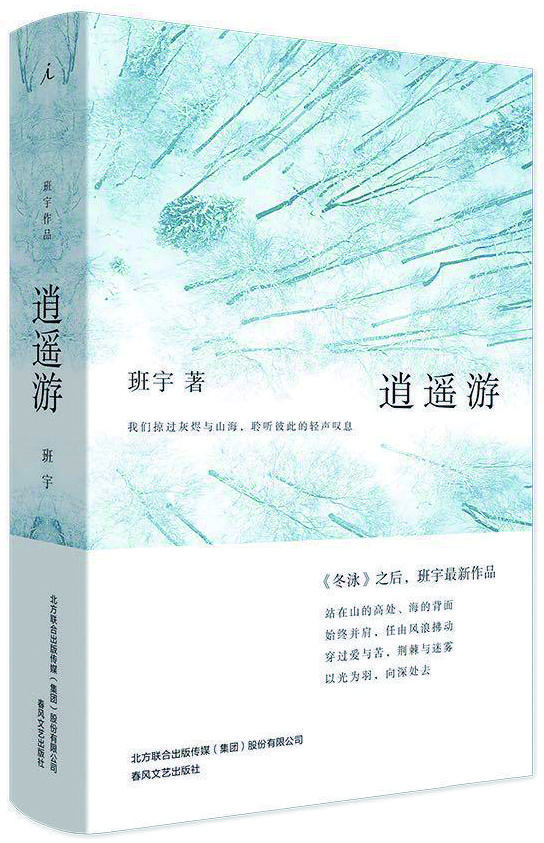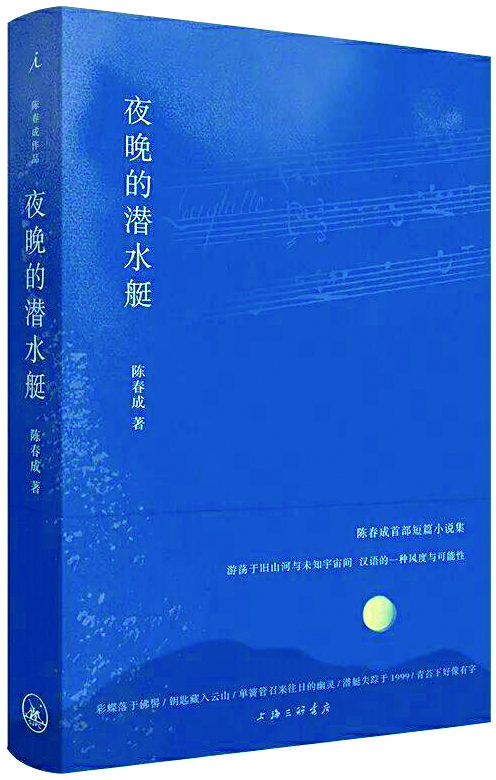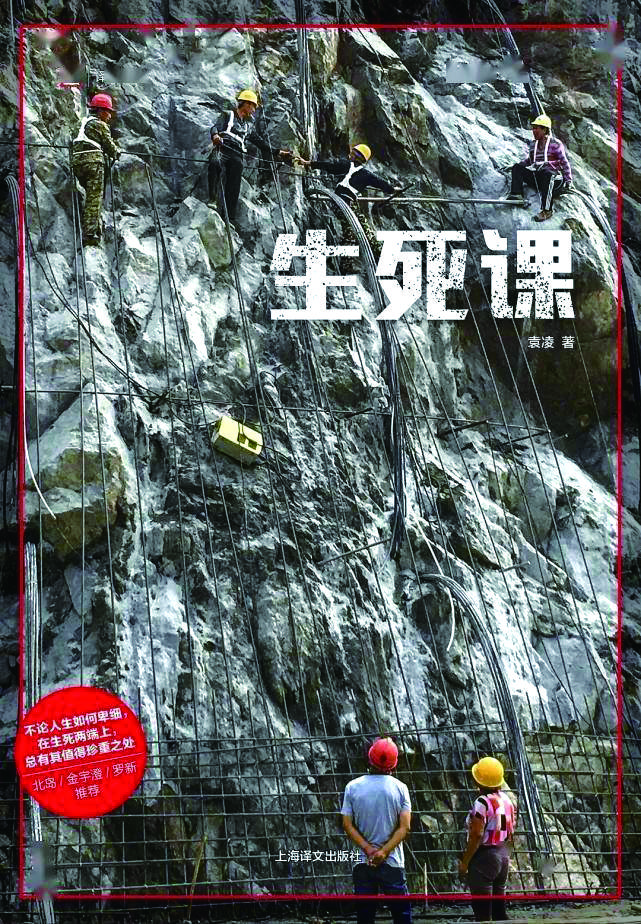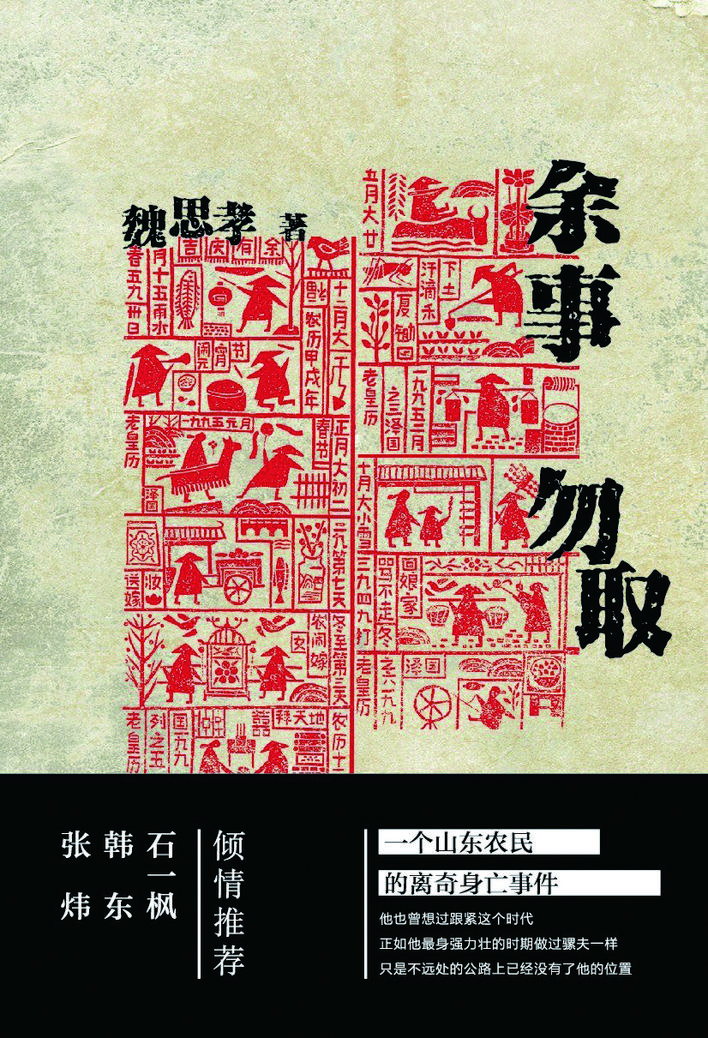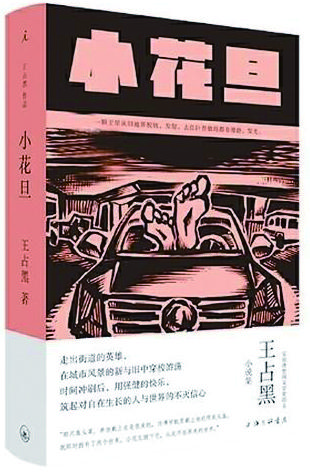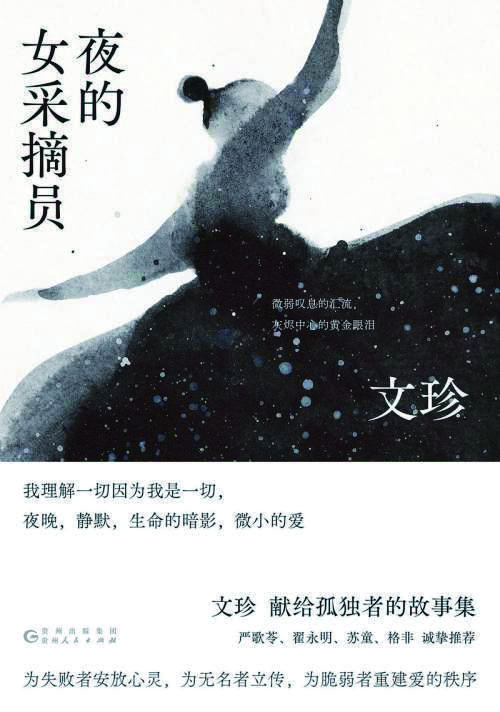我们离开了2020年,它仍将以那副前所未有的面孔长久凝望着我们。在这一年的摇撼及余波中审视青年人的创作,无时无刻不想到他们与世界的关系。
2020年,青年创作者依旧站在各自不同的维度上,试图理解和判断世界。尽管在这样的一年里,这种努力显得有些天真而不切实际。他们的方法和结论不一定尽善尽美,却也为我们拨开了世界的某一重褶皱,露出那些不为人知的所在。
一
陈春成的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在这一年浮出水面,是一个惊喜。集子里收录的9部中短篇小说,多数没有正式发表过。它们像一组奇异的水下装置,精密、繁复,经过了重重打磨和试验。这些小说大多具有一个“中国套盒”或“俄罗斯套娃”的结构,这当然不是新鲜事了,陈春成的贡献在于,他把这些装置的内核推向了一种宗教式的崇高,当层层嵌套的故事剥离,留下的是关于存在与虚无的辩证。
小说里随处可见一个狂热的、古怪的“朝圣者”。他们有的要酿出世间最好的酒,即便能让人忘却烦恼或者返老还童,也还不够;有的要铸一把剑,剑身需要九千个夜晚熬出来的汁液淬炼;有的崇拜博尔赫斯,甚至于要找到他的诗里写到的一枚落入海洋的硬币……而当酒酿成之时,这是一种无色无味,失去了存在也能抹去任何存在的酒;当剑铸成之时,它所穿过的任何事物都完好如初,又很快不知所踪;反而是那枚不一定存在也不可能找到的硬币,某一天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海滩上。小说在以具象化的方式向我们演示“有”和“无”、“色”与“空”之间的悖谬。《〈红楼梦〉弥撒》里,这种题旨与小说本身达成了空前的圆融。《红楼梦》可视为小说搭建的“中国套盒”里最小的那个,它不需要被打开,即可呼应《〈红楼梦〉弥撒》所告诉我们的:一切无可挽回的消散,正代表了永恒。
回到小说形而下的层面也不难发现,洗练的语言和悠游的叙事、扎实的细节和灵动的玄思,本来就足够碰撞出丰厚的诗意与深意了。小说集的压轴之作《音乐家》是其中的集大成者。这篇小说取消了带有一定机械性质的嵌套结构,转而在记忆或幻觉中铺排伏笔。古廖夫跟那个在夜晚驾驶着潜水艇的小男孩儿有点像,他的奇妙能力遭到抑制,像鸡蛋面对高墙。当小说结尾那些细小的音符形尘埃缓缓消融之时,古廖夫的危险得到解除,读者的恐惧得以释放,拯救与毁灭同时完成,小说抵达了一种净化后的圆满与安宁。
与陈春成笔下精巧的故事构造不同,班宇的小说几乎没有明显的情节。他的取材往往只是某个片段,比如一段交往、一个决定、一次出行,像在人生的线性进展上随意截取了一节,还保留着它原本的粗粝质地。他的小说里有很多琐碎,但他写的并不是一地鸡毛式的烦恼,而是人生中结结实实却又难以名状的痛楚。
班宇的第二部小说集《逍遥游》承继前作《冬泳》一贯的贴地现实主义,反复描摹那些在生活重压之下难以喘息的人们。《逍遥游》里那个患病的女孩儿,她比任何人都渴望用力地活着,但是因为没有未来,她不允许自己抱有期待。她开始学着适应自己的消失,一点点放弃那些本来就不曾拥有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班宇的小说人物身上没有悲壮,他们遭遇的不过是寻常的人间疾苦。他们也没那么可爱,很难说清他们的失意、懊丧、绝望是不是咎由自取。他们只是在大水快要淹没头顶的时候,踮起脚尖伸长脖子,艰难地露出脸来呼吸,却绝不会呼救。因为他们不准备相信,更不准备感激。
大段的人物对话常见于班宇的小说。在这些冗长、细碎、无效的聊天记录中,小说仍然保持着奇妙的节奏感,让人想起那个小游戏“贪吃蛇”,从一个拐点到另一个拐点,一节又一节,永远停不下来。然而,人物的话越多,我们越需要在言不由衷、虚张声势、插科打诨和短暂的沉默中,辨认出那些他真正想说的,或者不想说却偏偏又说了出来的。《夜莺湖》里就有一个滔滔不绝的人。他声称自己被前女友纠缠,不堪其扰,借了10万块钱给她。明知道可能有去无回,他还亲手毁了欠条。直到小说尾声,我们才隐约猜到,他当初是因为前女友得病而离开了她。对于别人的不幸,他无能为力,然而负罪感还是支配了他,尽管他自己并不承认。
按发表时间推算,班宇的短篇小说《游蜉》应该写于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最为紧迫的时候。小说里几次提及未能实现的武汉之行,似乎是对当时举国上下的关切和煎熬的一种渺远的反映。不得不承认,小说在近距离的现实事件面前往往是措手不及的,它最具有撼动性的力量一定来自于隐喻,一旦摇旗呐喊、正面强攻,往往就成了隔靴搔痒。《游蜉》的难得之处在于仍然试图寻找寄寓情感的那个容器,一点点揭示生命触底反弹的韧性。这个结论,正如吴琦那篇记录疫情的短文所引用的诗句——“在溺水中学会游泳”,也如鲁迅所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王占黑的短篇小说《去大润发》可视为中篇小说《小花旦的故事》的续集。那个跟着老山羊参观地下广场的游泳头,这下毕业了,工作了,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的新的烦恼。她讨厌工作,也吃外卖,也谈失败的恋爱,也和我们好多个漂在大城市的年轻人一样,不知道未来。一次去往大润发的奇妙之旅,让她逃离被工作时间规定的生活轨迹,在铺着怀旧的暖色调的空间和物件上发现细小的童趣,得到了片刻的疗愈。
从选材或者技术上看,王占黑的小说都称得上朴素,但这不妨碍它有一种奇异的动人力量,让人产生完全的信任。这大概有赖于小说里那个若有若无的叙事者。从小说集《空响炮》《街道英雄》,到最新的《小花旦》,王占黑的小说里往往都有一个“我”。多数时候,“我”是隐藏的,“我”所讲的都是别人的故事。然而,别人的故事也会牵涉出“我”,就像《小花旦的故事》其实是《小花旦与我的故事》。我们绝不会追问小说里的那个“我”是不是王占黑,这是一个既没有意义也没有答案的问题,可当这些小说联成一片后,它们所共有的漫不经心的自叙性质还是摆在了纸面上。透过叙事者看别人的眼睛,我们也认识了她自己。她是不设防的,她愿意暴露经历、立场和好恶,让我们听见她在心里自己对自己说的那些话。她从不是冷眼看客,而是热心观众,恨不得马上从小说里蹦出来,对更多的生活发表意见。
王占黑的小说还有很多伸往现实的触角,与真实的生活勾连在一起。《去大润发》里比比皆是,懂得的人总是会心一笑。比如“每个人童年里都有的那个男孩”,折成纸盒的购物邮报,《新概念英语》第一课的课文……还有大润发这样的所谓“野鸡超市”、优衣库、以及“9·11”事件。这就像是一代人的生活博物馆,里面有人也有物,有新闻也有旧事,有宝贝也有破烂儿。重要的是,这些展品还活着,还在此刻的生活里发生意义,只是我们常常因此而忽略了它。这样的小说显然不挑选也不迎合读者,它只是亮出这些黑话,给读者来去的自由。它也承认生活比自己更大也更高明,所以无意复制或压缩现实,只是要让我们沿着小说给出的线索,回到生活的乐趣中去。那个喜欢四处拍下“海宝”照片的小花旦,肯定想不到自己身后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寻找海宝的队伍。这时候,究竟有没有一个真的“小花旦”或者“游泳头”,完全不重要了。
在这种意义上说,小说也可以在虚构与真实的边界上反复横跳,如同陈春成所写的那样,“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幻想确实改变了世界”。
二
这一年,魏思孝的《余事勿取》、默音的《星在深渊中》两部长篇小说都写了一桩谋杀案。这一题材因为强烈的情节张力,已经繁衍出悬疑小说这种特定类型,而上述两部作品,显然不止于这个范畴。
《余事勿取》有个简明扼要的后记,作者在里面交代说,这部小说是按照第二章、第一章、第三章的顺序写的。长篇小说往往被视为建筑,那么这等于建筑师告诉我们:我先建了二楼,又建了一楼,最后建了三楼。——听起来就是座危楼,随时要塌。小说就在摇摇晃晃中完成了自己的三段式叙事:侯军杀了素不相识的卫学金,卫学金是个肝癌晚期患者,卫学金的儿子卫华邦回家奔丧。小说三章分别以“侯军”、“卫学金”、“卫华邦”命名,从三人各自的视角开始讲述。
如果仅仅为了用罗生门的方式陈列一桩谋杀案,作者可能不需要在结构上大动干戈了。事实是谋杀案限定不了这部小说,其中旁逸斜出的枝杈太多了。小说主要人物有三个,其他具名具姓出现并且不能视之为“次要”的人物至少有20个。叙述散漫,闲笔很多,造成了结构上的某种松动,同时也构成了三个人物各自的独立性,使调换章节顺序成为可能。
来看看第二章,也就是“卫学金”这一章的“楔子”吧,这确实是一个经典的鸟瞰式开场:“辛留村位于山东鲁中地区丘陵过渡地带包裹下的一块平原上……村子里的一些老年人保持着伺候土地的传统,年轻力壮的大多在附近上班,对循环往复的农业生产充满了厌恶……任何新生事物,在农村都是滞后出现,可一旦出现却又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2000多字的篇幅里,不乏对当下村庄生活景观、历史变迁、人情世故的精妙概括。如果小说从这里写下去,卫学金就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楔子”的最后介绍他出场:“五十一岁的卫学金是辛留村普通的村民……卫学金曾经是父母的小儿子,现在是丈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婴儿的姥爷。他还是拥有五亩土地的农民,他干过数不清的职业,但都是以农民的身份。”无数长篇小说的魅影从这里滑过。沿着出身、家庭、职业的经纬线,本可以织成一张清晰而庞大的家族叙事的网络,罩住这里的祖祖辈辈,把他们变成一个个可定位、易瞄准的猎物。可作者偏要带我们冲破出来,看看不是村民、不是儿子、不是丈夫、不是父亲、不是姥爷、不是农民的卫学金,本来是个怎样的人。
他也是个有尊严的人。有一次,他想把家里闲置的柴油机卖给收废品的人,讨价还价中,对方质疑柴油机多年不用,肯定坏了,“卫学金心里不舒服,摇头笑着说,你不知道我的为人。”于是柴油机不卖了,连废品也不卖了。他还是个有柔情的人。他元宵节赶骡子拉货,路上遇到吹吹打打的表演队伍,骡子受惊,把货物摔了,晚上回家之后,他战战兢兢地等着挨打。“卫学金站在马槽前说,白天的事怪我,光顾着自己看热闹,忘了你怕人。”又说,“以前只把你当牲畜,没寻思到你也有脾气。”后来,卫学金丢了工作,很缺钱,想起从前拒卖柴油机的事,非常懊悔。而几年之后,骡子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他“冲着骡子说了句,不管咋说,也是个牲畜,留着没用”,就把它卖了。生活总会迫使人消磨尊严,耗散柔情,让他变成那个不得不成为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身上那些转瞬即逝的闪光之处,才更显得珍贵。
在凶杀案的条框之下,《余事勿取》的野心分明是要描绘一幅当下农村生活的风情画卷。卫学金这样的村民,也许已经不是农民了,但他们跳脱不出太阳底下的残酷命题:贫穷、疾病、死亡。他们不是没有挣扎,也曾看到过希望,然而命运往往是轻佻又残忍的,它让刚得知绝症消息的卫学金马上又以更不体面的方式离开了人世,简直就是个恶意的玩笑。侯军没有卫学金那么窝囊,他对情欲有近乎变态的渴求,可是这种强劲的生命力找不到出口,只能像苍蝇一次次撞向玻璃,发出单调而惨烈的回响。因此,这是一部凛冽之书,其中当然也不乏热烈,只不过,热烈过后,是更甚一步的凛冽。
同样是多视角叙事,《星在深渊中》的篇幅几乎两倍于《余事勿取》。作者以惊人的耐心把故事铺开来写,试图揭露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一个叫陈晓燕的女人死了,她身边的恋人、朋友、亲人或多或少都有嫌疑。随着他们各自的前史、相互的恩怨一点点显露,越来越多的视角加入进来,同事、老师、记者、警察……像滚雪球一样,小说的体积迅速膨胀。然而这个过程中,陈晓燕的死因并不是被层层揭开,也没有更加扑朔迷离,而是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凶杀案成了一个叙事的借口,作者更迷恋的是拆解每个人物的念头和动机,描绘他们的生活细节。果然,最后谜底揭晓,凶手就是陈晓燕的舅舅,一个早早出现并且嫌疑很大的人,竟然与整本书漫长的叙述几乎毫无关联。
当然,作者的用意也许根本不在于破解这桩凶杀案。陈晓燕的死打破了以“蛋糕酒号”酒吧为集散地的小团体的平衡,最终他们或是达成了和解,或是完成了忏悔,又回归了某种意义上的平静。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小说像一场大型“剧本杀”,在寻找凶手的游戏中,玩家扮演不同的角色,带着各自的任务和秘密,他们既要为自己开脱,也要根据所知的有限信息提出怀疑,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说谎。随着剧情的进展,他们的选择也在影响着故事的结局。
《星在深渊中》只是提供了这个故事的一种发展路径。这也许是一段有意思的游戏复盘,却不一定称得上一部精彩的小说。写法上的“绝对民主”给了每个角色成为主角的机会,但是人物的前史占据了主要的叙事精力,每个人都是还没来得及呈现个性,就淹没在故事的进展中。他们更像是一个个设定,而非真正的人,因此他们缺乏行动力,小说情节的推进就只能依赖巧合。无论是家庭变故、校园霸凌,还是性侵犯、失语症,每一点都是对人的致命一击,但却不足以解释一个人,不能成为他们相吸或相斥的充分理由。在游戏的世界里,人物设定的空洞是为了给玩家留出发挥的空间,而在小说的世界里,人物就应该是人本身。
《余事勿取》与《星在深渊中》,一个写乡村风土,一个写城市中人,却都寄身于一个相似的故事外壳,这也许折射了青年创作者在整体性把握现实能力上的孱弱。小说本身与这个外壳的摩擦和反作用,也预示了他们终将破壳而出,去寻找更贴合的现实轮廓与精神结构。
三
非虚构如同小说的补集,在小说短暂性缺席的地方,非虚构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青苔”是《生死课》里常见的一个词,多半因为里面写到的好些人居住在潮湿阴冷、人气不旺的地方。同时它也是一个象征,作者袁凌曾有另一部非虚构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喻示他笔下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的际遇。《生死课》一如既往地书写边缘群体,但并不强调“边缘”,因为凡是有界限的地方,就有中心和边缘之分,在不同的维度上,人人都是那个边缘人。因此,概括《生死课》是徒劳的,我们只能笼统地说,它记录的是人世间那些平凡的生和死,而这些凡人承受死生无常的态度,都将成为一种启示。
袁凌是记者出身,也写小说,他在引言里说《生死课》里的人物“大都是作者在成长经历、采访调查以及公益探访中邂逅的”。可能因为缺乏足够的完整性或戏剧性,这些人物未能成为某篇特稿或是小说的主角,而是作为“边角料”保留了下来。非虚构的形式看重这些人物的本来面貌,作者在叙述中也力求准确,语言上不带考究气,不为了讲得好看。只是这些文学的原矿石,即便未经雕饰,也会隐约露出天然的脉络,绝不输精工细作的小说。比如《父亲的最后一个电话》,写一个厌世已久的父亲自杀前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在电话中并没有挽留。随着儿子逐渐向作者袒露心声,父亲的形象一层层发生变化,他为何决定去死,也在几重转折中逐渐清晰起来。作者的二手叙述成为了一个自然行进的结构,缓缓地托出了一对父子沉重的故事。
董夏青青的非虚构作品《我,只是刘虹位》暗合了这位小说家在创作上的某种转向。这一年,她的短篇小说《礼堂》可视为以小说集《科恰里特山下》为代表的军旅书写的延续,《狍子》则走出了军营,一改凝练冷峻的文风,落脚到家庭中去。《我,只是刘虹位》并不带有太多作者的个人气息,平铺直叙而不失细腻,记述了摇滚乐队成员刘虹位走进乡村的创业经过和精神历程。离开了新疆风物和军营生活的董夏青青,能否在新的书写对象中重塑以往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风格,令人期待。
眼科医生陶勇的随笔集《目光》,是一个经历了劫难的人的自我拯救和开解。他不是文学从业者,那些素朴的文字却因为背后惊心动魄的事实而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力量。他引用的句子,不是我们信手写在作文里的一条论据,而是真切支持一个人走出黑暗的信念,是将他挡在深渊之外的最后一道屏障。也许,我们应该就此反思,并不是文学越来越不重要了,而是我们自己在摆弄和玩味它的时候,让它逐渐折旧、贬值,直至失去了重量。有些时候,文学当然可以轻得像一句玩笑,但有些时候,它也能够和生命等量齐观。
2020年还有更多的青年创作者,在这里未能详细论述。文珍的《夜的女采摘员》撷取那些人与人、与小孩、与小动物之间的细小温暖;梁豪的《人间》不避烟火气,描摹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真情假意;淡豹的《美满》以绵延且跳跃的语句勾勒人生的“不美满”;李诞的《候场》是躲在聚光灯阴影里的告解和辩论……概括他们是艰难的,而我们对青年的期许和想象之一,也正是这种向四面八方生长的可能性、一种野草般芜杂而旺健的生命力。借由他们的眼睛,我们看见了世界的多维,回到现实的复杂中,我们又发现了他们的天真。他们是星河,在这暗沉的一年里,发出细微而盛大的光芒。当然,他们本来也是一颗颗行星,我们需要做的,只是让光飞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