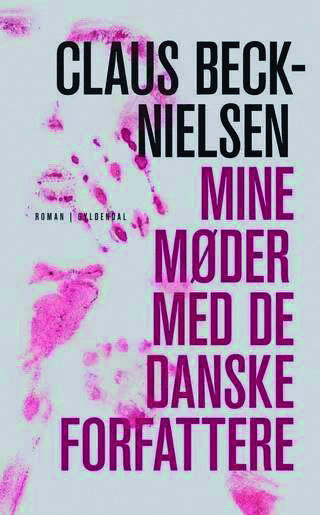克劳斯·贝克-尼尔森(Claus Beck-Nielsen,1963-)是丹麦当代小说家、剧作家、演员和音乐人。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尼尔森是一个摇滚组合的吉他手及歌手。90年代接受大学的文学创作训练。1997年推出第一本故事集,两年后推出第一本小说。2005年出版的《自杀行动》、2008年的《君主》和2015年的《大撒旦的坠落》组成三部曲。《自杀行动》让尼尔森在2006年获得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提名。2014年,尼尔森又借小说《我与那些丹麦作家的相遇》再获北欧理事会文学奖提名。尼尔森获得过若干奖项,他的书写里有残酷的自我揭示、痛苦的探索和怪异的前卫。
自我的毁灭
2001年,克劳斯·贝克-尼尔森宣布了自己的“死亡”。此后进行了一连串身份游戏。他使用过多种称谓,包括将丹麦文学史上伟大的名字如安徒生和卡伦·布里克森与自己的姓氏连在一起。
尼尔森在2002年推出的《自我消灭》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却很像配合身份游戏的文字记录。全书由13篇相对散文化的书写组成,采用他实际使用的各种假名来肢解自己,同时给自己分配出不同的人生任务。
对虽死犹生的尼尔森而言,2013年也是一个重要分界点,在那一年里,“尼尔森夫人”成为“死去”的克劳斯·贝克-尼尔森的最新化身。从那时到现在,称谓保持了持续稳定。尽管如此,要评点尼尔森还是不得不在他和她之间转换,在一副躯体和大脑的前世今生里转换。
当尼尔森依然是一个他时,已经借《自杀行动》为首的三部曲尝试了所谓平行的世界史的书写。他声称这一平行的世界史的书写旨在拓宽生命的深度和宽度。假如生命是一场终将不得不醒来的夏梦,尼尔森的自我毁灭为的不是死亡,而是以另一种乃至多种方式平行地活着。
出名的焦虑与自我的虚构
尼尔森将自己活成了虚构的一部分。他就是虚构,虚构也逐步蜕变为他的一种真实。一方面他高呼打破固有的自我,一方面他也以虚构来实践清晰的自我建构。
自宣布“死亡”以来,尼尔森以其作品试图表达对社会里必备的姓名及身份这一建构的质疑。他的艺术遗留品由一间所谓跨学科表演公司贝克维克(Das Beckwerk)管理,公司的影子总管和“已故”克劳斯·贝克-尼尔森在物理上百分百地重合。
没有一个身份来安放“死后”的飘荡魂魄的尼尔森,借这一间公司之口颇费苦心地进行过一番自我表白:克劳斯·贝克-尼尔森自1992年以来,以作家、词作者、剧作家、演员、翻译、评论家和舞台导演等身份生活……乍一听这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好像这人不仅仅是个艺术家,还是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和行为使他脱离普通群众的灰色薄雾,进入闪亮的《丹麦名人录》。
可事实是名人录过于包罗万象……此外,丹麦是世界上所谓的“艺术家”比例最高的国度。毫无疑问,克劳斯·贝克-尼尔森像成千上万的丹麦年轻人一样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但写作不一定能让您成为作家,弹吉他不一定能让您成为吉他手,表达和展示内心与外在的自我不一定能让您成为艺术家。实际上,在《丹麦名人录》之外,在丹麦街头,克劳斯·贝克-尼尔森根本不为人知,甚至在小小的丹麦也不为人知……克劳斯·贝克-尼尔森一生惟一做过的实事就是娶了个女人。他在丹麦沙滩上留下的惟一真实的痕迹是个孩子、一个叫艾玛的漂亮小女孩。鉴于他的故事是世纪之交丹麦普通男人的故事,他的婚姻失败了……在2001年秋,他如丹麦人所说的那样“走了”。一年后的2002年成立了贝克维克,负责管理和发展克劳斯·贝克-尼尔森的生活和作品,贝克维克的宏伟任务是将普通人的失败变成杰作,将休闲观念变成异象,将普通人的生活和故事变成世界历史。
这段自白背后站着一个绝不甘心只做普通人的家伙。原来的姓名承载的是普通的血肉之驱。婚姻及其失败被归结为普通男人的故事。这个普通男人将自己弄死的时候,包藏了让历史名人诞生的野心,坚信自己可以在新生的名人体内复活。
克劳斯·贝克-尼尔森或许就是个狂人和野心家。所有的人乃至他自己都不难对他的言行投以疑惑的目光。但他到底还是迎着目光、硬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现象,一个散发着当下欧洲的时代情绪的现象。他的意志狂野,而血肉之躯日渐消瘦,甚至脱形到让他自己担心,是否身躯不再能成为精神和心脏的容器的地步。
在“死去”已经两年之后,尼尔森书写了自传《克劳斯·贝克-尼尔森(1963-2001)》。这是个古怪的自传,同时也未标出作者姓名。不标作者显然是因为身份状态的尴尬,同时也成了标新立异的一个手段。自传详细记录21世纪之初的那场行为艺术:在哥本哈根街头,一个面色苍白的中年男人自称失去了记忆、无家可归。不久,尼尔森果真离婚了。回头看,他的街头表演倒像一场企图突围婚姻的强烈冲动,也像是要发泄精神上的丧家之苦。生活的真谛并非都能解密,即便当事人有时也不能,除非果真借助上帝的视角。
无论如何,尼尔森抱怨自己在丹麦不为人知,这实在是夸大其词。这抱怨里透露的是他对于出名的过度焦虑。成名焦虑从根本上说也包含死亡焦虑和被遗忘的焦虑。这样的焦虑人人都会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在尼尔森这里,显然演绎到了极端的地步。
身份的清除
“死亡”了的尼尔森躲在他的那家叫贝克维克的公司背后。这间公司声称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将尼尔森从个人身份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引入无名的、几乎可称为“空”的新存在形式。如果都采用这一存在的新形式,那么人人都可成为另一个人。按照这一思路,尼尔森的自我毁灭便不单是炒作,而兼具清除身份、找寻人类存在新形式的深意。
然而,世俗世界无法配合尼尔森的操作,熟人仍像他活着时一样和他说话。这游荡的魂灵不由得感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根本不肯放开个人身份。
似乎是万般无奈,又好像是蓄意谋划,在这个游魂的指令下,2005年,哥本哈根一处教堂墓地里竖起一座新墓碑,上头刻着克劳斯·贝克-尼尔森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没有什么遗体埋在墓中。贝克维克公司也就是古怪地活着的尼尔森本人煞有其事地为这奇怪死亡的合理性到古希腊罗马的故事里引经据典。事情还没完。2010年秋,贝克维克公司又与哥本哈根的一帮教会人员、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市民合作,给10年前死去的尼尔森举行葬礼。一具蜡像在小教堂里躺了10天,供人做最后的告别。这一次,克劳斯·贝克-尼尔森真的死了,死的不是自然人,而是身份。伴随这个人的“死亡”,贝克维克公司关闭。克劳斯·贝克-尼尔森的匪夷所思的死长达10年,又后事不断,尼尔森以其擅长的编剧和表演力毫无倦意地演绎着自己的生死剧。
尼尔森这个人弃用原来的姓名,号称要消除身份,却没有销毁迄今积累出的演员、作家、艺术家标签,相反不能排除他以姓名消除游戏强化艺术家形象的成分。消除的尽头是树立,他摆开一座迷路园,绕来绕去,却只还是一个出口和入口。这个人很难被埋葬,即便名字已从丹麦人口登记系统里删除,依然有原来的社会保险号。在私人领域,尼尔森很难向当时才6岁的女儿解释,自己到底叫什么、是否活着。不过他也表示:“还好,一切都没有回头路了。”这句话里有庆幸、也有无奈。也许证实了一点,世上没有绝对自由,人生无处没有枷锁,每一项选择都要付出代价。
性别是个机会
很难说尼尔森的生死、姓名和话语中哪个更真,比较确实的也许只有瞬间的情绪。为尼尔森举行国家认可的葬礼时,尼尔森走动着的形体也在葬礼上,在哥本哈根市内、距安徒生铜像并不太远的地方。这走动的形体是否暗自承认,自己操控着一出《皇帝的新衣》,是否在内心早已大笑不止,都不得而知。当然也存在另一个可能性,因为沉浸在巨大的戏剧情绪里,某些片刻,就连他自己也能被自己哄骗过去。总之,现场照片上,一张与被埋葬的克劳斯·贝克-尼尔森一模一样的脸躲在别人的肩膀后,像踌躇的幽灵以略带游离的表情看着眼前的人和事。2001年“去世”,2010年“埋葬”,2011年“复活”,2013年成为尼尔森夫人。尼尔森挑战生死,还跨越性别。
在2013年,尼尔森撰文表达出做一个“超越性别”的人的心愿。希望性别不再是社会建构的必需品,提出让性别成为机会。改变性别在尼尔森这里成了改变身份的重要一环,可以借改变性别让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成为另一个人。
本来,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在做不同程度的改变,就像牙齿,容易被人想当然地以为是固定不动的,其实一直发生位移。但尼尔森希求的改变更像拔牙,是摆脱过于固定的自我形象,在不怀疑自我存在的前提下扔掉固定身份。
必须指出的是,尼尔森憧憬的摆脱既定性别的愿景并非北欧正在讨论的第三种性别合法化。在尼尔森看来,第三种性别合法化不过是把给人归类的盒子从两个变成三个,这远非摆脱身份的需求。摆脱身份的需求是更大的解放,暗含巨大的责任,同时意味着找到发展自己身体和潜力的途径。尽管尼尔森的愿景里不乏闪光点,可也不难想象这会导致世界无序和自身无序。尼尔森似乎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癫狂,并以积极的意味自称是一个巫婆。巫婆就喜欢说不该说、不合适的话,拒绝成为同质的“我们”的一分子。巫婆好制造争端,以提醒人发现自我及生存环境里的弊端。
本来,当代北欧文学已经惯于将越轨的灵魂和越轨的身体与绝不妥协的创造力相连。创造力是积极而不可缺的,尤其对作家而言。精神偏差乃至疾病被视为颠覆性的能量。这能量能打破自我身份的固定形式,从而带来新的可能性。同时偏差总会引来污名和诅咒。
在健康问题商业化、日常生活医疗化的当下,自我以矛盾的方式试图借助模棱两可去敷衍社会既定的期望,同时在身体、性别、性等方面打破社会的规范体系。在北欧,一种几可称为精神病态的、逸出常规轨道的文学取向与自撰小说浪潮差不多同时兴起。在这些扑面而来的、基于自我经验的文本里,疯狂不再是个人生活缺陷,反之成为尝试新身份、谋求文学爆发力的兴奋剂。自我介于常人和抑郁者之间,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在嬉戏和癫狂之间。自我沉醉在极具挑衅性的双重方向里,处于摇摆又尚未坠落的微妙平衡中。性别、身体、性乃至整个人生都已掷入一场不惜代价的实验,同时投入了一场等待一夜暴得大名的豪赌。
说到精神病态,据说厌食症的病因就很复杂,而厌食症与渴望和排斥的矛盾情绪相关,也往往拒绝固定的性别认同。尼尔森夫人的瘦削身体带有厌食症特征,试图让自己超越男性或女性,以一种尚未实现的性开发身体潜能。于是 “性别是个机会”,可打开、关闭、改变。
尼尔森认为,在不至于怀疑自己是谁的前提下,设法摆脱固定身份甚至有助于缓解被互联网时代加大而非缩小了的民族主义、仇外心理和过度的自我专注。尼尔森赞赏不断的、终生的转变,持续地成为另一人。这个新的解放也要求每个人肩负巨大的责任,同时意味着可以找到发展自己的身体和潜力的更多方法和途径。 正是在尼尔森等人的演绎下,以性别为主题的北欧作品在当今不再是争取具有特定性别主体和特定性别身份的权利的尝试,而出现了要打破性和性别的既定规范联系,打破性别观念本身的新动向。
无尽之夏
尼尔森夫人在2014年推出小说《无尽之夏》。写一个男孩和女友在夏日里来到一座丹麦庄园。在那里,也有女友的母亲、一个丹麦贵族女子和葡萄牙男子的性爱和浪漫。小说被看作生命的赞美诗和青年的颂歌。有意无意地追忆似水年华。无尽之夏是生活和爱情的隐喻。生活和爱情有夏天一般明亮而眩晕的光,足以让人沉醉其间,忘记终将醒来,而任何夏天都有尽头。
延绵不绝的长句子兀自滚动向前,像表现欲极强的演员,并不在意读者的忍耐力。结构形成又消融,时间和空间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人物和故事演绎了夏和生的幻象。小说里有这么一句话,可以说是对文本恰好的自我评论:“就像这本书里的每一则故事一样,故事本身必须不断地被打断,然后继续播放,直到每一个故事都或多或少地抵达它悲惨的结局。”
尼尔森夫人自己则对这样的开头自鸣得意: “这个可能是女孩,但对此还一无所知的小伙。这个可能是女孩的小伙,绝不会想要抚摸男人,绝不会赤裸着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并且拿自己的皮肤摩擦对方的皮肤,绝不会,无论生活将多么令人兴奋和令人作呕,都永远不会。”
无尽之夏在时而迟滞时而迅疾的时间节奏里波动。一群人的道路在残酷的爱情嬉戏中交汇,命运的闪电冲击夏日的天空,领人走向始料未及的路。这个夏日里一切都有可能,也暗含致命因素。女孩的男友,那害羞的大眼而瘦削的男孩后来古怪地成了一个老妇。这老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用永恒的声音讲述无尽之夏,对生活里苦涩甜美的忧郁作出了精确又大胆的表达。这老妇似乎也就是背负类似的性别困惑的尼尔森夫人。冰岛当红作家松(Sjón)也被这部200多页的薄薄作品吸引,认为这是“关于爱情、死亡、时间和命运的,不同寻常且令人感动的小说”。除了松提及的几点,尼尔森夫人探讨了性别、性、身体等主题。
此前尼尔森也借用过卡伦·布里克森的名字。丢失的世界、贵族的垮台、青春、爱情、性和死亡的确也是卡伦·布里克森的符号。不光是布里克森,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在其处女作《尤斯塔·贝林的萨迦》里早就有对往昔时代和往昔人物的浪漫讴歌。不过尼尔森没有拉格洛夫的壮阔和浪漫,又比布里克森更歇斯底里。尼尔森夫人在扮相上越发靠近老年布里克森,其一或许因为转型后的女作家标签,其二或许因为消瘦,然而布里克森消瘦的根源是她走出非洲之前、从前夫那里染上的梅毒病后遗症,尼尔森的消瘦则和厌食症不无干系。
入侵和边界
一贯提倡打破边界的尼尔森反对把人群分为“我们”以及“其他人”,反对自我认定的固化。认为所谓真实的“我”或“我们”都只是个幻象,并提出“我”可以不断成为另一个“我”。成为另一个“我”时,有可能摆脱原本具有的对其他人的偏见。这些话不难理解,比如人到中年就可摆脱少年人对中年人的偏见;比如一个人陷入此前不曾想象的处境时,终于理解某些原本不能接受的行为。然而尼尔森以自我设计和手术的姿态阉割自己,这种大刀阔斧的刻意改变还是并不多见。尤其是当今的世界里,身份依然是人们在日常奋斗中必须携带的重要通行证,通过越来越先进的技术记录和验证身份数据已成常态,尼尔森拼力摆脱身份带来的实际问题。一方面,每一个人对应一个身份,另一方面,北欧社会自诩消除了阶级,而事实上“我们”与“他们”的区分在北欧依然和本能一样重要且鲜明。
然而果真没了身份,会是个什么处境呢?也许和没有护照的难民有相似之处。2015年秋,大批难民从非洲流入欧洲。难民流中,混入了涂着大红的唇膏、戴一顶红色贝雷帽的尼尔森夫人。尼尔森夫人从希腊沿巴尔干路线穿过欧洲到丹麦,2016年便推出了小说《入侵》。
本来,2015年8月,尼尔森夫人正于郁郁葱葱的柏林创作剧本。新闻媒体上,难民消息突然铺天盖地,对危机和危机中的人一贯充满兴趣的尼尔森夫人起意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以自己的身体去感受。《入侵》被认为形式很新颖,尼尔森夫人不仅是小说作者,也是小说人物。语言有时跳跃,有时冗长而复杂。书名其实颇耐人寻味。在政治正确的当下的欧洲,恐怕没几个人胆敢将难民流入欧洲称为入侵,从副题看,“入侵”这个字眼儿可以指尼尔森夫人自己闯入了难民区域的行为。但更可能的是,它携带双重意味,包括在当今的欧洲语境下不可明说、只可意会的。
在《入侵》这部小说中,德国南部边境的一座村落里甚至没人愿意谈论难民,村民担心的不是难民,而是自己和彼此,难民入境让本来团结的社区面临分裂的危机。尼尔森夫人描述了自己与难民、移民、志愿者及普通公民的直接相遇。
尼尔森夫人的难民流亲历很可能基于这么一个野心,身处值得见证的一段历史当中,描述内景,同时描述相对超脱的自身的平行运动,借此获得纵深感和历史感。尼尔森夫人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纵深感和历史感尤为重要,因为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平了,我们拥有事件和新闻的庞大网络,却少有记忆。在难民营,尼尔森夫人成了在篱笆另一侧工作和睡觉的志愿者。她没有刻意成为也不可能成为和难民水乳交融的一部分,反之她相信差异能让世界表现出所有的复杂性。
在欧洲,因为短期内难民的超负荷涌入,对陌生人的恐惧和排斥在增加。欧盟自成立以来,多少涂画出了一幅拆除了边界的大同气象。而在2015年的难民流袭击下,人们惊觉边界并未真正被拆除,只是一度隐形,如今羞于公然再现,便默默移动。无论各国的边境检查是否卷土重来,欧洲各国的很多人已默默将边界带入内心深处,这从右翼政党的迅速壮大可见一斑。
这场难民流之后,因为不堪重负,北欧各国从敞开大门转而开始推出严格的难民政策。尼尔森夫人坦言,《入侵》的书写并非出于一个享受着一定财富的北欧人良心不安的自责,而是出于对世界、对人的关联的兴趣。成为世上的一个人,成为观察和行动中的人是尼尔森夫人的追求。《入侵》也以切身体会揭示,自我的意识会出现在边界破裂之处。
真实与虚构边界的消蚀
尼尔森通过一系列文字、行动和表演,在真实与虚构的边界移动。那本狠狠地钉死他自己的自传,正是利用了媒体报道和日记描述他如何在2001年初哥本哈根的流浪者中度日,如何试图以无身份的方式扣开社会系统之门,如何成功地让自己登报,突然有一天,晚报上出现整版报道,出现了瘦削而苍白的尼尔森的脸,外加大标题“我是谁”。虽说这一出流浪者之歌是一场虚假表演,“我是谁”的问题还是很尼尔森,他喜欢研究自己到底是谁,也很享受让大众“看着我”。尼尔森的自传是文学作品,它的产生模式却有些不自然,仿佛预先设计好的某个东西的一部分。这小说不是从生活中提炼出的,倒像有一个被隐匿的脚本,戏剧已如期演完,随后脚本得到了公开。
本来,关于小说的社会共识之一是,虽然故事和人物源于生活,小说依然是虚构的。时下的状况则是,一方面社交媒体里假信息铺天盖地,另一方面,尼尔森一类的作家在现实和虚构的边缘主动进行演绎。比尼尔森更具商业成功性的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的自撰小说《我的奋斗》的畅销,在北欧催生了大量模仿者以及越发鲜明的新型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有它的犀利,有它的魔幻,恰如真实的谎言。凡此种种已使读者习惯于放弃区分事实与小说、真实和虚构。一个边界已被消蚀。
戏子的人生
2018年,尼尔森夫人推出小说《怪物》,聚焦于一对孪生侏儒,以带有散文风格的独白,对历史、时间、感官、生死的本质进行考察。书中写道:“放弃,并且突然没了目标或决定,丧失对事物和自己的所有权,只是让自己屈服于那个新的、滑动、扭曲、赎回或解放了的存在形式,就可摆脱自我。”
怪物最终以一种预见性的愿景,在一个全新世界中彻底转变为一个全新的人类:“你不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就是应该做自己不知道的事,尽可能精确地去做,直到它成形并出现为止,这样不仅你自己,而且整个世界都可以看到它是什么。”
可见,尼尔森对于人的生存形态的文学探索还在继续。这个作家的书写得到评论界的瞩目和赞赏,不过总体来看,尼尔森的书写与其说是靠文字出彩,不如说是靠着性、难民等边缘且热门的话题,靠着作者和小说的高度重合性在发光。这些书写走在真实和虚构的边界消蚀处,是实况转播式或行为表演式的,极具时代流行元素的写作。
尼尔森以不同的性别和称谓书写扑朔迷离、雌雄难辨的故事。在一个真假毋需固执地辨别、只需冷眼沉醉的新欧洲里,尼尔森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场郑重其事的表演,也是一段郑重其事的生活——这是戏子的人生,是边走边演、在每一个陌生村口的戏台上粉墨登场的戏子的人生。当尼尔森将这一状态意识化、最大化时,多少也活出了一分跳脱。在人生的台前台后变换,展现虽将粉身碎骨也能怡然自得的无畏,这无畏里几分是真,几分是即便胆怯也极力展现出的逼真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