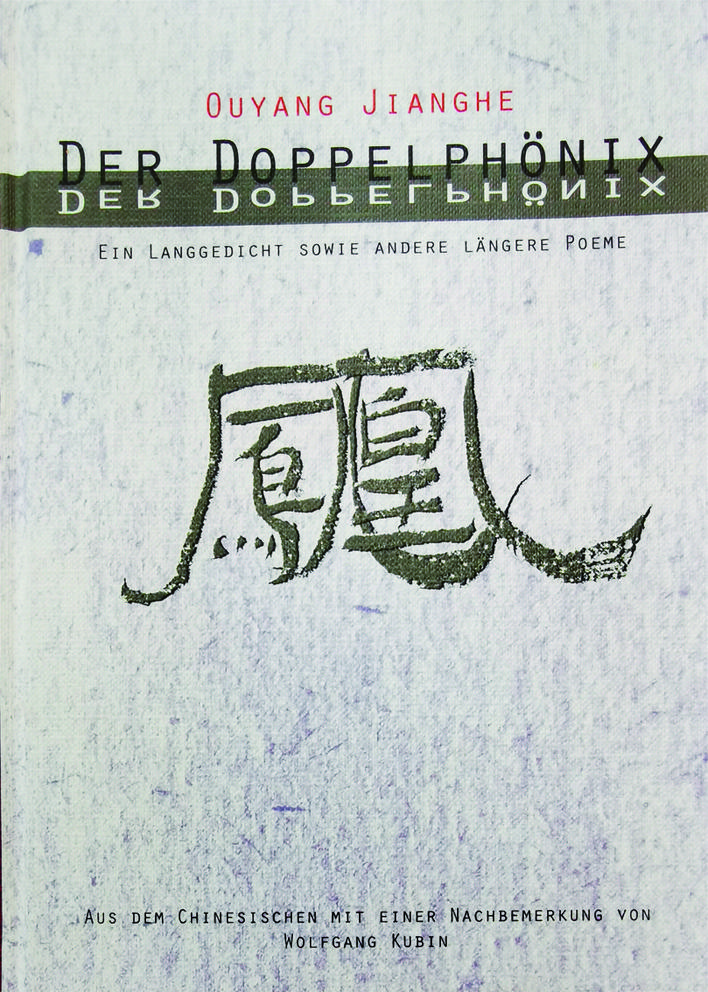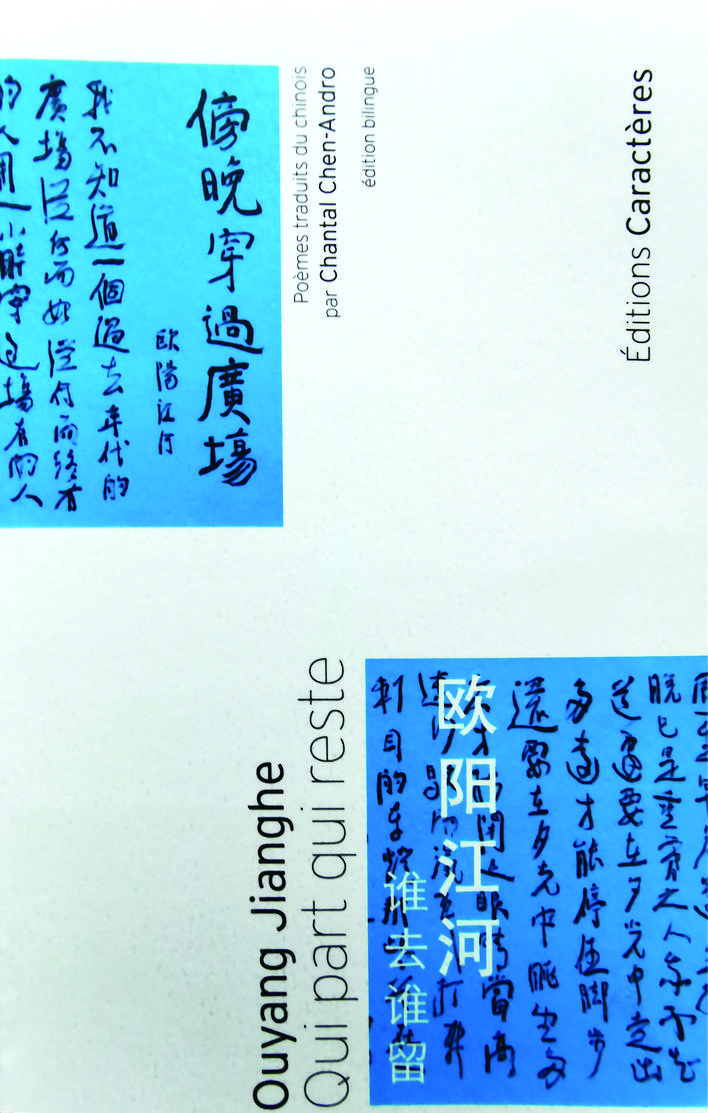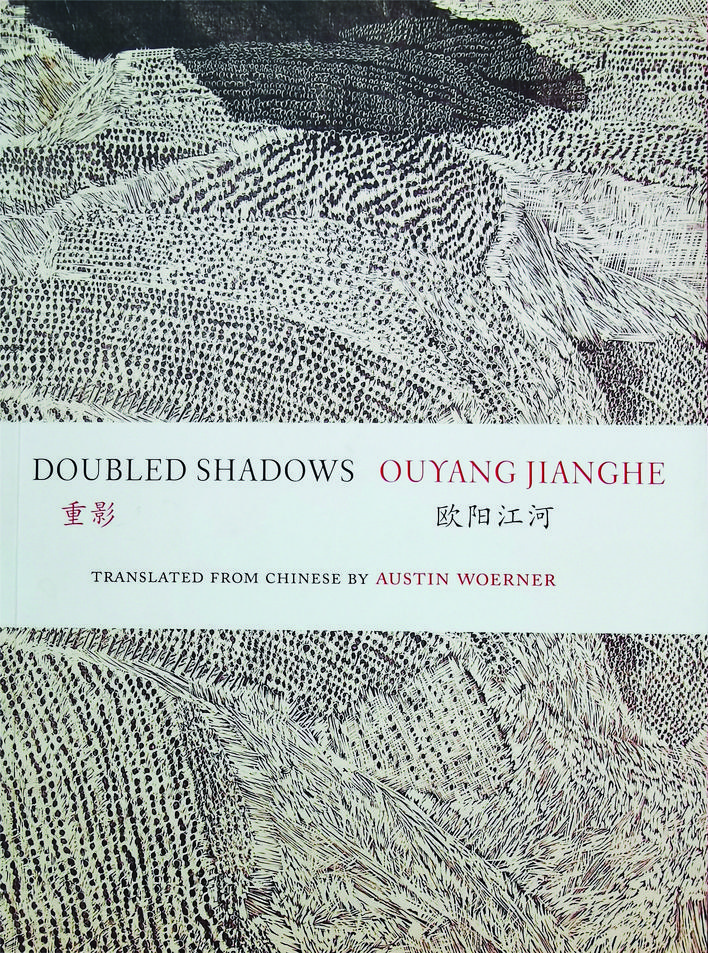何 平:1979年左右你开始新诗写作。上世纪80年代被想象成文学的黄金时代,当时的许多诗歌从业者在后来很长时间里不断缅怀那段日子,哪怕他们后来几乎不再写一首诗歌。我注意到你很少夸张地回忆那个时代近乎波西米亚的诗歌社群和类似行为艺术的诗歌活动,你基本上把这个时代作为诗学和诗艺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和你1990年代之后的诗歌写作构成一个合乎逻辑的对位关系。
欧阳江河:你说的这些,直接把我从写作之始嵌入到一个大的历史发生现场,而且正好是改革开放的起点——1979年。上世纪80年代对我来讲,不光把精神成长的东西放进诗歌文本里去了,我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活法、写法都在里面。整个80年代,我们成都那一群诗人都被诗歌裹在一起,诗歌本身就是日常生活。我一开始就带入了问题意识,不是说仅仅只是写诗那么简单,我已经在考虑某种纠正的写法的可能性,不仅仅只是修辞问题,它涵括了那个时代一些含混的、错杂的、兴奋的东西。那个时候好像各种可能性都夹带着某种沸腾的、灵氛的内涵,它被突然打开,火山爆发般降临到头上,悬垂我们,烘烤我们,把心之所感、手之所触、目之所视,全都融为一体。
我刚开始也写抒情诗,写得很烂,我自己都非常惊诧:我还写过这种东西?1983年突然写出了《悬棺》。动笔之前我深深考虑了语言的另类使用:中文诗还有没有其他写法?我把这个问题悬搁在脱胎换骨的高处逼问。比如,巴蜀文化中巫的成分被特意提取出来。巫的东西,作为地域文化,作为巴蜀话语,在语气、构词法、虚词使用等诸多方面,与北方语言大异其趣。这些语言元素的差异,被提取出来植入《悬棺》,句式奇诡突兀,用词咬文嚼字,种种杂糅语式,包含了对古汉语和现代中文的混用,以及词语张力的狂野扩展,这在国际汉学界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80年代还有像《玻璃工厂》《手枪》这样的诗,表层是在处理词和物的关系,但是实际上我都是从中文语言自身固有的规则、汉语固有的独特文明归属和可能性生发出来的。词物两者是一个相向而行的相遇过程。比如《手枪》,此诗用别的语言很难翻译,因为没有现成的对等语言规则、对等构词法可用。不止一个英译者断言《手枪》不可翻译,其中一人说:除非为英语发明一种临时的、译后即焚的专属语言。
上世纪80年代我还写了《快餐馆》《玻璃工厂》《汉英之间》等,都是跟空间、跟在场有关的。我的写作里的现场感、空间感,既是世俗空间、实有空间,但同时又是写作的、观念的空间,这两种空间的重合构成了我写作的现场,而这个现场又是作为“发生”的时代现场。比如说《汉英之间》写的是当时成都的英语角。这个作品里,已经有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日常生活方式的、语言学习和交流的以及隐含在语言背后的历史变化。总之,英语进来了。
我认可的是复杂的当代诗歌,写作定式极为重要,它与当代艺术“内在图式”的重要性颇为相似。
何 平:从你个人写作史的角度,我觉得你的1980年代应该结束于1993年。1993年前后是你精神、诗学和具体写作乃至个人生活都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你1994年发表于《花城》谈“中年写作”的长文,涉及你个人和同时代诗人的文学史和精神史转向,也谈到诗人的知识分子身份问题等等。其实,1993年前后也是中国社会结构和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过渡期和变动期。就文学而言,以上海《收获》为代表的先锋转向和北京《白鹿原》《废都》等重要长篇小说发表。这意味着真正意义的1990年代开始了,就像你1993年2月在成都写的《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这是你去国前最后一首重要的作品,也是对一个新的时代的预言。谈谈你这一时期的思想和诗学等方面的变化吧。
欧阳江河:如你所言,按照当代中国文学大的断代史划分,我的80年代一直延长到1993年。那一年,我离开中国去美国,这之前我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归并入80年代。我在去美国之前创作了《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同时又在写《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意识、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这篇长文,该文是我为洛杉矶的亚洲年会写的主题发言稿。我的这篇文章处理了“结束”这样一个主题,但这个结束本身已经包含了新的开始。首先是本土意识的苏醒,其次是中年写作的介入,第三个问题比较复杂,我所定义的知识分子身份意味着我本人对“纯诗”的告别。换句话说,我从此不再作为一个纯诗的、元诗的、美文诗的作者写诗,而是作为一个置身于“历史之当下发生现场”的诗人在写作。
我1993年出国后,从自己的“在地性”抽离出来,写的还是中文诗,但是由于人不在中国,有一种隔世、量子纠缠的眼光:我是我自己的隔世之人,我在我不在的地方,这样一种性质暗含在写作内部。这种写作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归零语境里面,深切感到它的抽空。写作变得推敲和审慎起来,处理的主题也从中国的本土现场变得隔了一层,出现了对比的、潜对话的成分。比如那个时期写的《纸币,硬币》《我们的睡眠,我们的饥饿》,还有短诗《去雅典的鞋子》等等,其内在声音都带有那个阶段难言的、双重言说的特性。《那么,威尼斯呢》是我旅居德国时写的,也处处闪烁着一种介于东西方的词物重影,把我珍藏在内心深处的成都搬到西方的威尼斯加以察看和思考。还有长诗《雪》,这首诗处理了个人自传式的材料,旅居心灵史的东西也放进去了。我连续几年居住下来,把西方世界那种震惊的、奇异的感觉变成了日常性,这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必须要经历这个转变,才能置身其间思考、呼吸、写作。我90年代出国旅居国外好些年,这个转化真是太重要了。
与此同时回看中国,在地的、诗意的、伦理的、心智的、词象和物象的,种种对比呼之欲出,汇聚而成写作的“定式”。因为我认可的是复杂的当代诗歌,写作定式极为重要,它与当代艺术“内在图式”的重要性颇为相似。你可以把定式的东西当成他者、圣者,但同时也是你自身宿命和日常性的一部分。写大格局的诗歌,尤其是长诗,对我来说这个深度定式不可或缺。
这个定式慢慢地、模糊地、开放性地形成了。旅居美国期间,除了活法、写法和读法的混用以外,又多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挪移、东西方的对比,文明这个角度被逼了出来。我的写作是有抱负的,这个抱负体现为一种阔视,一种深虑,带点冒犯,将天真与匠心搅拌在一起,但落脚点何在?我不是一个旅行家,也不是学者,我就是一个诗人。“诗人是语言的仆人,而不是语言的主人”——我认可艾略特的这个说法。我也一直在使用“定式”语言,比如《悬棺》,而它究竟是怎样一种中文,我自己也说不大清楚。它不是母语意义上的中文,里面包含了父语,甚至儿孙后辈的语言,包含了尚未诞生的婴儿的未来语言。但它也包含了古腔杂语,其他语言的东西,翻译的、反翻译的语言,这就是我所理解和使用的定式语言。到了美国,这一点特别清楚,我知道我的写作语言是汉语和中文混用,这不仅仅是语种意义上的母语,我所写的那个语言,我要穿透进去的那个语言,是诗歌最深处的、根部的定式语言,它在母语里都需要翻译:一种外语意义上的母语。茨维塔耶娃也说过类似的话,她说真正的诗歌不用母语写作。那不用母语我们用什么写作呢?用诗歌语言。
何 平:我查阅了一下你的发表目录,1993年到2010年和2012年在《花城》发表《泰姬陵之泪》和《凤凰》,这中间你发表的作品很有限,可以视作你个人写作史的沉寂期,但我倒是愿意把这种沉寂理解成一种精神和诗学的蛰伏期。经历这个蛰伏期,你进入到这10年来的写作爆发期。在我看来,《凤凰》是一首重要的作品,不仅仅因为它是一首你复出以后,和徐冰的装置艺术作品《凤凰》被并称为“现象级”的文艺作品(王书婷),也是因为《凤凰》本身的象征性意义——它出现在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历史时刻。李陀从两个《凤凰》读出了“21世纪开始”的意味。我觉得至少就中国主流对世界的想象而言,这个判断大致是准确的。而你和徐冰完成《凤凰》的90年之前,郭沫若的诗歌《凤凰涅槃》也被解读为一个新世纪的开始。写《凤凰》的时候能够感受到那个特定历史的时代气氛吗?
欧阳江河:我1997年从美国回国后,定居北京,写作上有一种没落地、飘在半空的不适感。那段时期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我正好错过了。10年停笔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写作本身的原因。由于错过了文学的先锋性全面退隐这一非常重要的错层、转换时段,我的现场感不在了,而没有现场感我是不会动笔的。我不会依循惯性、习气去写作。
在《凤凰》写作之前,应该说我本人的90年代已经彻底结束了。《泰姬陵之泪》创作于2008年,这可以看作是我恢复写作的第一个重要作品。但此诗当时只写了一半,全诗完稿已是10年后的事了。因此,我2011年创作的《凤凰》,才应该算是结束蛰伏期后写出的第一首完整作品。《凤凰》所处理的时代主题,在时间节点上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以及稍后的上海世博会大致重合,当时中国的腾飞举世瞩目。徐冰的装置作品中出现的凤凰形象与中国腾飞有关,但这个飞翔意象是由钢铁翅膀、建筑废弃物、工地劳动者的痕迹等组装而成的,其历史追溯、思想性质、复调方法都是开放的、正在发生的。换句话说,是一个有待命名的腾飞。我的长诗《凤凰》处理了这样一些材料,这样一个时刻,很多与时代精神、时代症候相互对视和对话的东西,以及对话后面的沉默、感动、冥想,那些劳动的、伤痛的、坚忍的、甚至软弱的东西,还有资本这个庞然大物,还有艺术本身的东西:它的光晕、它的附着物、它的自我指认,凡此种种,在这首诗里汇聚为碎片化的、但又是总体性的拼贴与建构。《凤凰》这首诗也陆续被翻译成好几种语言,被看作是21世纪前10年的重要诗作。
我写的凤凰和当年郭沫若的凤凰截然不同。郭沫若的凤凰是革命发生之初的、激进现代性的一个命名,用凤凰涅槃处理了生死转化。而这也是20世纪初东方革命的重大主题。我写的凤凰并不是介于生死之间的转化,而是介于命名和被命名、词象和物象之间的转化,介于将要消失之物和正在出现之物、碎片化与总体性之间的转化。这肯定是一个大的转化,涉及全球化时代的大格局之变、多层叠的建设脚手架、新的可能性。
我不算那种每10年就非得换一个写作阶段的诗人。《凤凰》写于我第二次旅居美国时期,我在曼哈顿居留了3年,处于写作爆发期,除《凤凰》外,我还陆续写了《祖柯蒂之秋》和《黄山谷的豹》等一系列诗作。写《祖柯蒂之秋》时,我正好置身于纽约现场,这首长诗处理了“99%对1%”这么一个全球注目的大事件,是一首反思美国、透视资本、从事件提炼诗思主旨的长诗。《黄山谷的豹》也是一首长诗,它带有文脉考古性质,从“当代中文”的写作现场,追溯古人身上“老汉语”的在地性,处理的并非元诗主题,而是中文/汉语混用的“元语言”问题。这对世界范围的当代诗歌写作也是个值得警醒的问题,因为手写/键盘、人类写作/AI机器人写作,两者相混之后的元语言之豹变,肯定是一个根本的大问题。
何 平:2020年你写了一组名为《庚子记》的诗歌,这不是简单的“庚子纪事诗”,我是从“反思全球化时代”角度看这组诗的,因为发生在2020年世界范围的疫情完全改写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想象和图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组诗歌的?
欧阳江河:《庚子记》全诗1100行,完稿于去年7月。这个诗的内文脉像、内视镜像、内听声音,是有强力的方法论定式的。由这个定式统摄,写作的复调性、碎片性、杂俎性,构成了一个隐在的、集束的系统,足以容纳头脑风暴式的翻滚、席卷、压顶、滔滔不绝。这个作品带有一种日常性,而且是那种一边写一边发生的日常性,从流水账式的东西里提炼出异质混生的诗意。
疫情期间,我处于密集阅读的状态,重读和初读了许多源头性质的书籍。这种阅读进入日常生活后,使我的肉身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当下抽身出来,引回到经典的历史语境中。这个回溯性语境跟我的写作构成了对话的复义关联,它所起的文本作用不是赋形、定调、整理,反而是起扰乱的、纠正的、呼魂的作用,引导必不可少的纠偏力量出现。
我深度考虑了《庚子记》的写法问题,但又跳出了这个写法。你待在房子里,外面有一种世界性的病毒在发散:这样一种处境,把你逼到生命的、存在的边缘,病与死的边缘,你怎么对生命、对写作做出交代?这里似乎有一种被逼出来的、与常态写作不大一样的例外性质,就是在末日的逼视下如何看待生命,而且不仅仅是回看,是逼视当下。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代性时刻”向“当代性”转向的巨变时刻,甚至带点“超历史”的意味,不光感性的东西,所有知性的、意向性的、可公度的东西,全都卷入了这个大转向。诗歌写作从中接收到的消息与含义,是否具有某种程度的启示录性质呢?我注意到,很多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置身于医学病毒、政治病毒的双重包围下,几乎全处于失语状态。20世纪所形成的思想定式,话语表达,突然一下子失效了。在这种情况下,《庚子记》试图命名某些难言的、无以命名的东西,表明了一个诗人的思考、感受、回答。它带有世界场景的想象性投射,以及“现世/余生”主题的设问。
诗歌写作当然是大地上的事,但它也包含了一个自古以来的律令:引导人的认知上天入地。
何 平:至此,我们能够发现你个人写作史的几个时间节点:1979年、1993年、2010年和2020年,这些时间是你的个人时间,也是中国或者世界时间。个人小时间和时代的大时间相遇,恰恰构成完整的改革开放时代你个人写作史的精神建构,现在回过头看,你觉得这种个人时间和时代之间的相遇和交集是一个事实,或者是你不同写作阶段的精神事件吗?
欧阳江河:我的写作与我所处的时代,在时间节点上的互文式对应,这是我很少想到的。这里面可能包含了我的写作抱负,一种预先植入的历史无意识。我一直对自己说,我的写作一定要对我所在的这个世界有一个总的交代,它要求我的写作在文本世界与真实世界这两个平行世界之间,建立起某种对应关系。这构成了我诗歌写作的一个基本特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的写作进程与时代转化在节点上的对应,构成了我本人的写作事件,但绝非自传式的构成,反而含有一种把自我泯灭的性质,一种主体身上的大他者性质,这样一种纠结与共同呈现。所以现实发生的现场,投射到我的写作现场以后,那种深层勾连关系可能也隐隐催促我个人精神的成长。这种特质在我的某些作品里面表现得非常明显,有的比较隐晦,但肯定是存在的。在我的成熟之作里,写作既是一种事件的发生,或从未发生,另一方面它又呼应勾连,换魂一样换出精神的发生。
何 平:个人写作史和更大的文学史都存在源起、绵延和转折,但个人写作史和文学史不一定在同一条延长线上,它们存在各种关系方式。说得简单一点,像我们前面谈的1980年代、1990年代和新世纪,也意味着存在整个时代社会结构、思想方式,也是文学史等等的延长线和转折点。个人文学史的延长线不一定都能并轨和接驳到文学史的延长线。因此,观察和你同时进场的写作者,有的还守着1980年代文学的延长线,生长着自己的写作和美学,而每个文学史的转折点则被你get到了,你因此可以不断从“旧我”生长出“新我”,你意识到自己写作的阶段性衍化了吗?
欧阳江河:这个问题涉及我诗歌写作的变化。进入新的时代现场以后,怎么对待原有写作的风格、质地和辨识度,怎么和旧我保持联系,但又融入不断自我质疑、自我更新、自我变形这样一种力量。这包含了中年变法、晚期风格的问题。
新世纪我的写作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我写了诗集《大是大非》,其中不少诗作融入了口语,而且是带有加速度、带有断言语气的口语,体现了中年写作的牢骚和讽喻,把旅居国外时写作中的那份冷静、矜持、那种隔了一层的隔世感,变成了在场感,变得激烈、决断。新闻与长时段的东西,在社会学语境里混杂,那份恍惚,那份强扭,颇有点马脖子被强扭过来的冒犯气度。
第二阶段我专注于长诗写作。这些长诗所处理的诗意、所使用的语言材料、所表明的风格特质各不相同,但在呈现最低限度自我、在寻找对新现实的新命名方面,又有着某种共同特性。“新命名”不是基于纯属个人经验的东西,而是来自新诗意的拿捏,来自断言与难言的杂糅。它甚至超乎“定式”之外,连写者的主体都越来越含混,但又一直在问那个古老的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写者主体,越来越明澈,也越来越活在词语的显身之中。但这个人是谁呢?写作定式所确立的那个自我,在形成的同时也在被消解。尤其在1700行的长诗《古今相接》写作过程中,这种“我是我所不是的那个人”的写作主体意识,变得异常明确。
21世纪的人类置身于大转折、大幻化的环绕之中,原来我们以为已经铁定的、像福山所宣称的所谓历史之终结,其实一直还在变。范式之变,已经停不下来。从西方世界的现代性到全球范围的当代性,从全球化时代到后全球化时代,从消费至上到新冠病毒,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在塑造和形成的过程中消散了。中国也在变:该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界定新的中国形象?中国通过介入全球的经济体系、金融系统、全球产业链、全球反恐和环保系统、语言交往系统,介入了世界事务,全世界以更为广阔的目光和声音面对中国,界定中国。这个变化是双向的:当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认不出自己时,中国反而更坚定地确认自己。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自我?这其中的新命名、新形象,有待我们共同考察和界定。
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个人和时代的关系,对诗人和作家,包含了和写作的关系。中国的文学写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的变化特别明显,新一代小说家所追求的东西,和我的同龄人这代小说家,呈现出相当不同的取向。年轻一代作家的文学抱负大为减弱,各种各样的诱惑铺天盖地而来,获奖、畅销、快速成名、改编影视、一夜“网红”,还有消费的、资本的、媒体的、网络的深深介入,改变了他们的写作。写作的语速、节奏也不同。很多人使用一种键盘式语言、操作性语言在写作。这样的变化扑面而来,工具理性的东西大面积出现了,连带传播方式的变化。
我们80年代的那一批诗人又如何在变呢?不少人的写作迷失了。有人长时期行走江湖,成了符号和传奇,成了民俗。有人彻底离开了写作。当然也有人持续写作,但如你所言,如果个人写作的延长线与文学史的延长线没能并轨和接驳的话,写作是不生效的。打个比喻,80年代的诗人是开着绿皮火车在写作,而绿皮火车不可能直接在高铁轨道上伸展自己的延长线。现在是一个高铁时代,一个手机的、热搜的、广场大妈的时代,这当然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但它触及了诗歌写作的转向问题。人有时会陷入这样一种尴尬:不是说找不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是连问题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我在这里提出的转向问题很简单。一是诗歌写作自身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当代诗的写作经过40年的成长和衍变,已经形成某种公共的、固化的“写法惯例”:诗意从何而来,诗意主旨的聚散、辨识与确立,诗意后面的逻辑、理路、政治正确,诗意本身的语言织体、风格表达,已逐渐累积成“惯例”。很多诗人依靠它写作,诗越写越成为惯例“自动合成”的产物。原创性呢?例外呢?问题意识呢?
第二个问题事关写作的不同现场。80年代的诗歌写作相对而言比较任性,比较个人化,写作现场可以是个人内心的、理想或浪漫的,也可以是江湖的、荒漠的。但当下的写作则是一掀桌子不认80年代的现场,众多年轻诗人不再是为杂志发表和诗集出版而写,他们在手机上、在朋友圈、在公众号与热搜平台上谈诗、论诗、写诗。一个诗人假如上了热搜,诗歌上了热搜,与诗歌在纸上写、在刊物上发表、以诗集方式出版,能是一回事吗?诗歌圈也出现了“广场大妈”,这样的现场肯定会影响时代精神,影响写作定式。况且还出现了资本推手,话题引导、点击率统计、后台操作,所有这些汇在一起,构成了当下现场,影响了写作的性质。我一直说热搜是一个没有在思想的、哲学的层面被处理过的东西,诗意的深邃维度、诗歌写作的可能性、诗歌语言的多元性质,这些都不可能上热搜。我的两首近作《算法,佛法》《瓦格纳能上热搜吗?》从不同角度触及了这个问题。很奇怪,当下的中国人不以如何看待瓦格纳、莎士比亚、庄子或康德来划分不同人群的圈层,而是以如何看待特朗普来划分。
这种东西的出现对诗歌写作意味着什么?我的《自媒体时代的诗语碎片》预设、预知了某些桥段,我想做的事情是:做出新的命名。举一个例子,我在《自媒体时代的诗语碎片》与《古今相接》中,处理了无人机。无人机运用于实战之后,对战争的性质做出了根本的、概念与定义上的改变。传统战争中的男子气概、献身精神没有了,英雄没有了,神枪手没有了。无人机对战争形态和性质的种种改变异常深刻,这是一种文明转折层面的、反词层面的根本改变。因为无人机是个反词,它在词的意义上尚未命名,有待命名:而这正是我在诗歌写作中想要做的事。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形式、新命名而言,无人机只是一个碎片般的文本例子。比如我关注算法问题,它能算到佛法头上吗?在长诗《宿墨与量子男孩》中,我关注的是量子时代的科学话语,经由诗歌话语的处理,它们发生了怎样的两相改变?各自不变的又是什么?量子论有灵魂吗?还有我在《祖柯蒂之秋》里对资本话语的处理,以及《庚子记》所处理的新冠病毒对全球化的深刻改变,都体现了某种新命名的当代冲动。时代已经这样了,诗人不去处理它,行吗?时代就在你面前,你就活在这里,你为什么只能写那种唯美的、小聪明小陶醉的、自恋的自嗨的诗,而对需要命名的东西视而不见?我如果这样选择,会觉得愧对这个时代。
所以我的写作,延长线的特质在于词与反词的重合。延长线把我的写作延伸到热搜的(反热搜的)、量子男孩的、高铁的、广场大妈的,这样一种综合语境、新的写作现场里。80年代的绿皮火车在21世纪的高铁轨道上不能行驶,需要换轨。要想把诗歌写到火星的现场去,就得换航天飞机。绿皮火车上不了天。诗歌写作当然是大地上的事,但它也包含了一个自古以来的律令:引导人的认知上天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