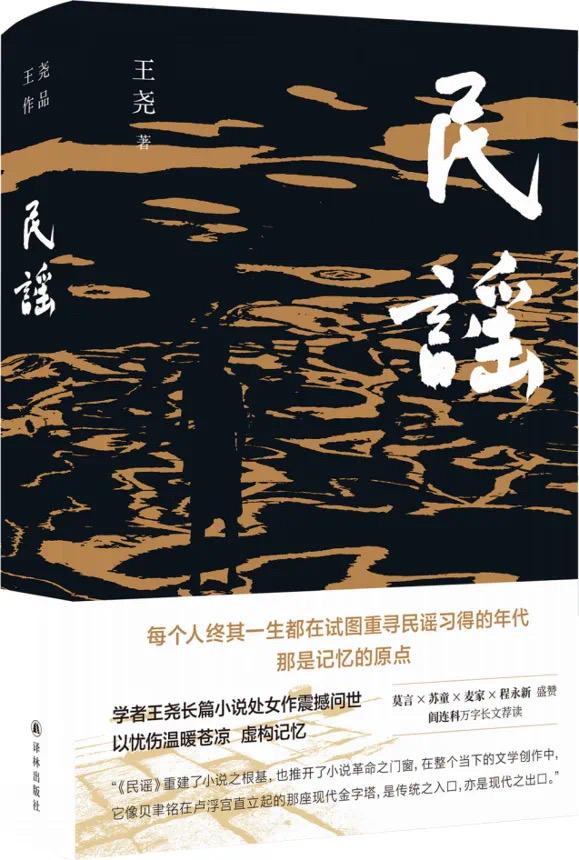《民谣》是一首关于动荡年代的歌,是王尧关于“我”和世界的感受、洞察和记录。“民谣”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对记忆的回溯、对生命的思考,代表着对生活的感观、对自由的向往,也代表着这种自我的表达被接受、被流传。因此,我们讨论《民谣》,其实是在探索理解自己、打开自己的方式,也是在探寻理解世界、打开世界的方式。
《民谣》发表以后,在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作家、评论家都撰文予以讨论。程德培从记忆与虚构的视角指出《民谣》反故事的特质。王春林从王尧提出的“新小说革命”出发,探讨了《民谣》的自传性和实验性。张学昕则从个人与历史、乡村与伦理等多个层面,将其界定为“朴素的诗,或感伤的歌”。关于《民谣》的诸多评论,显然已经超出了一个“批评家”写小说的无聊“噱头”,而隐秘地彰显出这个文本自身的“异质性”。而“异质性”正是“民谣”的内在特性。
这种“异质性”的表现之一是民间性。《民谣》是一个有着强烈秩序感的“民间”样本,这种秩序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王尧对于小说“空间地理”的熟稔和安排上,《民谣》中,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方位,在作家的脑海中都有着极为清晰的图谱和准确的勾勒。这种明晰的方位意识,隐含的是作者稳固的个人记忆和自信的小说意识。这种清晰也代表着理性和客观,代表着一种理性而稳妥的生活秩序在个人情感上的投射。在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中,人的灵魂也是有序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觉得奶奶把旧社会的东西带到了乡下,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奶奶其实也在延续一种和乡村生活格格不入的文明或者是一种生活秩序。奶奶一辈子都生活在她的旧时代,她从来没有走出那个小镇。”但这个“民间”在时间的压力之下显然已经摇摇欲坠了。就像在小说中,随着叙述的展开,一个乡村世界的没落和消亡已经不可避免。“村中有庄,有舍,舍围着庄转,庄围着镇转,镇围着县城转,这就是通常的社会秩序。有一天,我们村庄的秩序被打破了。”“外公和老杨打破了这一平衡,他们参与的革命活动,在悄悄改变着这个村庄。”“现在,我站在桥上,看着向东行驶去的两艘船,我觉得这个村庄好像也在分娩之中。”“我看到我越来越靠近的那个庄子,像正在瘪下去的气球。”在革命、技术、时间的合围中,这一稳妥的秩序感已然被各种碎片化的力量侵蚀并割裂,一种混乱且痛苦的经验正在剥离着我们失序的脆弱心灵。
《民谣》不是历史的康庄大道,而是一条时间的“小径”,这条小径上标注着时代的编年,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就是在这条编年的小径上行走,由此展开一份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生命地图”。因此,民间之外,《民谣》的异质还表现为它独特的时代性。为了呈现这一特殊的时代,小说主要采用了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个人史来透视大历史。《民谣》写的是一个少年曲折的心灵成长史。这个村庄的变迁发展,是和个体的成长紧密相连的。那些破碎的历史,既重要,也不重要,重要是因为个体就生活在庞大而繁复的历史体系之中,不重要是因为个体在历史的漫长时间中从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写作方法似乎也不出奇,但在具体细节的处理上,《民谣》还是显示出了它的高妙。二是通过两种不同的语言方式来呈现一个复杂时代的样貌,在这个意义上,《民谣》的杂篇和外篇成为小说结构中十分重要的两个篇章。这是另一种历史情状,也是另一种生活状态。它的重要性甚至不仅仅表现在这种形式的创新上,而是用这种新颖的“实录”方式将历史颓败状态下,语言的扭曲所标示的人性的走样和病态一一刻印出来,且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分裂的语言让我们坠入生命的“幽暗之地”。两种语言预示着两种历史、两种生活,也昭示了这个时代的独特和不同。我想,这部小说的意义之一或许就在于,当我们试图重新回溯那个时代的真实面目时,我们要在《民谣》的这些人里、这些事里、这些物里去寻找蛛丝马迹。
《民谣》有着辨识度极高的地域特色。但是这一地方性,好像并没有为评论家所重视。《民谣》的叙事是从码头开始的,是在关于河流的叙述中逐渐展开的。河流几乎贯穿小说始终。“河水从西向东流。大船、小船、木船、机船,偶尔也有竹筏荡过。”我与村庄的关系,是和河流紧密相关的。我的许多感觉,甚至于都和河流不可分割。比如小说中写道:“在后来的写作中,当我试图叙述死亡前的感觉时,那只水泥船,像畚箕形状的船舱,像猫叫的橹声,还有外公的鼾声,就在水面上向我飘来。”王尧说,他在写下了小说的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上”之后,找到了小说的“调性”。在我看来,这个“调性”是和河流紧密相关的,河流成了他身体和心灵的一部分。《民谣》的视角有着一种河流的视野,河流塑造了《民谣》。试想一下,如果《民谣》中缺失了这些河流,那它的调性和叙事一定是干枯而乏味的。“在四面有河的地方,先人们筑巢而居,庄出现了。在田野的河岸旁边,舍出现了。这就是李先生说的风水。”“河流”是《民谣》的“风水”。在河流的深深滋养下,《民谣》表现出一种蕴藉的抒情性,朴素而感伤,深致而平和。也是在河流的缓缓流动中,《民谣》将一个时代的苍凉和一个人的忧伤幻化成记忆的虚构。“站在码头上的那一刻,我很快把自己看成废墟中的一块青砖,一根朽木。我又毫无理由地想把一个村庄一个小镇蜕变的历史承担下来,毫无理由地让我的记忆在潮湿和阴郁中成为废墟。”这是一种天然的、而非人工的情感状态,有着“民谣”一般的纯真和自在。因此,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没有这一异质的“地方”,也便不会有《民谣》。
《民谣》的另一“异质性”则是其人文性。《民谣》是王尧来自心灵深处的思考和抒情。他通过小说,将内心和世界相连。作为一名批评家,王尧对小说有着非常清醒而深刻的理解:“我固执地认为,小说写作需要思想、学养和多方面的文化积累。我们不是把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附加在小说中,而是说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把握,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小说的故事、语言、结构和意义。换一种表述是,思想、学养和文化积累影响着我们对历史、现实和人的理解。”小说包括其他文学样式,其最终的落脚点是人。这人当然不是孤立的个体,他是民间的人,是时代的人,是地方的人,是有爱有恨、且善且恶、又苦又乐的人。王尧是一位有着人文情怀的批评家,他即将在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沧海文心:战时重庆的文人》等书,都贯穿着这一写作思想。同样的,这一思想也藏匿在《民谣》中。《民谣》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有缺点的。正视人性的局限和弱点,可能就是一种可贵的人文性。当然,《民谣》的人文性不止于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人文性在《民谣》中被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深化了。那种可以被观察到的人文性,虽然已经带有了某种被完善的价值,但尚未被充分展开,而具有一种模糊的含混性。《民谣》就是试图召唤并重建这一人文性的正常状态。
王尧说《民谣》不是他的自叙传,但他显然用自己的风华正茂为我们换取了一段特殊历史的记忆和虚构。而活在历史之外的芸芸众生,如何与脚下的土地、身处的时代、周遭的世界重新连接,读完《民谣》或许可以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