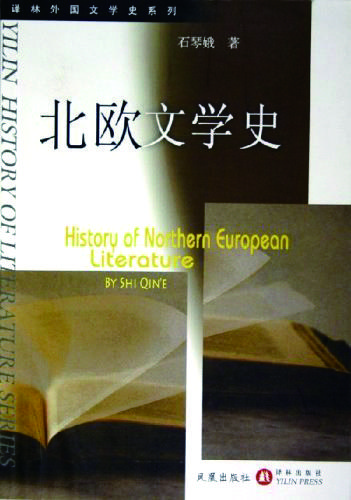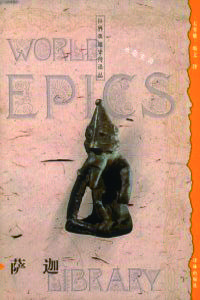“从小注重文学教育、给他看书的,长大了的确和从小不看书、不接触新东西的孩子完全不一样。”84岁的北欧文学翻译家石琴娥接受采访时说。石琴娥近年来将主要精力都投注在北欧儿童文学的翻译上。2018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石琴娥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最近,她主要在翻译挪威和丹麦的儿童文学,“北欧的儿童文学真的好。它有传统,从安徒生开始,主题一般都是宣扬真善美,而且充满了幻想、想象,无拘无束,非常适合儿童,能够培养他们大胆去思考,而不是前怕狼后怕虎”。石琴娥说,一个人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有创造,老禁锢在一个模式里头是不行的,通过文学阅读,孩子们能够放开思想,从小就充满幻想和想象。
“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老禁锢在一个模式里是不行的”,这是石琴娥自己人生经历中的深切体会。她从上海弄堂的亭子间走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一直到走遍北欧各国;她做过外交官、老师、学者、译者,甚至导游……看上去温和安静、安于书斋的石琴娥,笃定、柔韧,特别有主意,她的人生丰富多变、不断突破边界。
从亭子间到外语学院
1936年,石琴娥在上海出生。父亲原是宁波的农民,十二三岁到上海学生意,讨生活。成家后,因为穷,没办法在当时的租界内生活,只能把作坊开在闸北区——当时所谓的“中国地界”。一台车床,夫妻配合,按照规格要求加工铁板,小作坊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占领上海时,不敢轰炸租界,但在闸北狂轰乱炸,一夜之间,小作坊被夷为平地。为了逃命,大批难民越过外白渡桥进入英租界,后来英国人封锁了租界,很多人就从桥上跳下去,跳到苏州河上的“船上人家”,想办法到桥的另一边去。石琴娥的父母就是这样带着孩子们逃到了英租界,保住了性命,在苏州河新闸路一条弄堂里阳台上搭出来的亭子间安顿下来,石琴娥就在这个亭子间里长大。
父亲重男轻女,没有认真考虑过女儿的读书问题,但妈妈因为深受文盲之苦,决心不能再让女儿过这样的人生。石琴娥8岁时,妈妈觉得不上学不行了,带她到家旁边的小学报名,名字是老师根据妈妈说的发音写的。小学毕业后,石琴娥又和家里争取,希望能读到初中毕业。爸爸让她自己去找学校,找到就可以接着读,石琴娥就自己找到了女中。12岁上初一时,上海解放,这对石琴娥的触动很大。早上一打开门,门口地下整整齐齐躺着解放军——直到现在,有时候闭上眼睛,石琴娥脑海中还是会出现这个场面。上海解放后,交大、复旦的大学生们到中学宣传党的政策,石琴娥也非常积极,初三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中学的团干部。
初三时爸爸说,行了不要再念了,女孩子已经足够了,将来又不是我们家的人。但父亲没能阻止她的求学之路——学校免了她的学费,爸爸也不好再说什么,“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解放了,我恐怕到初中毕业就到此为止了,可能成为和很多人一样的家庭妇女”。
高中快毕业时,石琴娥本想学园艺,已经开始准备复习了,学校通知她去考语言和外交。“那时候思想比较僵化,学什么外语啊,我不愿意。但这是国家需要的,虽然不是我当时想要的,但让去就去吧,服从分配。”到了考场发现,考卷上写着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这样,18岁的石琴娥离开了弄堂的亭子间,进入外国语学院。
“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
上世纪50年代的外国语学院很小,只有一个三层楼的房子,马路对面是当时正在建的俄语学院,附近有齐白石的墓,周围环境很荒凉。石琴娥上学时外国语学院实行军队化管理,入学每个人发两个碗一双筷子一个小马扎,吃饭之前要唱歌——“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这类歌曲。专业也是分配的。入学前石琴娥想学德语,觉得德国人科技发达,学好德语可以把先进技术介绍到中国来,但最后被分配学英语,她觉得既然是组织安排,那就去学。
当时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主要来自三个地方:北京、上海、天津,石琴娥的同学中有很多是北京的高干子弟。而她因为父母的作坊扩大成厂子,属于“资产阶级”,同学觉得她有点“异类”,她也觉得与同学不太一样。加上刚从上海来,普通话说不好,不敢发言,在有些事情上想得不多。很快,运动开始多起来,石琴娥没受到什么冲击,她想自己是来学习的,就要把学习搞好,“学到点东西”。
1958年,石琴娥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外交部,进了翻译队。翻译队由北外和北大的毕业生组成,住在位于现在外交部街的宿舍。翻译队属于一个过渡性质的机构,新进人员先在这里了解一些外交部的情况,再分配到各个司工作。50年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续和一些国家建交,正需要外语翻译,外交部翻译队外派了一批工作人员,有的去西欧,有一部分去了北欧。北欧五个国家,外交部向每个国家都派了四五名工作人员,石琴娥被派去瑞典,同行的还有和她一起从上海进入外语学院、一起分配到外交部、后来成为她丈夫的斯文。
去北欧的旅途“长路漫漫”。一行人先乘火车去莫斯科,走了一个礼拜。当时中国驻苏联使馆还没有建起来,使馆人员先住在莫斯科一个大饭店里。随后,大家在莫斯科分别乘飞机前往各自要去的国家。60多年后,回忆起当时路上的情景,石琴娥记忆犹新:“外交部的确给了我们一点小费,告诉我们要给列车员,但我们觉得给小费很不尊重人,不要一上车就给人小费,想要下车再给。结果一到车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茶水,也没有人提供服务。还是过了两天之后,跑到其他同学车厢一看,人家什么都有。同学跟我说必须给小费,结果一给了之后,什么都来了。”石琴娥说:“这条道,我走了五六次呢。”
在瑞典被“到处借”
1950年,瑞典同中国建交,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石琴娥和同事们到瑞典工作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学语言——通过英文来学习瑞典语——使馆只给了大家三个月的时间。与被派到东欧各国的外交人员不同,瑞典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作人员不允许去外面学习,所以石琴娥和三位男同事只能在使馆的宿舍学习,老师是当时瑞典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儿子、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正在勤工俭学。课程一星期三次,从早上开始,不上课的时间复习。学习三个月后,四个人被分到使馆不同机构,石琴娥到了研究室,斯文在文化处。
研究室的主要工作是为使馆外交人员整理和翻译信息。石琴娥每天早上6点就要到使馆,将当天的报纸根据不同的内容翻译和打印出来,在9点外交官们上班之前送到各个单位——当时我国的外交官懂外语的不多,需要看翻译的内容。石琴娥刚学了三个月的瑞典语,懂得也不多,好在这个翻译和文学翻译不同,有国际背景知识,意思不出错就可以,她也借助看报和大量翻译“实战”,一点点提高了瑞典语水平。
当时使馆工作人员可以带家属,家属也都不懂外语,石琴娥就被“到处借”,一会儿到武官处,一会儿借到商务处,大使或者大使夫人有活动,她也要去当翻译,因此口语练得比较好。在瑞典,除了夏天,基本上天亮就已经9点多钟了,石琴娥早上走得早,工作结束天又黑了,“那时候基本上看不到太阳”,石琴娥就这样在瑞典待了四年。
四年间生活上的一个重要改变是,石琴娥与斯文在瑞典结婚。1962年,两人一同回国。
外国语学院十八年
回国后,斯文进入外交部西欧司,石琴娥则回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站上讲台。石琴娥在瑞典工作时,国内还派了5位留学生到瑞典,留学生不算使馆人员,可以进入瑞典的大学学习。这5位留学生于1961年底回国。同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在1961年第一次正式招收瑞典语专业学生。这样,外语学院就有两个瑞典语班,石琴娥负责留学生那个班。
此后,直到1980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石琴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度过了18年光阴,身处其中经历历史浮沉。1970年到1972年间,整个学校搬往农村,石琴娥什么都没带,只带了一本瑞典文的《长袜子皮皮》。劳动之余,她就翻看这本书,特别喜欢。回来后,她在北京跑着找出版社,想要翻译出版这部书,“出版社说,对不起啦!当时的孩子已经够淘气的了,再来一个淘气的,不可能的”。她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说了这个情况,任溶溶说,北京不敢,上海可以,遂在复刊后的《新民晚报》上开始连载自己翻译的《长袜子皮皮》。1984年,石琴娥在瑞典见到了《长袜子皮皮》的作者林格伦,说起这段经过,林格伦问石琴娥有什么感受,石琴娥和她讲,当时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皮皮那么大的力气。“我们下放到劳改农场,很苦,我要是有皮皮那么大的力气就好了。”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石琴娥有几次被借调的经历,陪同来访的瑞典作家代表团。对于细节,石琴娥笑着说记不清了,“但我们中国人确实是这样的性格”。“我做的主要是沟通协调的工作”,瑞典的摄影师拍摄背着手、拿把镰刀溜达的农民,当地人不乐意,石琴娥就和当地的人说,既然同意人家来了就不要限制人家,让他看看真实的。有时候她也会给瑞典人做工作,两方面协调,瑞典的作家们都觉得她努力而且坦率。
“当时我还不知道以后会走上文学的道路,所以没有和他们交流太多文学的东西。我当时想的是,多少年了,我都没有好好接触瑞典语,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提高我的瑞典语水平,提高口语;我要了解一些瑞典的情况,看看从语言上、教学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用。”有意思的是,她后来和这些瑞典作家成了很好的朋友,多年后她去瑞典做访问学者时,每到节假日,都会受邀去作家朋友在乡村的家里住几日。之后在中国驻瑞典使馆文化处工作期间,和作家的交往就更多了。
“我要写一本《北欧文学史》”
1980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的冯至先生被聘请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化科学院外籍院士。当时,社科院外文所还没有专门研究北欧文学的学者,冯先生想引进一个能做瑞典文学的人,就托在外语学院做德语教授的夫人姚可崑征求石琴娥的意见,将她调到外文所。
“去了之后吓我一大跳。”石琴娥到外文所时,所里不少人已经是知名学者,文学功底深厚,还有很多赫赫有名的老先生。石琴娥觉得周围要么是名人,要么就是科班出身,而自己已经40多岁,又是半路出家,有点犯难。心里有底后才能工作,她第一件事就是先摸底——跑图书馆,从院图书馆到首图、国图,查一查到底有多少北欧文学被翻译成中文,有哪些研究北欧文学作品的著述。查了半天,石琴娥发现,没多少东西,绝大部分是鲁迅、茅盾、叶君健等老一辈作家、翻译家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翻译的,且不是从瑞典语直译的。除了易卜生、安徒生以及从德文翻译的拉格洛夫等几位作家之外,当时国内对瑞典及北欧其他国家的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并不多,比较系统的研究著作是学者李长之的一部《北欧文学》。
“我当时就和冯先生说,我既然来到外文所了,就一定要写一本《北欧文学史》,现在就要开始写。”冯至先生建议她不要心急,写文学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积累很多资料。听从冯至先生的建议,在系统阅读和研究其他国家的北欧文学史以及作家作品评论的过程中,石琴娥认识到翻译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性,决定从介绍和翻译当代瑞典作家开始。她先是翻译了瑞典当代作家、后担任国际笔会主席的魏斯特贝里,雇工派代表作家伊·鲁·约翰逊以及197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温德·雍松的作品,发表在《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1981年,瑞典在斯德哥尔摩举行首届国际斯特林堡戏剧节,石琴娥受邀参加。这也是她回国20年后第一次重返瑞典。为准备会议发言,她对斯特林堡进行了初步研究,同时翻译了斯特林堡的《失去本性的朱巴尔》发表在1981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研讨会上,石琴娥用瑞典文做了题为《斯特林堡在中国》的报告,阐述了自20世纪初叶到80年代我国对斯特林堡的译介、接受和评价,全场轰动。这令石琴娥非常感动,“我不是觉得我怎么有能耐,时局和机遇很重要,当时正好是改革开放不久,我们想了解国外,国外也想了解我们,正好处在这样的时间”。回国后,石琴娥把会议情况和20年后重到瑞典的感受写成《中国人》,发表在《人民日报》(1981年10月10日)上。
在翻译了几部瑞典文学作品之后,很多出版社找到石琴娥,希望她也能翻译丹麦、挪威、芬兰、冰岛的文学作品。石琴娥认为自己有责任介绍北欧其他国家的文学,这是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在英语和瑞典语之外,她开始有意识地学习其他语言。
1991年,石琴娥应丹麦驻华使馆的邀请到丹麦做访问学者,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她与丹麦作家座谈,参加北欧理事会文学奖的选拔会,还参加了为期两周的丹麦文夏季训练班。石琴娥因为选拔会只参加了第二周的学习以及最后的考试。“好在北欧的语言都有点类似,我有瑞典语的功底,对学习还是有点好处的。”这一年,石琴娥55岁。
为了能够听懂和翻译挪威文学作品,石琴娥又开始自学挪威语,学习方式很特别——当导游。1998年,石琴娥结束了为期5年的中国驻冰岛使馆借调工作回国。她的一位在国旅驻斯德哥尔摩做代表的学生打电话请她在国内帮忙接待瑞典旅行团。为了学习挪威语,解决翻译上的问题,石琴娥主动提出接待一些挪威的旅行团。她随身带着挪威语材料,听旅客们交谈,有问题就记下来,利用旅途中的零散时间向他们提问。她还利用参加外交活动的机会,在挪威驻华使馆向大使和工作人员请教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从63岁到70岁的7年中,石琴娥依靠这种方式学习了挪威语。
为研究北欧文学,石琴娥有意识地了解所在国的社会和文学状况,尽量多地接触北欧各国作家和文化学者。调入社科院之后,在近20年不断翻译作品、学习语言和广泛了解北欧各国文学情况的基础上,石琴娥写作北欧文学史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1998年从冰岛回来后,石琴娥开始写作《北欧文学史》,该书在2005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世纪至20世纪北欧五国文学发展情况,并对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评介。
“文学翻译的意义就在于此”
上世纪80年代开始,石琴娥投身北欧文学翻译。除了安徒生童话、塞尔玛·拉格洛夫《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以及斯特林堡《红房间》等经典作家作品之外,石琴娥还与丈夫斯文合作,将雄伟瑰丽的冰岛神话史诗《埃达》和《萨迦》译介成中文,在新世纪之初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后,得到读者的高度评价。这是两部史诗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她还翻译了瑞典工人作家伊瓦·鲁—约翰逊的《斯德哥尔摩人》、挪威作家福劳德·格吕顿的《蜂巢》、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的《神秘》等北欧现当代文学作品,并与斯文合译了瑞典作家斯蒂格·拉森“千禧年三部曲”之一《玩火的女孩》等多部文学作品。
“文学就是反映人生,它同时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推动不是像一个具体的科学发明一样,它是潜移默化的,时间比较长。”石琴娥觉得文学翻译的意义就在于此,虽然介绍的是别人的东西,但我们也能够通过借鉴获益。《斯德哥尔摩人》写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社会情况,80年代石琴娥翻译这部作品时,觉得书中所写的农民工、城市建设和人的生活等具体问题和国内情况很相似。有感而发,石琴娥在后记中特别说明,小说写瑞典二三十年代的情况,但瑞典社会发展得很快,大家现在生活过得还不错,希望我们的国家也能努力建设得更好。
在新世纪,北欧文学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各类文学体裁共同发展。其中,新现实主义作品占据了当代文学的主流地位;现代主义创作手法被广泛运用,这主要表现在历史小说、自然题材等作品上,如冰岛作家古德蒙德松的《酷暑天》以及挪威作家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我的奋斗》系列自传性作品。在题材上,相较于过去“从农村到城市”,北欧文学近年来多关注城市中人的情感、关系以及单亲家庭、领养等社会问题,代表作品有丹麦的《慢性天真》、瑞典的《屋顶上星光闪烁》等。石琴娥认为,北欧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是跟随欧洲大陆文学潮流,但在近20年来,北欧迎来了一个悬疑犯罪小说的繁荣时期,比如瑞典作家斯蒂格·拉森(Stieg Larsson)的“千禧年三部曲”(《龙纹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捅马蜂窝的女孩》)等,“挪威人认为他们的悬疑犯罪小说比美国的更早更精彩,冰岛也有一批优秀的悬疑小说家,他们会说‘丹·布朗我们早就有了’”。此外,作为北欧文学创作传统的诗歌和戏剧也比较发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北欧文学译介整体有了较好发展,一来由于读者对于北欧文学兴趣的提升;二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陆续培养了一批北欧语言人才。北京外国语大学除了瑞典语之外,还先后招收芬兰、丹麦、挪威和冰岛语专业的学生,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也开设有瑞典语等北欧语言专业,培养了部分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才。另外,北欧各国都有支持本国文学作品翻译成外文的资助机构,也为北欧文学译介到中国提供了一定便利。
“希望恢复北欧文学学会”
说起中国北欧文学译介和研究的话题,还有一件事令石琴娥念念不忘——“我非常希望能够恢复北欧文学学会”。
北欧文学学会成立于1989年4月25日,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的分支学会之一。学会成立时,冯至先生任会长,学会顾问由萧乾、叶君健担任,石琴娥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石琴娥回忆,成立大会非常隆重,除了冰岛当时还未设驻华使馆,四个北欧国家的驻华大使都参加了大会,资格最老的芬兰大使代表四个国家讲话,表示非常愿意看到有这样一个机构能够介绍北欧文学。外交部、中联办、文化部等各个单位懂北欧语言的人都被吸收入会,“因为专门做北欧文学的人太少了”。
1990年,在时任丹麦驻华大使的建议和支持下,北欧文学学会组织召开了一次丹麦文学研讨会。会议经费由丹麦驻华使馆出了一部分,石琴娥又在工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募捐了一些,邀请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两位教授到会,做关于当代丹麦文学的报告。冯至、叶君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北京创作专业研究生班学习的中国作家莫言、余华等也应邀参会交流。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挂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1992年,石琴娥被借调到中国驻冰岛使馆后,外文所没有专门做北欧文学的学者,北欧文学学会取消。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设有专门的北欧文化研究机构,但石琴娥总觉得,外文所的北欧文学学会有一种全国性的意义,北欧驻中国的文化官员以及国内高校的研究人员都曾向石琴娥表示过恢复北欧文学学会的希望,“他们觉得社科院作为研究机构,有这样的号召力,能够让全国各地对北欧文学感兴趣的人信服”。
“应该培养和鼓励年轻人”
2018年年底,冰岛现代作家弗丽达·奥·西古尔达多蒂尔的长篇小说《夜逝之时》中译本出版。该书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策划的“北欧文学译丛”第一辑五本书中的首部。“北欧文学译丛”计划出版50到80部北欧五国的当代文学作品,目前已出版包括《神秘》《慢性天真》《屋顶上星光闪烁》《在我焚毁之前》等11部作品。丛书以长篇小说为主,兼选少量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诗歌和戏剧,均从原文直接翻译。
翻译这套丛书的有很多是年轻译者。《夜逝之时》的译者张欣彧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石琴娥的情景。在冰岛使馆主办的一部冰岛文学中译本发布会上,石琴娥做了题为“冰岛文学在中国”的演讲,“她讲得很从容,是个特别好的讲演者,在不长的时间里,给我们一下子提供了好多有趣的、难得的、充实的文学史史料”。当时刚刚20岁正在读大二的张欣彧在活动前就听说石老师要来,很兴奋,想“认识石老师”。他学冰岛语才一年,已经开始借着词典在做翻译了,译的是冰岛中世纪文学最经典的散文体作品《斯诺里埃达》——现在通行的北欧神话传说,基本都出自于此。译完几章后,张欣彧想请石琴娥看看自己的译稿,就在活动之后凑到石琴娥跟前,一边自我介绍,一边把译稿拿给她。石琴娥收下了译稿,告诉张欣彧“一定看”。
“这个画面,我记得很清晰。现在,我越回想那时的唐突和幼稚,就越对石老师的温柔和鼓励充满感激。”这几年张欣彧在国外读书,也已经翻译了多部冰岛文学作品。他时常和石琴娥通电话,回国时总会去看望她。“石老师偶尔回忆起冯至先生,讲到冯至先生对她学术事业的支持。我想,石老师之于我,就如冯至先生之于石老师一般。她给予我的帮助和信任巨大而纯粹,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将这力量也传递下去。”
为年轻译者创造条件是石琴娥主编该丛书的初衷之一。她把翻译看作是事业,虽然“翻译在学校和科研单位都不算成绩,而且稿酬又低”,但石琴娥还是希望能够培养有事业心、能坐冷板凳的人从事这项工作;特别是要帮助和鼓励年轻人,“大胆放手让他们去干”。
“愿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
2009年8月19日下午,斯文在家中翻译斯蒂格·拉森《玩火的女孩》时晕倒,这次,他没能像前两次一样化险为夷,永远地离开了石琴娥和他热爱的翻译事业。
“他走后,我陡然觉得人世空虚起来,觉出自己的渺小和孤独,感觉失掉了依靠,失去了主心骨。”石琴娥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不让保姆擦拭书桌,不让挪动原版《玩火的女孩》和斯文的手写翻译稿。她知道完成逝者未竟的事业才是最好的纪念,但往事历历在目,令她难以提笔。
从大学同学到一起赴瑞典工作,再到共同为北欧文学翻译贡献力量,石琴娥与斯文在生活和事业上是真正志同道合的伴侣。石琴娥在外语学院任教时,每周只能回家一次,孩子和家里基本上都是斯文操持。从1958年起,斯文在我国外交战线上奋斗了40个年头,从普通翻译到58岁成为大使,其间的辛勤和艰苦可想而知,但他仍然利用业余时间做了大量文学翻译工作。石琴娥与斯文第一次共同翻译出版的长篇作品是塞尔玛·拉格洛夫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此后,夫妇二人又一起翻译了《埃达》和《萨迦》,并合作编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北欧文学、戏剧和历史三个部分。夫妻俩没少因为字句的译法争论,甚至吵得面红耳赤,但每完成一部译作,又颇有成就感,“喜不自胜,有时到附近的龙潭公园遛一圈,放松一下;有时出去吃一顿以示庆祝”。翻译《玩火的女孩》时,石琴娥因为手头有急需完稿的作品,本不想接,但斯文认为值得向读者介绍,不顾身体虚弱而决定翻译。
作为“后死者”,石琴娥强忍悲痛,在思念和回忆中接过了丈夫未完成的译作。译完全书最后一句话,她没有一点成就感,反觉凄凉悲切,“再也不能在一起翻译了。终结了,永远永远地终结了”。
石琴娥家的书柜里,满满摆放着她翻译的各种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以及其他北欧文学作品的中译本。因为女儿女婿常年驻外工作,斯文去世后,石琴娥独自生活,逢年过节也会去外孙女家团聚。
北欧文学仍然是她生活的重要部分。“我不喜欢跳广场舞,也不喜欢别的,看看书做做翻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现在,石琴娥每天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吃完早餐下楼遛一圈儿,回来工作一两个小时;午睡后精神好的话,也会做一点翻译或研究。2019年,石琴娥因为耳朵前庭功能衰退引起头晕,休息康复一段时期后,又恢复了工作,“年纪大了应该要服老,但一点儿不干我也不行。只要我不生病,还是愿意做一点力所能及的”。
近几年,石琴娥翻译了很多北欧儿童文学作品,给她看病的医生朋友邀请她去自己孩子的幼儿园讲讲故事,她觉得很有意思,“我就准备把故事弄个图,到时候给他们讲一讲”。2020年初,外孙女生下一个女儿,石琴娥“升级”为曾外祖母,说起来给小不点儿讲故事的温馨时光,石琴娥满面春风,这位“曾外祖母”将会继续把那些瑰丽奇幻的北欧故事讲给孩子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