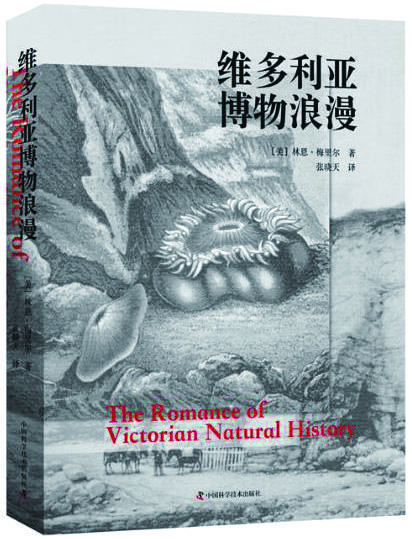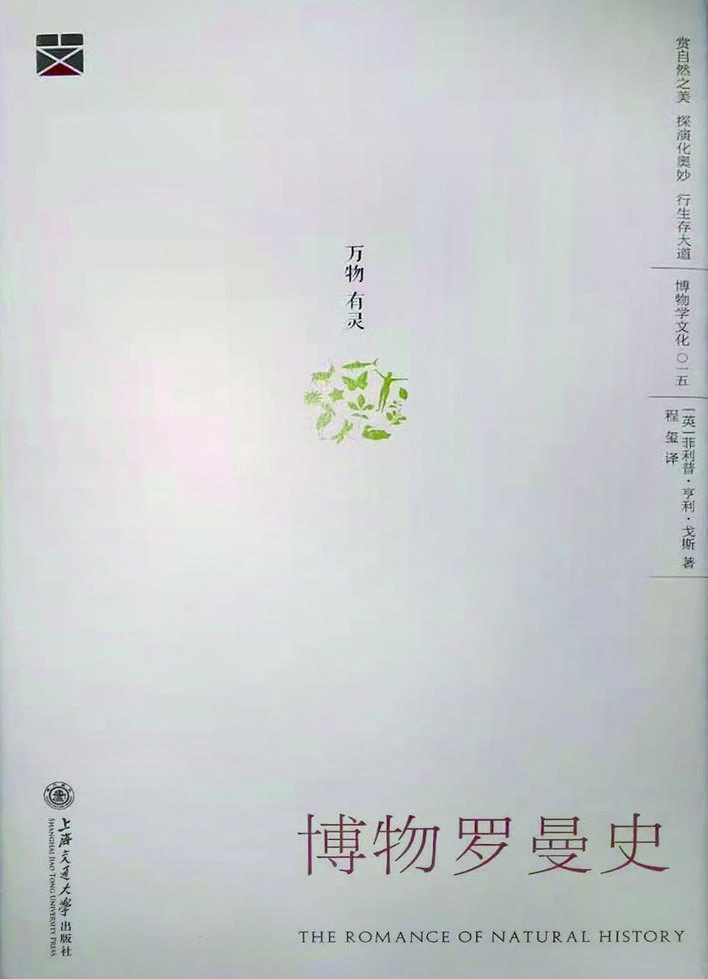最近十多年,博物学由一个冷词变得不那么冷,却远说不上热,个中原因极其复杂。我的学生张晓天新近翻译了《维多利亚博物浪漫》(The Romance of Victorian Natural History,梅里尔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内容极为丰富、有趣,可配合另一名著《博物罗曼史》(戈斯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来阅读。这本书谈的主要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博物学是个什么样子,有哪些人参与,它与新兴的自然科学之间是什么关系。这部“二阶博物学”作品的英文版早在1989年就有了,直到今日才与中国读者见面,它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博物学是个什么东西,作为个体的普通人要不要自己尝试踏入这一领域。
博物学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既容易也困难。打比方或许更直观,我想到了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中介”。
假如你相中一套二手房,对房子的历史不甚了解,对过户手续不很熟悉,对房产合同用词的法律含义没把握,怎么办?俗话说,专业事让专业人来办。于是你找了房产中介。假如你想办移民,这个也得找中介。假如你想找个女朋友,也找中介,过去有媒婆,现在有婚介所,还有各种网络平台。可是谈朋友这件事,你晓得不能全靠中介,至少中介不能代替你判断两人是否“来电”。如果中介说他替你谈了两月,亲自上阵,感觉还不错,推荐你接手并收取中介费,你接受吗?若中介说,通过他的深刻细致“考察”,A不适合你,转而推荐B,你认可中介的感受力和判断力吗?
现在让我们把场景转到人与大自然。作为个体的人,生存于大自然之中,个体是非常渺小的,一个个体如何了解大自然?对于任何生命来说,这都是个攸关生死、关乎生存质量的大问题。从出生那一刻起,你就在尝试了解这个世界。但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除了儿时有限的东跑西颠、磕磕碰碰外,了解外部世界的绝大部分工作,并不需要亲自进行,体制上早已安排好,每个人都要进学校在特定的环境下学习。学习他人、前人已经总结好了的东西,有非常多的定律和习题,学一辈子也学不完。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对大自然的直接经验比较少,少到可以忽略不计,而间接经验、书本知识比较多,多到不可胜数。一个有教养的人,特别是有科学文化的人,通常是学识渊博的人,讲起地球旋转、宇宙膨胀、引力波探测、基因编辑、量子计算,一套一套的。我认识一位物理学老师,课讲得“贼好”,但他不会、也不敢换灯泡。
对于大自然的方方面面,普通人已没有话语权。科学或者科技,在其中充当了中介的角色。它是怎样的中介呢?非常专业,平台支撑一流,颇会营销,提供的知识服务相当客观。科技如何做到这一点?说来话长,略过细节,简言之,它通过几百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取代宗教而成为现代社会最具话语权的“主体”(agent)。过去巫师、牧师行使的职责、扮演的角色,现在都转交给科技专家了。这个“中介”相当厉害,绝对不可小觑。明日天气怎样?从北太平庄到海淀路怎么走?这种植物可否食用?空气污染是否严重?那地方风景美不美?这些问题原来都要自己体验一下、试错一番而获得结果。现在简单了,不需要自己劳神,科技这个中介做得很专业,因为有气象台、手机导航、植物化学、环境监测、景观评估等专业部门和人员。
社会分工变细、中介增多是必定的,但这不意味着人注定要成为分工的奴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探索、求知的权利。人属于大自然,人与大自然之间构成特殊的关系,一个人不能不尝试以个人的方式感受、亲证这种关系。而现代教育、高科技,恰恰有意忽略了这一点,一个强大的力量时刻提示我们,别太把自己当回事,要相信专家的专业知识、意见、判断、感受。
我们今天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但维多利亚时代不是这样。
《维多利亚博物浪漫》作者梅里尔(Lynn L. Merrill)说,刘易斯(G.H.Lewes)尽管专注于文学评论和哲学,却用两个夏天在海岸线上寻找海洋生物;诗人丁尼生夸耀自己对沃特科姆湾任何微小动植物都具有亲密而充满爱意的了解;小说家兼社会改革家金斯莱(C.Kinsley)同样愿意花时间在海滨愉快地收集无脊椎物种。“无论社会名流还是普通大众,富豪或者穷人,特权阶层或是平民,都是如此。”“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发现,将博物学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几乎发展成了一种信条。作为一种爱好,博物学意味着无止境的消遣和无止境的教育,在有用的工作层面这一表层之下还隐藏着娱乐。”“面对大自然令人窒息的丰饶,博物学家享受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奇妙感。”那时,芬芳的花朵、潺潺的溪流、飞舞的蝴蝶、嶙峋的山峦,对每一个接触它们的人来说,不只是知识和有用性,还有意义、情感、信仰,令人激动、着迷。生命在大自然中舒展、行走、觅食、奔跑还有猎杀,哪怕是小鸟、小虫一般的生命也能够感受大地的丰饶、流动和风险,人更不用说。它们/他们不用特意声明探究大自然是自己的一项权利,因为他们拥有这种探究能力,也一直顺利地行使着这项天赋权利。社会化的知识当然也重要,那时各种来源的知识能够互相平衡,包括口耳和代际相传的知识,包括自己实际摸索出的知识,也包括文化人书写出来的知识。更重要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行为主体是否直接下场操练、知行是否合一。
在维多利亚时代,普罗大众所做的千奇百怪的博物学算什么?娱乐、文学、科学?坦率地说都沾边,都曾被热情拥抱过,可后来都被抛弃了。如今,多数人并不从自己探究大自然中找乐,找乐要去游戏厅、夜店、影院甚至战场,有的作家闭门就能写出30集连续剧,有的科学家压根儿瞧不上百姓的业余博物学。维多利亚时代多样性的博物探索,为近代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地质学贡献不菲,这是基本事实。科学史家心有余力之时,自然会照顾到博物学曾经为科学“圣殿”做出过一点可怜的贡献。梅里尔作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文学博士、文学史研究者,旁观了如今学界的施舍,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评论家和历史学家通常把博物学掩盖在科学的大标题之下,而这是不幸的。把博物学当作科学对待、期望它在现代意义上是科学的,对博物学而言是一种伤害,也忽略了它的非凡魅力。”
现在有学者注意到了博物学的重要性,还把它与科学联系在一起,认为有些博物学还是不错的,经过去粗取精的整理之后,还是可以归入科学队伍的,即可以化作科学的一部分,甚至有学者不无夸张地讲“博物学是完善的科学”。但这也只是少数学者的看法,多数学者根本不把博物学当回事,但梅里尔却说这样的做法是对博物学的一种伤害。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很好回答了。经过多年的思索,包括学术思想的多轮自我斗争,我可以给出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平行论”叙述:历史上的博物学,不是什么科学,它就是它自己。它并不需要依靠别的什么学术而树立自己的地位。博物学包罗万象,它施展各种探究手法,对象遍及大自然中的一切,当然现在来看研究的深度可能不够,操纵力也不够强大。那时,具体到维多利亚时代,自然科学,即今日我们从课堂、媒体、实验室、企业与政府了解到的科学,就像刚刚出生的小兄弟,虽然成长迅速,却无法独当一面,更不可能作为一种强大势力站在舞台上。宗教比它强大,博物学也比它资格老得多。达尔文、华莱士、赫胥黎、赫歇尔、莱尔等都是博物学家,当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两个称号摆在面前时,他们首先认同的是前者,那个时代的社会也是这样认同的。可是,100多年后,博物学(家)却被“不公正地遗忘了”。
T.赫胥黎十分看好新崛起的自然科学,也愿意人们称他为科学家,在“两种文化”之争中他选择了与阿诺德(M.Arnold)不同的立场,但他还是说过:“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博物学指导的人来说,他在乡野或海边漫步就如同走在一条充满奇妙艺术作品的画廊上,可其中九成他都视若无睹。你应该教他一些博物学知识,再在他手心上放上一本指导什么样的自然物值得细看的图鉴目录。”现在的情况是,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到乡野,重要的是在人工环境下学习和工作。
维多利亚博物学寻求的不全是硬邦邦的知识,“博物学家通过观察,可以将常见之物转变为神话,将平凡无奇升华到无与伦比的层面”。虽然在英国有自然神学与博物学捆绑的特殊文化背景,但是一般而言,在非基督教地区,人们收集自然物、仔细观察大自然,也会有超越性的精神收获。这种收获是无法完全通过中介获取的。现在在认知领域,在感受大自然方面,也要启动一场改革,我们不敢藐视无处不在的、作为权力话语一部分的“科技中介”,却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它,保持独立访问大自然的通道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