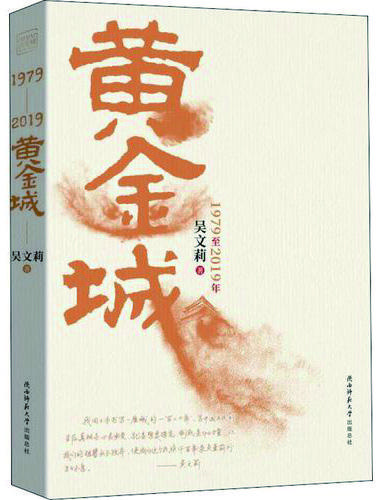吴文莉的《黄金城》在一定意义上是她的《叶落长安》《叶落大地》的姊妹篇。《叶落长安》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十几年前曾经受到了很大关注,与另外一位著名编剧孙毅安的《道北人》一样,是对上世纪初期因为各种原因迁徙到西安的河南人的生命经历的记叙。这些河南人经历了命运的折磨与艰辛,在个人、家庭和小群体的背后,是中国社会一段历史境况的写照。吴文莉之所以执著地持续书写这段历史和人物,用近百万的文字为之立传画像,起因是对这一段历史了解后的一种震惊与悸动,是一个作家的责任与情怀,是对于人类命运的一种思索和探究。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与坚持,才成就了她持续十几年对于同一题材的关注,并较为完整地呈现出了一组文集,而《黄金城》的推出,为这一系列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
正如之前作品一样,《黄金城》的书写风格一如既往地体现了一种温情。作者发自内心的关爱,在笔下倾注了亲人般的关切和对这一群体生命状态的描摹。之所以这么定义,首先是缘于作者的家庭因素,正如作者在《从西安到黄金城》一文中写到的:“他们是我的祖辈,我的外公外婆站在他们中间,我认识的许多老人都站在这段历史的边缘”。“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外婆曾和我诉说了整整一天又大半个晚上,我永远无法忘记自己面对真相时的震惊和悲痛,使命感至今依旧如影随形并令我痛彻骨髓。一心想当个画家的我,从那天决定,我须得用文字去记载河南难民们逃到这城的传奇,把他们平常琐碎的日子留在西安城的历史里”。正是这样的机缘,让作者萌生了写作的初始动机。当然,作者不是为家族或亲人立传,也不是以身边的故事作一个纪实性的书写,她是要以此为契机,进而深入并扩展,为这一群人、这一段历史进行一次创作。这是作家写作的动机和缘起,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规律,就是从熟悉的感兴趣的故事开始,进而开掘出写作的深度和广度,最终达到为一个群体、一个时代写作的目标。这样的来自家庭的初衷,加上作家的思想和修养,赋予作品以温情,也奠定了全书温暖与关怀的基调。
作者虽然深怀悲悯同情与怜惜,但笔下的描写和叙述并没有因此而主观化,更没有埋怨和抱怨的负面情绪,有的是秉笔直书、客观描叙,这是写作者素养的体现,也是成就一部好作品的前提。比如作者在描写特定年代的政治生活扭曲与人性复杂险恶等方面,虽然肯定有自己的判断与好恶,但为了作品的需要,为了尊重读者的鉴别力,作者避免了评叙,不做先入为主的议论和评判。这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自我克制,正是这种自我克制,才能客观地反映出事物的本来面目,也才能够平和流畅地展开故事、真实自然地塑造人物。
《黄金城》依然是对“小人物”“草根”命运的关注。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案头和田野调查,对他们生存、生活状态熟悉,这使得她在叙述中游刃有余,娓娓道来,让故事饱满、人物丰满。对芸芸众生生命历程的描叙中,充溢着平等、亲切甚至是家人般的情怀,既不是揭开疮疤,也不是粉饰拔高,也非诊断评判,而是充满了对大众的关怀与悲悯。没有小人物,只有小作品,无论针对什么样的人物,只要准确把握、倾情用心,都会成就好作品。特别是对于小人物、草根等很少见诸于传播媒介的群体,为他们树碑立传,把他们的故事讲好,是文学创作者的责任。
这部作品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情节描叙的绵密细致。作者以细腻的心思、不倦的笔触和极端负责任的态度,把许多细节描绘得十分全面、细致,几乎是绵密到不洒一滴水、细致到不漏一缕风,近乎于一种影像式的记录。书中的大量细节,有着十足的现场感,既能代入,又能引人回忆,这些细节对于作品整体、人物变化、发展脉络等,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给阅读带来满足感,增加了作品的丰满度。
《黄金城》对人性进行了客观、冷峻、深入的剖析和展示。一部作品,要讲故事、要写人物,更要让人感悟点什么。其中对人性的剖析和展示是最难的,因为人性本身是抽象的、又是善变甚至捉摸不定的,如何展示,就要看作者的功力。要通过对细节、情节、事件、关系等的设计,让读者自身感知,而不是作者先入为主的界定。
作品还展示了对社会生活的准确把握、对历史延展的冷静观察和客观展示。作品时间跨度很大,并且是社会剧烈变化的时间段。在这样的跨度下,能够准确把握并精准描摹,实属不易。尤其对于曾经的时间段,很多价值观念会随着历史场景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创作者,如何围绕全书的需要,调动相应的历史背景,采用怎样的观点,这考验着作者的功力。
《黄金城》所采用的穿插式的、两条线的叙述结构,把现实与过往对比,进而显现出发展变化。这种手法,如果掌握不好时机和节奏,很可能会形成割裂。但作者把握得比较准确,让现实与历史实现了无缝对接和节奏准确的“闪回”。
《黄金城》是吴文莉厚积薄发的一次丰硕收获,一部立意准确正向、风格细腻婉转的作品,可读性、思想性都可圈可点,她持续十几载的书写有了圆满的呈现,当然,这不会是结尾,一定还会有新的作品乃至新的系列不断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