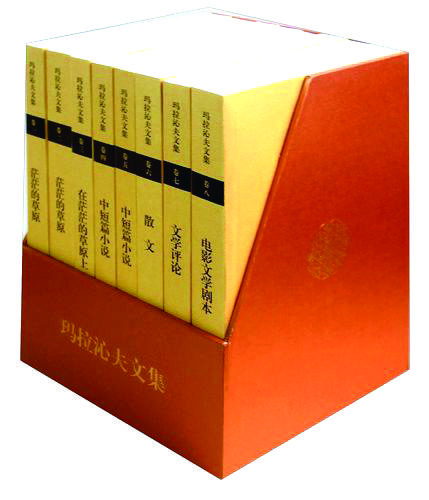在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会见卓别林大师时,请他欣赏的中国电影是《草原上的人们》。这部电影是根据玛拉沁夫的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摄制的。这部作品使青年作家玛拉沁夫一举成名,成为新中国蒙古族叙事文学的开山之作,开拓了“草原文学”流派的先河。这在全国文坛引发新奇、欢欣与轰动的效应,受到广大读者与专业人士的热评、赞誉与检验。电影插曲《敖包相会》也流年经代,广泛传唱。
从这个节点出发直至上世纪60年代初,玛拉沁夫才情喷涌,勤奋耕耘,创作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暴风雪中》《歌声》《琴声》等30多篇小说,《草原晨曲》《祖国啊,母亲!》等多部电影和报告文学《草原英雄小姐妹》。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他又创作发表《第一道曙光》《活佛的故事》和《爱,在夏夜里燃烧》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1952年开始酝酿构思,1956年定稿出版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是玛拉沁夫的代表作。作品问世数十年以来一版再版,深受各民族读者喜爱。有多位杰出的专家学者出版发表过研究《茫茫的草原》的专著,其间还有四篇成功的博士论文。从共时性、历时性各方面来看,《茫茫的草原》都臻萃为经典性作品,奠定了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卓越地位。
“经典是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每一次重读经典,都是一次发现的航行”(卡尔维诺)。最近,笔者重读了作家出版社刚刚发行的《茫茫的草原》上下部完整版,并与作者深入地进行了采访交流。在这里仅从几个维度及侧面,追溯一下玛拉沁夫在文学创作经典化道路上探索、跋涉的踪迹及其宝贵经验。
深入生活,珍藏体验,寻觅感觉,讲述记忆。1963年,老舍赠予玛拉沁夫条幅,称赞他为“草原千里马,慷慨创奇文”。1964年,邓拓在《内蒙吟草》的诗中,用“茫茫路,奔走小牧童。千里草原飞骏马,洪炉炼就一身红,努力写英雄”来赞誉他。大师前辈们的诗句,真中有幻,静中有动,不仅隐喻惊叹玛拉沁夫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也呈现了他世远年深的人生经历与文学求索的影像。玛拉沁夫从15岁投身革命队伍开始,在接受革命道理与英雄战士熏陶洗礼的同时,组织与部队尽量创造条件,提供机会,因应他的文学天赋进行培养,促进他的成长。玛拉沁夫在内蒙古地区解放战争的历程中,通过斗争生活与战地采访,积累了丰富的令他感动与记忆的人和事。这成为他烈火般创作热情的驱动力量与珍贵素材。他在重头作品中所塑造的形象性格都有鲜活的人物原型。内蒙古骑兵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和鲜亮标志之一,在新中国及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在维护国家团结统一等方面都付出过牺牲,荣立赫赫战功。开国大典时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的骑兵方队就是由这支部队的战士组建的。这成为几代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光荣记忆。《茫茫的草原》中骑兵师政委苏荣的原型,就是对作者言传身教,并亲自安排他继续学习的骑兵师女长官乌兰。
玛拉沁夫的创造,总是在深入生活中寻找艺术灵感,从感触最深的地方动笔,从发现美的原点出发。1954年4月拟好《茫茫的草原》大纲后,志在写成精品。为此,他从北京返回内蒙古,直奔察哈尔大草原,在明安旗挂职深入生活3年。1958年,国家决定建设规模仅次于鞍钢的包钢,得到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援。“这里从此不荒凉,钢城闪光芒”,“我们将成钢铁工人,把青春献给包钢”。玛拉沁夫创作的电影《草原晨曲》及其插曲,正是当时各民族青年,也是玛拉沁夫像张开双翼的神马飞向包钢、建设包钢和书写包钢热诚与激情的真实写照。玛拉沁夫在这一年把户口、组织关系都转到包钢,在这里扎下了根。在一天夜里,他被施工机器的轰鸣声震醒后,兴奋地爬起来坐在窗台倾听与观察,直到天边映现曙色。这促使他构思动笔并成功地创作了《草原晨曲》。玛拉沁夫经常说,我向往追求的不是生活的文学,而是文学的生活。他这话的意涵,可以理解为文学不在于表现生活,要旨是再现生活。照搬生活往往矮化文学的崇高属性与审美品格。玛拉沁夫在保留、过滤和提炼素材的同时,聆听辽远的声音,开拓深邃、诗性的情境。1951年,玛拉沁夫参加工作队,到辽阔、美丽与富饶的科尔沁草原做群众工作。刚到那里不久,一位休产假的牧民妇女斗智斗勇,捉住越狱逃犯的动人事迹轰动了草原。玛拉沁夫深受触动,萌生以这个素材写一篇小说的冲动以后,一是没有匆忙动笔,二是没有去直接采访那位英雄妇女,而是广泛深入地观察了解草原牧民当家做主人的整体风貌,体验时代社会保卫胜利果实、肃清残余敌特的浓烈氛围。写作中又反复过滤打磨,借鉴经典作家的经验,力求简洁精练,把42000字的中篇小说,浓缩成14000字的短篇小说,这就是作品《科尔沁草原的人们》之生成。这种文学本体性的自觉遵循与严谨的创作态度,规避了时代环境未必典型,导致作品仅是一时一势生活语境的附和或者虚假的标配,甚至造成把文学创作贬抑地视为好人好事的浮泛宣传。因而,作品得到《人民日报》具有文学高度的评论:“写了新的主题、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先进力量,用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
文学创作经典化之路,不可或缺的途径是学习锤炼语言,开阔文学视野,刻苦阅读名著,专心学习经典,汲取创作经验,提高写作技巧。原本不懂汉文汉语的玛拉沁夫从15岁开始学习汉文。他通过学习汉文学习文学,又通过阅读文学学习汉文,并摸索出学习汉文的独特方法。但他也始终珍惜自己的母语,精通蒙文蒙语。汉文、蒙文的书法都颇具功力。他在两种语言间穿梭,互补互促,相得益彰。在书本与民间撷取并融合各种语言的无穷奥秘与优质元素,在创作上形成语言的新奇性、丰富性、超越性与流动性。在组织的安排下,玛拉沁夫1946年到内蒙古自治学院学习,1952年到丁玲任所长和导师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在这六七年及其后的岁月,无论是在院所,还是工作之余,他的决心与行动就是克服困难、创造条件读书、读书、再读书。没电、断电时,他点油灯读书,有时沉浸读书时只睡两个小时。当年,有位同事大姐送给他一件缴获的日本军大衣,他立即卖掉购买蜡烛用以照亮读书。当初,他如饥似渴见书就读,选择性并不强。当后来得到与他创作意趣、艺术感觉有共鸣、相契合的书籍时,他简直读到走火入魔的境地。然而,文学创作是讲求艺术追求与个性的。当谈到阅读名著与自身创作的关联时,玛拉沁夫认为,既使令人崇拜与敬仰的作家作品,如果与自身的创作题材、创作志趣不大对路时,你也会有陌生与疏离之感,文学创作忌讳的是盲目追随与蹩脚模仿。他坦言,最早使他产生亲近感的作家是萧军、惠特曼、杰克·伦敦与屠格涅夫,而令他震撼并被其征服的作家则是肖洛霍夫。精读《茫茫的草原》以后,读者应该会体会到肖洛霍夫式的恢弘构思、广阔丰富的草原情境、复杂跌宕的人物命运、深邃的时代内涵与强烈的艺术魅力,也能领略到《八月的乡村》那样对苦难的真实描绘,还能感受到杰克·伦敦的粗犷与惠特曼的激情之艺术气质。
1962年,茅盾在评论玛拉沁夫作品的万言长文中说:“玛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积累,同时他又富于诗人的气质,这就成就了他的作品的风格——自在而清丽”。玛拉沁夫的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俄、德、日等多种文字,走向了世界。虽还不能轻言《茫茫的草原》,可以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屠格涅夫的《白净草原》、契诃夫的《草原》以及艾特马托夫的《草原和群山的故事》等相媲美,但《茫茫的草原》确已呈现出与之相近相似的艺术风貌与品格。这无疑是献给中国与世界文坛的华彩篇章,成为新中国“草原文学”的范本。
玛拉沁夫传承、遵循的是中外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自觉追索、践行的是恩格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之创作原则与美学理想。作为入党74年的老党员,玛拉沁夫对于党性与文学的本体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清晰的时代意识与文学表达的艺术性、民族性书写与家国情怀等诸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都有哲理性和正向性的把持与坚守。这既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上,也渗透于他的文学管理工作中。他在文学领域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等重要职务,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他牺牲个人创作的时间与精力,呕心沥血、竭诚尽智,在推动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在培养一代又一代民族文学新人诸方面居功至伟、贡献卓远。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是他率先同其他几位少数民族作家一道,把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升到新的高度,推向新的发展繁荣。同时,也丰富与扮靓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景观。
“共时性”与“历时性”本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术语。原义是说人们集体意识的认同,与没有觉察到的相互关系之联系性及持久性。把这个借用于文学评论上,则是指代经典性作品诞生时为一个文化群体与广大读者所接受和喜欢,并可以流年经代地产生更加广泛的认同与影响。随着时光的推移,相信玛拉沁夫及其创作会在更大层面造成积极影响,成为我国当代文学推动性与丰富性的一个元素。同时,以玛拉沁夫等为代表的优秀民族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也为国家全面的发展进步,为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宝贵的人文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