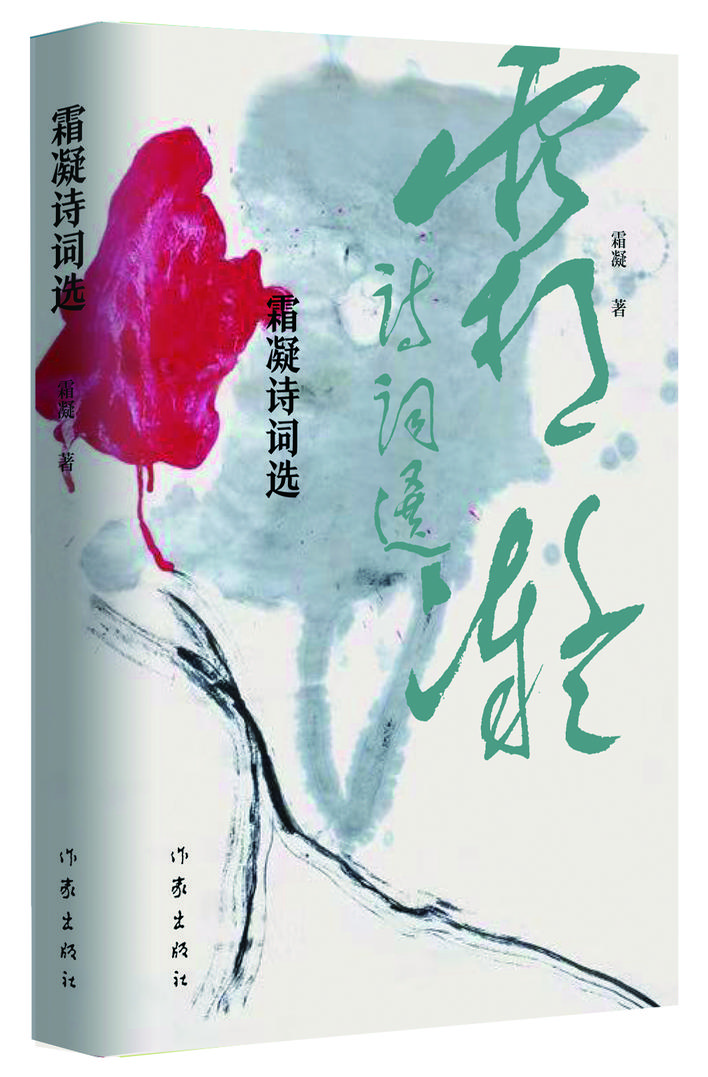我从小喜欢诗书画、文史哲。诗,写过古体、旧体、新体,既写诗,也填词。算起来也有几千首吧,但大多随涂随丢了。退休后有了闲暇,找到300多首,主要是近几年新作,承蒙作家出版社抬爱,出版了《霜凝诗词选》,贺敬之先生题写书名,叶嘉莹、郑欣淼先生为之作序,自是非常感谢。
我现在能找到的最早的诗作是1966年不满12岁时写的《闾山》:“期期心相闻,今日觉尤亲。峰上松烟霭,阶前草碧茵。石棚飞瀑泻,海寺白云真。恨见时虽晚,闾山有后人。”但坦白交代当时并不懂什么平水韵,原作是这样的:“期期早相闻,今朝始登临。山上松似烟,岭下草如茵。石棚泻飞瀑,海寺拂流云。相识恨见晚,枉为闾山人。”平水韵这首是后来修改的。
我虽喜欢诗书画、文史哲,但命运弄人,却从事了一辈子金融工作。说来话长,起因是1978年恢复高考,我时任一家工厂的宣传干事、党办秘书。当时文科高考共五门: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按说政治题对我是小菜一碟,二十几分钟就答完了。但当时没好意思立即交卷退场,第一遍的试卷觉得有些潦草,索性就又抄了一遍。抄了不到一半,已经过去一个小时。当时不知哪根神经作用,觉得可以退场了,就没再继续往下抄。退场时规定卷纸不准带出,两张券纸就都留在了考场。结果一张判了90多分,一张判了40多分,按40多分的试卷计算了总分,并被当时的辽宁财经学院今天的东北财经大学录取了。当时允许查分,经查发现了少计四十多分,经向招生办交涉,承认了计分有误,但当时录取已经结束,征询个人意见,如果不愿意被录取可以明年再考。事已至此,就这样走进了财经院校,毕业又被分到基层银行,三十出头就当上了处级干部,四十几岁又从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任上调到总行,把当时央行货币政策、支付服务、金融监管三大职能的司局长全干了一遍后,又成为了中国银监会的副主席。在此期间,别人眼里已是时代的宠儿了,自己当然也是心满意足,唯有一憾就是自己的所爱不敢拿到台面,怕被说为不务正业。但兴之所至按捺不住,业余也创作了不少。2006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30周年的日子。我们这一代人对周总理有着特殊的感情。那天早上,大概四五点钟,不知什么原因,我突然惊醒,无论如何也睡不下去了。我下意识地打开电脑。我过去从来没有在这个时候打开过电脑。我突然发现,这天是周总理的忌日,是周总理逝世30周年的忌日。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0年了,网站上的留言像雪片一样,怀念,怀念,无尽的怀念;我的泪水像潮水一样,止不住,止不住,无论如何也止不住……我就一口气写下了这首长诗《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附后)。
这首诗传播很广,很多微信公众号都是10万加。最近手机的一个微信群里的一个朋友,偶然在北海公园还拍到一位老人向游客朗诵这首诗。看到这条微信我当然也十分欣慰和感动。这是后话。
2007年光大集团资不抵债濒临破产,中央派我去救火,出任董事长兼党委书记。中央的决定我必须服从,但个中苦衷唯有自己知晓。按照当时业界的普遍说法是光大“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谁去都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本来原来工作正顺风顺水,突遇此变,一首《沁园春·三峡大坝泄洪有感》,很能说明当时的复杂心情:
呼啸西来,盖地铺天,万里马嘶。却横天一坝,迎头矗立。忽闻四面,故楚歌吹。末路英雄,佳人相对,垓下凄凄泪别离。抬双眼,任平湖如镜,忍做催眉。
说人且莫伤悲。昔勾践柴薪尝胆时。聚江东子弟,西陵解锁,千堆白雪,大浪如狮。落叶西风,旌旗漫卷,横扫荆襄事可期。凭韬悔,若包羞忍耻,便是新碑。
到光大集团工作后,真正使我彻底想通的还是那首《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和周恩来精神——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思想通了,一通百通。到我2017年退休时,光大集团已成为世界500强企业。当时的一首《相见欢·梦中秋》,就是自己个人的内心独白:
恍惚一梦床头,又中秋,十载圆缺多少喜和忧?
夜难寐,婵娟泪,未空流。堪慰终圆顶上小银钩。
退下来后,我的上述个人爱好也从“隐蔽战线”转入公开战线了。家中小院有个篮球架,偶尔投投篮,写了一首七绝:“未到中秋月不圆,婵娟寂寞有谁怜。廉颇小试仍能饭,一路扶摇上九天。”晚上家中茄子黄瓜就小酒,也吟上一首 “翡翠黄瓜碧绿光,仙茄紫气百回肠。银丸圣薯红须麦,金酱琼浆玉液香。”体检指标正常,更是高兴地唱出“莫笑当年楚女痴,春风吹瘦柳条枝。老身几度频重组,飞燕廉颇未可知。”
我诗词创作的体会,第一,诗言志,诗是生活的产物,更是内心的表达。庚子春突发新冠疫情,我写了100多首旧体诗词,《忧全球疫情》写到“频传羽檄小球危,独锁家门面壁痴。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遍相思。云缠高阁天来赋,雨打西墙地落词。砖石生情忧作句,一楼土木一楼诗。”一首《渔家傲》还写到“霪雨绵绵天裂缝,残烟缥缈熏风动。最是今年阡陌痛。瘟神弄,桑麻惆怅人沉重。四海疫剳悲与共,玉盘恰似相思洞。心事一楼谁寄送。愁难控,耕云锄月忧心种。”另一首《庚子惊蛰》写到“惊蛰春风笼万家,山披阳气水披纱。雷行天裂江吞雨,耜走田开垅吐芽。新柳将飘新柳絮,老杨欲放老杨花。不知何日龟蛇醒,云梦湖边共晚霞。”武汉解禁时,又写了一首:“大湖襟抱向天开,地展星罗十万枚。华夏一盘同布阵,荊襄千里共驱灾。连波楚水西江溯,接脉巫山北岭来。云泽唏嘘情一盏,龟蛇泪雨祭三杯。”没有抗击疫情的伟大斗争,是写不出这些作品的。
第二,诗是诗人的不吐不快,诗人一定要有真性情。苏东坡因乌台诗案,曾发誓不再写诗,可本性难移,一出乌台,就吟了一首“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苏东坡就是苏东坡。他的真性情就决定了他一定要一吐为快。反过来讲,没有真性情,就写不出好诗。苏东坡因“日啖荔枝三百颗” 、“报道先生春睡美”,而遭嫉一贬再贬。我为他写了一首《读苏轼〈纵笔〉诗》“愈是才高愈是痴,道人好意谪人悲。藤床小阁依然睡,只管听钟莫写诗。”他如果只啖荔枝只爱春睡,不去写诗,也没人会再想到他。可苏东坡就这个秉性。只是我们现在同苏东坡的时代不同了。这是诗人的大幸。
第三,诗书画一体,可以打通,打通后是可以互为促进的。书法挥毫的同时,我吟出“斗室苍茫起紫烟,心河九曲任蜿蜒。毫锥裂岸雷霆滚,尺素崩涛赤电穿。志在八荒无酒醉,神充五内有人颠。游魂已附龙蛇去,不记霜凝不记年。”泼墨丹青我也写了很多诗词,特别是我近年迷上了抽象绘画,我认为艺术的本质是美,艺术特别是抽象艺术,是人类共通的精神语言。这种美可以打破宗教和各种文化差异的边界,为人类共同接受。 如果一般艺术由于阶级、种族、宗教的原因难以被人类共同认同,那么艺术中的抽象艺术,可以把人们从阶级、种族、宗教等各自不同的具象外化之中抽出来,抽出人类共性的真善美,抽出人类的心中之象,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我的抽象绘画分为反皴画法为主的宇宙万象系列、泼皴折流画法为主的知白守黑系列、泼染画法为主的大美自然系列、皴擦画法为主的现代抽象系列等。我自以为之所以迷上了抽象绘画,与我的诗词爱好有很大关系。
诗有诗源、诗魂、诗容。上面说的诗是生活的产物就是诗源,诗言志就是诗魂。诗容,我以为可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韵律。我以为如果不讲韵律便不成其为诗,或可称为散文。二是旧体的平仄、对仗、押韵。既然是旧体,既然冠以绝、律、词牌,就要严格按平水韵,词林正韵的要求去规范。旧体当然也可以用新韵,但要标注为好。三是赋比兴。赋是铺陈叙事,比是比喻、类比,兴是托物言志。对于诗容的平仄对仗押韵,我以为既要知律依律,也要在关键处不为律所缚。如苏东坡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将五、四、四断句写出“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后人王国维评论此词才情境界凌驾原唱之上,同侪晁补之称“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清人赵翼云:“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种知律依律前提下的关键处极例又不为律所缚,使苏东坡能跳出词浅吟低唱的条条框框,自开一派。
当年霜降时节,我写了一首“离雁声声翅未收,凭空抖落一天秋。公平最是霜天降,地上谁家不白头。”白头,是自然规律。“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白头绝不是消极。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提出“诗意的人生”。白头,通过诗意人生可以重新染就。
末了,我想借《霜凝诗词选》的出版,借这篇小文,祝所有人都能过上——诗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