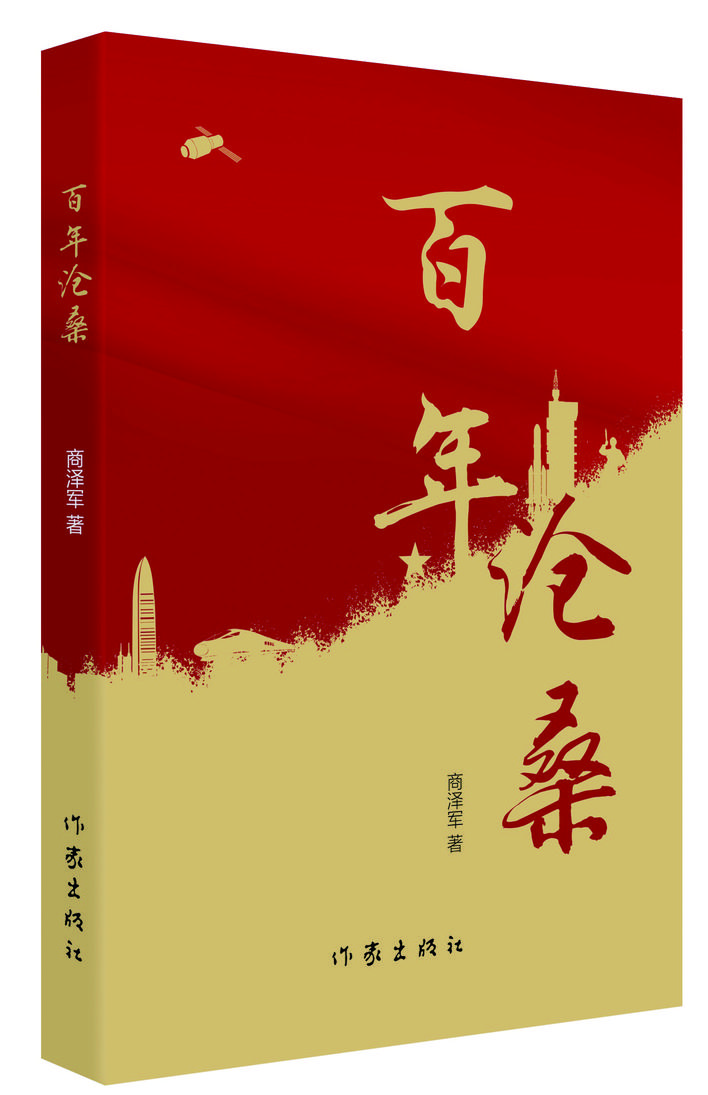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作为新时代精神的诗歌,自然对新时代的反应更敏感更直接。自《诗经》楚辞起,中国诗歌有自己的传统基因,家国情怀、江山社稷,一直是诗歌的主题;虽然近百年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的诗歌形态变了,从旧体的格律的,转向了新体的、自由的。但是中国诗歌接受了新的营养,使它变得更加自由、更加贴近时代。看五四时期郭沫若的《女神》就明白,他诗歌里表现的是五四时期,那种冲破一切旧的势力、封建道统、三纲五常、枷锁镣铐的狂飙的精神,是自由、科学、民主,五四时候的诗歌,是时代的喉舌,是时代精神的代言。那时的诗歌就是从半文半白中走出,那自由的诗行,就是五四的自由精神。而抗战时期的街头诗,更是对鼓舞民众、揭露敌寇的罪恶起到军号战鼓的作用,我喜欢诗人艾青的《火把》《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更是诗歌史和抗战史上的丰碑。新中国成立后,《雷锋之歌》《青纱帐甘蔗林》,以及食指的《相信未来》等一大批诗歌,莫不是对时代的回应。对我个人来讲,我一直信奉,诗歌是诗的,个人的,也是时代的,社会的,诗人不能独立于时代和社会之外。随着阅历的丰富,我更加相信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除掉个人的喜怒哀乐,更应回应时代,承担起时代之使命和责任,从屈原到杜甫,到龚自珍,这些诗人,无一不是从情感和思想上,与国家民族同频共振,在国运不昌时候,探索救国救亡之路,讴歌光明鞭挞黑暗,唤醒民众,歌赞进步。从我的阅读史和创作史,我是这些诗人的学生,这些诗人的血液也一样流淌在我的血液中,这就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当这片土地受到伤害,就像我自己受到了伤害,当这片土地收获了成功,就是我自己收获了成功。当孔繁森牺牲的时候,我写下长诗,怀念这位曾帮助我办文学社的三哥,歌赞他的质朴,他的三次进藏;当1998年夏季大洪水肆虐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到了长江的堤坝,自身感受那些军人的血肉之躯对抗百年不遇的洪水;当五环的旗帜飘扬在北京上空的时候,我的笔也没有缺席。我知道,我的诗歌是和这个时代互相塑造的,时代是我诗歌的根脉,我的诗歌,是时代的回响,所以,当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时候,我首先在脑海里回旋的是回望来时路,这百年的沧桑,从几十个人到9500多万,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凝聚,又是什么信念,把他们聚合在一起?我曾到过一大的会址,也曾漫步在南湖,曾驻足南昌城头,也曾重走长征路。在这个百年纪念来临的时候,这一切,都如燃料在我心中燃烧。我知道,时间是有分量的,一个政党,百年来,不忘初心时时在前行。从百年前的那个热血青年,从走上街头,为民族的未来奔走呼号,到十字街头到安源煤矿,到百姓的田间地头和炕头,宣传奋起抗争、改变命运;到民族危亡,在延安窑洞、太行山上、林海雪原,有多少党的儿女,为国捐躯;在和平年代,在两弹一星的行列里,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又有多少故事,被这群优秀的儿女演绎。百年,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也是反思、记录、铭刻的日子。记录的方式很多,作为一个诗人,更应该用诗行来铭记、来雕刻。我决定,用长诗的方式,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用一个个的点,来反映一条红色脉线,来反映这个大体量的伟大征程。为了避免粗糙化、脸谱化,我选用一些细节,为避免同一题材的撞车,我在情感、哲理、形式等方面,浸泡我的题材,为了反映这宏伟的100年,我选择高亢和委婉的谐和,来扩大诗歌的张力。无疑,红色题材,是一个个作家熟悉的题材,如何在这些题材里出新,这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这里面既有写什么的问题,更有怎么写的问题。我最大的苦恼和思考的突破,就是如何避免这类题材的同质化,要写,就写出一个别样的百年沧桑,写出一部提气、提劲、能立住脚的作品,这样,才与这百年英雄们的丰功伟绩相匹配。党的百年史是一个富矿,当写作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在写,而是土地,而是江河,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诉说,在歌唱。那些奔腾的血、那些抗争不屈的灵魂,那些从《新青年》走出的年轻的身躯;那些船工们,那些船长们,那些波澜壮阔的惊涛骇浪,那些呐喊,好像都一起奔涌到我的心底、眼前、笔端。我觉得,创作好的新时代诗歌,也是经过心灵浸泡,经过思考,然后情感和灵感的大爆发,犹如地下涌动的岩浆,有了一个突破口,一个契机,就一下子爆发了。这个契机,可以说是时间的节点,这100年的长度的节点,但这些积累,却是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累积。没有什么一蹴而就,有的是平时的汗水、体验、阅读、思考。所谓的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在诗歌里,我努力反映一种精神,一种魂魄,这里面有对一个政党百年的回顾,更多的是这个政党与民族和人民的联系,写下了那些对民族尊严的探索,对民族乃至人类未来美好的憧憬和奋斗。诗歌里的精神,不仅仅是诗歌的,它比诗歌大,它是百年的历史沧桑,它是一个政党百年的缩影,如果我的诗歌能达到一点点,那我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