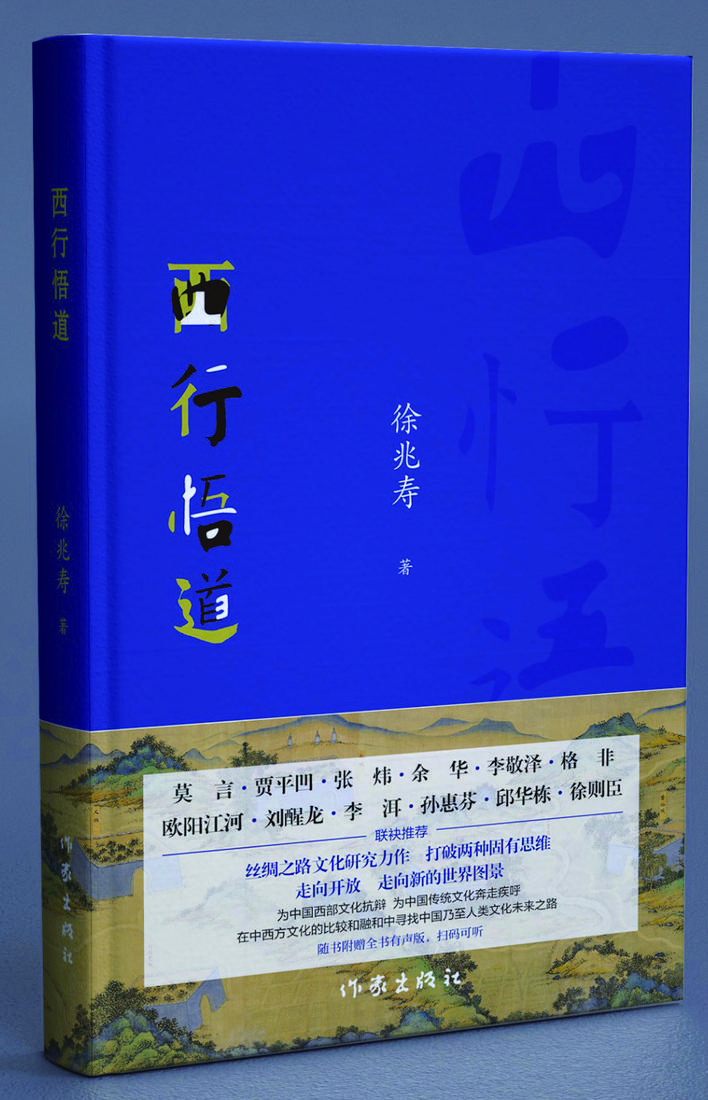从《荒原问道》到《鸠摩罗什》,再到《西行悟道》,徐兆寿一直在“西部”耕耘,这“西部”不只是指地理位置上的西部,也指他笔耕不辍多年中“发现”和“定义”的西部的精神气质与理想观念。“生命中必须有一块地是荒芜的,它不是供我们来用的,而是供我们实在的心休息的,供我们功利的心超越的,供我们迷茫的心来这里问道的。”从地理环境的辽远和疏阔中寻找精神力量或追求灵魂救赎并非新鲜独创,甚至容易落入地域偏差的陷阱,徐兆寿的特别在于致力于从荒芜西部的山川河流、荒漠苍林中追寻文明起源的秘密,甚至是文明起源之前,“人”与“天地”的互动。徐兆寿并非要做历史学或人类学的学术考察,而恰恰是要在既有的学术体系之外重谈“怪力乱神”,重塑辽阔的西部世界的另一种天地情致。
在徐兆寿笔下,西部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天马,有乐舞,更有骁勇善战的各个民族部落。诸神纷争的年代,西部世界崇尚野性、自然、随心所欲,游牧民族的“草原往事”为中原文明输送了元气,但古老的蛮荒力量却也因中原文明的兴起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封建血统对原始道统的凌驾是进化论角度的前进,却也是对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天道自然的遗忘。徐兆寿首先击碎的,便是今天的我们习以为常的文明中心论,不管是西方的欧洲文明中心论还是中国的中原文明中心论,徐兆寿为我们揭开被黄土尘封的文明故事,甚至是史前故事,为我们讲述文明的变迁与变迁之中人类思想精神的漫游。
《何谓究“天人之际”》是文集中相当重要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徐兆寿借参观司马迁墓的机会与学生讨论什么是“天人之际”,一问一答之间颇有《论语》中孔子与弟子对话的意思,在形式上更是风雅十足。文章讨论司马迁对天、人的理解,其实是今天的我们对司马迁的理解的理解,我们观察的是比我们睿智得多的古人如何看待他那个时代的未知,而这未知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算不上难题,或者说,有很多人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这一难题的答案。从董仲舒的视“天”为准宗教到司马迁的认为上天并非不可把握,而是有规律可循,徐兆寿其实是向学生介绍了“天道”的意义,而与这种意义相关联的,是《周易》,是河图洛书,是古人对世界的认知,“八卦与《易经》的真理在于,将人视为天地之一物,与天地运行的真理相通,即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是徐兆寿想要厘清的古人的思维方式,是他们如汪洋般的大智被今天的我们悄然忽视的事实。这也是为什么在《佛道相望》一文中,徐兆寿再次讲起孔子与《周易》的关系,信奉“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晚年进入《易经》的世界,“将变化无常的命运与人的道德合为一体,将功名得失也与人所遵奉和履行的道德视为因果关系”,儒道实现了思想根源上的契合,它们两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便是佛家的用武之地,佛家最为圆满地回答了人类的终极追问。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已经不再时常想起的时代,伟大的先圣们为我们完成了怎样艰难的功课。而这三家的起源与流变都与西部有关,从《易经》创始人伏羲的民间传说到天水麦积山石窟的佛像,儒释道三家的疑问与对疑问的认知、解决始终扎根于西部大地。流水带走光阴的故事,却终究要留下痕迹,徐兆寿跟随痕迹溯流而上,追寻古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旨归今日人类精神与灵魂无根飘零的困境。今天的我们还有可以依凭而能无困惑的“天道”吗?今天的我们身处繁华都市还能欣赏文明起源的荒芜落寞吗?今天的我们还有兴趣,还有能力了解圣人的言行与智慧吗?
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寻找昆仑》理应是本书的压卷之作。如果说《何谓究“天人之际”》中老师与弟子有《论语》的风雅,《寻找昆仑》中与“科学朋友”对话的思辨逻辑则有柏拉图《对话录》的风采。由中及西,由古及今,打破文明中心论的徐兆寿又在这里打破了科学与现代性的神话。徐兆寿在行文中不断质疑,当我们身处物质极度丰富、科学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是不是就可以完全依赖现代的知识,不用再去考量那些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更不用说那些带着神秘色彩的远古奇谭。昆仑是什么?是名山,是古书中的文明发源,是无数神话传说的皈依,“为什么从古至今的中国人都在寻找昆仑,不仅仅在寻找原始之地,还在寻找缘起。用你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初心之地。”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我们沉迷于对“新”的命名,是要给时代和群体一次次重新出发的机会,却也是一次次将过去和历史抛在身后,今天的我们倡导“不忘初心”,倡导“文化自信”,其实正是一次有意义的纠偏,回看初心,回望曾经使我们骄傲的文化与历史,不是要沉迷于过去的功劳簿,而是恰恰通过回眸的过程发现形塑这些文化与历史的观念,重温那些被今天傲慢的我们嗤之以鼻的信仰。也是以此来回到徐兆寿的终极焦虑,“中国文化到底还能不能给中国人以未来?还能不能说服世界并造福人类?”
理解历史与过去的终极方法便是找寻真正的“源头”,“昆仑”也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象征的能指,我们并不是要找一座实实在在的山,不是要去印证《山海经》和上古神话里的确切位置,而是去理解对“昆仑”的定位本身蕴藏的古老的对于天道运行规律的认知,理解天干地支、五行八卦中的规律与考量,理解古人在对自然万物观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敬畏、自信,理解他们对个体与外界关系清醒的界定与寄予浩瀚苍穹的伟大愿景。如此,我们又有何底气和资格去厚今薄古,有何信心和胆量去盲目崇拜西方与科学,有何必要和需求去沉溺焦虑与恐惧?
也是在真正试图和古人亲近的过程中,我们理解了身为后世子孙的我们的诸多执念,如对国家统一的认知,并不是源于某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过激的其他情绪,而恰恰是“国家观”之外的“天下观”,是“天下就可分为九州,这是以天的形象来进行的,这就叫地法天。而人也是九宫形,这就是针灸学和中医学的基础。所以说人法地。那么,天又法谁呢?自然。”似有豁然开朗之感,那些被西方民主科学思想规训过的理念突然间有了动摇的预兆,久被修饰的现代灵魂似乎有了返璞归真的可能。我们的生命多久没有触碰真正的天、地、自然?
也许,从精神层面来讲,没有文字记载的漫长的史前史是人类最美好的时代,因为在艰难岁月里,他们拥有美好、坚定的信仰。他们的心灵有如大地一样朴素、动物一样单纯、神一样灵敏。他们简单、纯一。也只有那样单纯的心灵,才能与天地通灵、对话,才拥有最为明亮的眼睛看到星空的变化。在黏稠的时间里,他们对时间和死亡的态度定然与我们现代人有着质的区别。因为那样,他们才创造了天人合一的太初哲学,保持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绝对统一性。
“寻找昆仑”的过程也是不断与“原初”“太一”“起源”等概念重逢的过程,更是一个需要不断质疑自己和重新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我们重审古人的“天”“人”之“道”,重审儒释道的价值起源,反省红尘之中的自我德性的缺失与言行的傲慢;我们重寻“初心”,重寻辉煌灿烂的文化在创造之初被赋予的逻辑与规律,扪心自问我们对其无情的误解与抛弃。徐兆寿在这样的双重意义上终于实现了对“鸿蒙之初”的重返,对赤裸、真实、纯真的复现。行文中当然也还带有过于敝帚自珍的偏见,或许多少有自证自明的想象与执念,但在共情与纠偏的基础之上,这种重返有足够的价值。不管是天地玄黄还是巍巍昆仑,混沌年代的太一是人类作为生灵的起点,也是之后逐渐偏离“天道”“自然”的开始。徐兆寿并不奢望人类在回望自身的过程中真正实现对原初一切的回归,而恰恰是希望以此抚慰当下,更烛照未来。发现来处的清晰与透亮,才能更好地走向明天的光荣与梦想。“最重要的是打破封闭思维,要走向开放,走向世界图景。”或许这才是徐兆寿真正包容的人文情怀与西行路上悟出的天地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