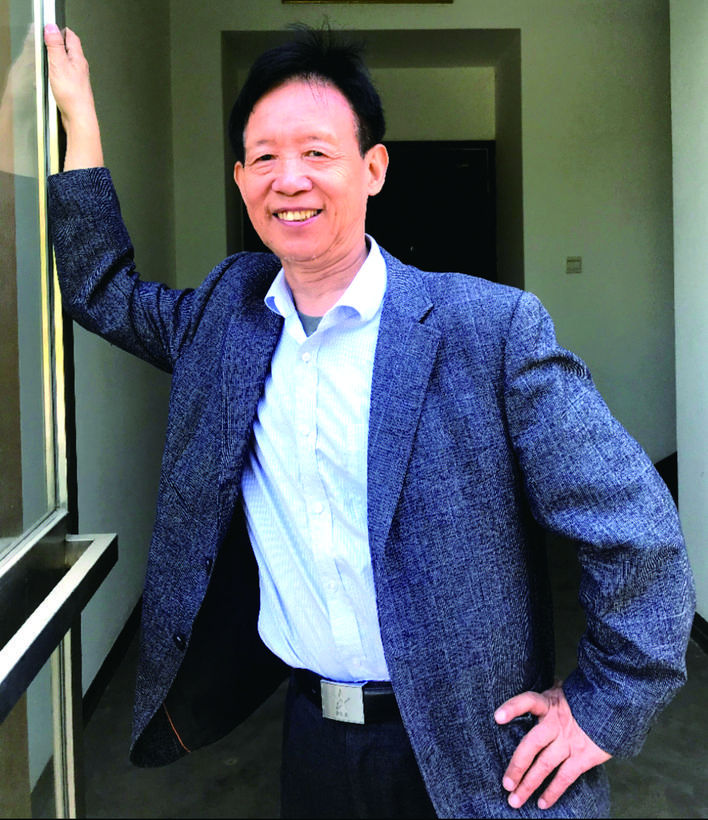2015年,我承担了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撰写解说词的任务,近一年的时间,我阅读了大量各种版本的抗战史料及相关文学作品,梳理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关于中国抗战的诸多特点,其中有开战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等。说开战时间最早,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打响了反对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与1939年9月1日德军闪击波兰,相较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早了8年;说持续时间最长,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抗战坚持了14年之久;说付出的牺牲最大,是指东方战场而言,中国抗战中伤亡3500万人,损失5000亿美元。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毋庸讳言,在中国上百年来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惟抗日战争是最旷日持久的,也是最悲壮惨烈的,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最具“民族秘史”意义的一部分,它积淀成的文学富矿深厚而复杂,血腥而悲怆,为作家们深入持久的开采,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如果梳理一下中国抗战文学史,就不难发现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这座富矿里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开掘,在深耕细作中,淘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中国抗战特色和品质意义的文学黄金。再做进一步梳理,大至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抗战期间,从解放区到敌占区,从国统区到抗日民主根据地,一大批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出了许多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如《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四世同堂》《吕梁英雄传》《风云初记》等。第二次浪潮,就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也称作十七年),这次浪潮来得相对有些猛烈,创作者大都参加过火热的抗战斗争,全国解放后,他们过上了安定日子,静下心来写了一大批主题鲜明、故事曲折、可读性强的抗战文学作品,如《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苦菜花》等。第三次浪潮是新时期以来,一些没有参加过抗战,却有较强实力的作家,他们依据阅读史料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写出了一批具有新的战争理念和某种反思意义的抗战文学作品,如《红高粱》《亮剑》《历史的天空》等。这三次浪潮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战文学景观,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创作的抗战文学作品,再现了不同的战争场景和面貌,留下了不同特点的抗战英雄形象,不仅丰满了中国抗战文学史,也生动形象地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客观地说,作为军旅作家,我是第三次抗战文学创作浪潮中的一员,我的家乡冀中平原的热土曾被抗战的烈火燃烧过,被英雄前辈的鲜血浸染过,我是听着父辈们讲着打日本鬼子的故事长大的。参军后,我所在的原北京军区部队前身是晋察冀军区,而冀中是晋察冀军区的腹地,也是产棉产粮的富庶之地,为华北敌后抗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战争资源。1942年,新上任的日军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扬言要摧毁八路军的战争血脉,用五万大军报复百团大战,对冀中平原进行拉网式、篦梳式、鱼鳞式清剿,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这就是抗战历史上的冀中“五一”大扫荡,那次大扫荡日军共杀害和掳走冀中军民五万余人,其惨状如电影《地道战》中所描述:“迈步登公路,抬头见岗楼。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也正如我的父辈所说:“那真是推了碾子又上磨,过了筛子又过箩,老百姓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简直就不让你活。”可我英雄的冀中父辈们,凭着血性、顽强和智慧,喊着:“今年消灭希特勒,明年赶走小日本儿”的口号,在“三光政策”中挺过来了,熬过来了。经过十几年的思考沉淀,2012年我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血地》。在我的小说面世前,关于反映冀中抗战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在三次抗战文学浪潮中已有相当多的数量,而且有着广泛的影响,面对无法超越的“大山”,我只好另辟蹊径,我把目光投入到民间抗战中去,投入到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身上。这些人物几乎都没有高大全的英雄痕迹,而且在他们身上还存有某些人性弱点甚至斑斑劣迹,平时一片散沙,窝里斗,而抗战却把他们拧成绳子,一旦遭受外辱,他们便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在他们身上,闪耀着朴素的爱国情怀和人性光辉,如红军团长出身的李长生虽文武双全,不计杀父之仇的家恨动员村民抗战,却死活走不出亲情与爱情带来的尴尬;侦察员铁榔头嗜酒如命且与村里的小寡妇有染,但在反扫荡中站出来舍身掩护老百姓毫不含糊;大学生出身的抗敌剧社社长郭文秀因忍受不了李长生对她的批评连夜开了小差,在外一路寻找“实业救国”无果满怀羞愧归队;风流成性的小白鞋,大屠杀中本来能活命,却回头扑向从死人堆里站起来的铁榔头,两人双双倒在鬼子的枪口下;当了汉奸的小刺猬最后良心发现,阻止鬼子扫荡未果杀身成仁……这些人物构成了《血地》具有民间色彩的抗战英雄画廊,他们把战争作为一种平常日子过,就像他们自己编的歌曲那样:“死了的已经死了,咱活着的接着活,该吃咱还吃,该喝咱还喝,该唱咱就唱,该乐咱就乐,气死小日本儿,解放全中国……”这就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过活的冀中人,这就是被战争动员起来的庄稼汉,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一边打仗,一边干活,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的祖先埋在这里,他们要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这片热土。任何凶残无道的敌人都不能来惹他们,一旦把他们惹翻了,就会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如今抗战胜利已经76个年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研究抗战的史学家到从事抗战题材创作的作家,再到民间的普通老百姓,都对这场战争有了更加客观、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认识,虽然中华民族百余年来饱受外来欺辱,但都没有抗日战争给我们留下的精神创伤更为痛彻,对我们的民族尊严伤害得如此无以复加。清代文人赵翼曾有这样的诗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正因为中华民族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才沉淀成深不见底的抗战文学富矿,但回过头来看,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们虽然经历了三次开采浪潮,也创作出了如上所述的诸多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但跟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受的那场深重灾难和付出的沉重代价相比,仍是不太匹配的,或者有说不出的遗憾,我们从心底里呼唤,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够出现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世界名著那样鸿篇巨制的抗战文学作品,像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一样彪炳显赫,但这只是一种愿望,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作家大都作古,即使健在怕也力不从心,而我们这些依据史料加想象的作家,经过几十年的阅读、沉淀与思考,承担起这一使命,并当之无愧地留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但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作家写历史,首先要研究历史,走进历史,而作家与史学家所肩负的使命不同,作家要通过文学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再现历史,让历史成为一种叙事背景,人物的命运发展处于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也就是说,作家不仅要研究历史的脉络,更要走进历史的纹理与骨髓,更要关注和吃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细节,这样所塑造的人物才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和典型意义。抗日战争是一本具有深度、厚度与广度的历史大书,啃透它相当不易,它不仅旷日持久,且错综复杂,不仅有国民党军队为主力的22次大会战,更有壮怀激烈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和华南游击队对侵略者的广泛抗战,这些抗日武装是打败日本侵略军的主要力量,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应该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战争时期那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民众动员程度如此广泛,群众发动规模如此浩大,战斗意志如此坚强,斗争如此悲壮惨烈艰苦卓绝。应该说,凡是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们,只要不当汉奸,不管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都是英雄,那是一个遍地英雄的时代。所以,我们这些作家应该启发心智去写他们的家国情怀,写他们的英雄壮举,写他们的儿女情长,写他们的人性之美,写他们在战争中的普通日子及命运际遇,这便是对中国抗战文学富矿最有价值意义的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