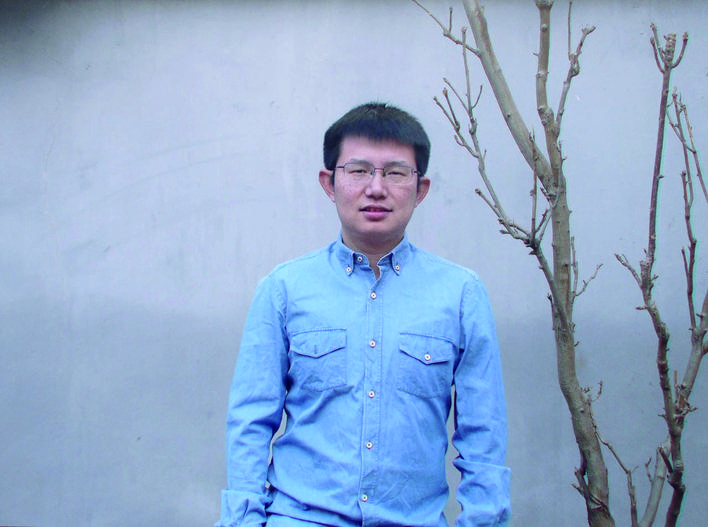如果承认文学是历史性的,那么作为文学关键性元素的想象力也是历史性的。具体地说,想象力的位置、功能和社会性意义,在不同的时空语境下并非完全等价。中国新文学百年的历史进程中,素有重摹仿而轻表现、重经验而轻想象的隐性传统。倚重想象力的写作,往往被视为现实性的缺乏,甚或是历史的虚无。而作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普鲁斯特的生活圈子并不开阔;卡夫卡更是声称,他最理想的生活,就是终日在地洞中思考和写作。他们都是与外部生活关系紧张的内省式作家,但又恰恰因此,他们如同但丁、莎士比亚与歌德一样,与其所处时代形成了深刻的同构关系。复杂混乱的时代,正是想象力以广义的文学为载体、重建并提供意义的历史时刻。
后疫情时代与百年前的世界一样,也是沧海横流的大时代。一成不变、日复一日的生活,无论我们是否喜欢,似乎都已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这是全球保守主义抬头的时代,完整的共同体想象渐次破碎,处处布满有形无形的“柏林墙”和“次元壁”,人们的悲欢并不相通。在普遍意义的共识和真相不易获得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无法通过体验,而必须经由想象,才可能穿透话语的层叠泡沫,接近历史和现实的内在性。这就像中国古典文论中的言意之辨,尽管言不尽意、得意忘象,也即“言”只是通向“意”的一个并不完善的中介,但是“意”也只能经由“言”才可能通往。此时此刻,想象就是达“意”之“言”,是我们实现破壁、靠近真意的唯一方式。我在今年年初的一篇笔谈中说:“如果从未来的眼光回望,我们当下可能正处于《三体》中大低谷时期的开端,或者用阿甘本的术语说,我们将长期处于一种世界性的‘例外状态’。在这个历史的‘断点’上,我们无法再按照某种目的论从未来解释过去,甚至无法通过过去理解当下。”也就是说,事到如今,想象力已经不仅是科幻文学的必需要素,因为无论是远未来(far future),还是近未来(near future)乃至“明天”(immediate future),都需要想象才能撬动。
在这样的因缘际会中,一批青年作家开始走入人们——兼括文学圈内和圈外、职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视野,并以异质化的想象获得其风格的新颖性。与前辈作家相比,他们较少中国现实主义的痕迹(obsession with China Realism),而是自始就带有一种我称之为“新世界主义”的视野。这种视野降临在小说中,就如卡夫卡《中国长城建造时》或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中的“中国”元素,是符号的、象形的、言近旨远的“世界”。青年小说家陈春成在《音乐家》《夜晚的潜水艇》,以及新作《雪山大士》中,都尝试挑战不限于中国,而是更具抽象意义的人物、故事、主题。识者自可由此生发,探讨认知层面的微言大义,关于如何理解自我、国家与世界,如何理解过去、现实与未来的关系,这些作品都提供了不同的契机和可能性。
但更为重要的是,“想象”自身的边界和秩序,在陈春成等小说家的作品中打破,又在新的层级得到重新结构。诚如王夫之《姜斋诗话》中所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例如,在对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的接受层面,我注意到不同群体间的微妙差异。出版者青睐其中更“文艺”的篇什(如“同名主打”《夜晚的潜水艇》),而批评家则重视更具“厚度”的《竹峰寺》《音乐家》和《红楼梦弥撒》。在我看来,在后面的这几篇小说中,作者的文学想象力、历史想象力与社会学想象力,达到了更高程度的综合和平衡。历史和现实在其中以高度抽象化、但绝非抽空化的方式存在。《竹峰寺》对于历史暴力、《音乐家》对于极权政治、《红楼梦弥撒》对于意识形态,都有个人化的独立看法,但这些看法,又不能简单划归于某种立场、态度、理论或观念形式。这正是想象力柔软、丰富而又极具绵延性的潜能所在。不只是陈春成,周恺的历史小说《苔》及其新作《少年、胭脂与灵怪》,李唐的奇幻小说《身外之海》及新小说集《菜市场里的老虎》等作品,或以今鉴古,或以实证虚,都从不同方面开掘并延展着想象的综合性潜力。他们引起的广泛影响,也让我们从另一角度重新思考1980年代以后的先锋写作。无论捍卫者还是抨击者,大抵都将“非历史”或“去历史”的艺术特征,视为先锋小说的观念核心。但事实上,其时或后来获得较高声誉的代表性作品,如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残雪的《山上的小屋》、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格非的《迷舟》,其实都是想象力、形式感和历史性的综合。它们都从特殊的路径触及历史,以及处在历史连续性中的某种现实。
除此之外,青年作家的想象,还呈现出内、外两个向度的辩证互动,也即自我想象与社会想象的关联方式问题。在公共空间阻隔、失序的时间节点,需要想象力进行理解和建构的,不只是个体存在与公共生活两端,还包括“我”与这个世界、个人与其实际生存之间的想象性关系。加缪名句“重要的不是活得更好,而是活得更多”言犹在耳,但又如前所述,今天我们已经(或仍然)很难通过“亲历”的方式活得更多,而只能通过反向运动,以想象的神游“占有”更多的生活。一些青年小说家的小说痴迷于密闭空间的营造——比如潜水艇、水瓮等各式“洞穴”,并由此生发出一整套“藏”的方法论。在内外交互的维度,我认为“藏”的诗学在两个线索上提供了耐人寻味的启发。其一,穷则独善其身,个体首先通过“我思”确认“我在”(有趣的是,传说笛卡尔早年在巴伐利亚的寒冷冬日,就是钻进一个火炉子整日沉思的),继而“照我思索,可理解人”,密闭成为领悟的前提条件;其二,所谓用舍行藏,可以说舍是一种特殊的用(介入),藏是一种特殊的行(实践)。由此,以舍为用,以藏为行,就成为特殊年代里个人与集体之间特殊的联动方式,一种虽然被动却不消极的生命形式。或如陈培浩所言,《音乐家》中蓝鲸体内、花苞内部、月球背面、雪花玻璃球,都在“内面”的世界里成为主人公古廖夫的音乐厅,想象由此具有了生命救赎的意义。
在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在无所希望中得救。无论如何悖谬,我愿与青年作家们抱持相同的信念:人类想象能力破壁、综合与联动的潜在能量,将在业已展开的大时代中承担重要的使命,甚至从未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