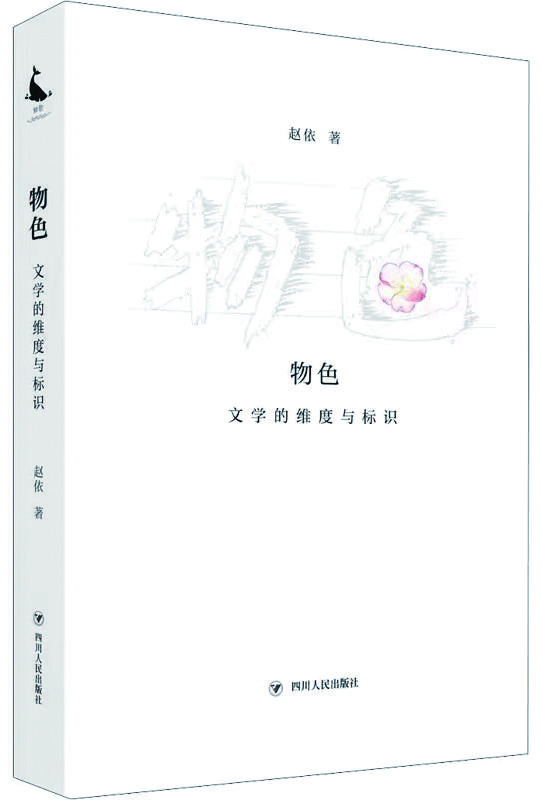长期以来,我以为文学批评是一种“偏见的集合”“顾左右而言他的生发与阐解”。多年前读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惊异于作家对其他同行的高度认可,如他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伤害的》的讲演当中,是极其温和的、敦厚的和智慧的,当然也显示出他深厚的文学“解构”“提升”与“重组”等能力。而阅读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其中有诸多的“眼光鲜亮者”“雄浑广阔者”,但大多数已经成名,长期占据和“统领”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坚与前沿。然而文学创作和批评始终是一个不断接力的事业,当时代与文学创作持续跃进、不断进行自我变革的过程中,新的文学观察及其批评者便突兀、有效地显露了出来,并且显示出他们“别有洞天与新见”的气质和魅力。赵依和她的《物色:文学的维度与标识》便是其中之一。
赵依年纪轻轻,文学之路却走得步步扎实。她既是很好的文学批评家,同时又把小说写得风生水起。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切换,自我意义上的建构与站在高处的俯瞰,彼此相得益彰。多年前我就意识到,新一代的作家和批评家的起点已经超越了我们的期待,他们显然已经自然性地区别于此前任何年代的作家和批评家了。因为时代的文化与环境因素,已经使得新一代的写作者们摆脱了既往的“文学教条”与“思维习惯上的羁绊”,几乎从一开始,他们就是新鲜的、勇猛的、周全的、光鲜的、前进的,甚至是世界的。在《物色》中,赵依的批评视域之广阔,“刻刀”之深,可谓满纸光芒。从小说、散文到诗歌,乃至大文化、泛文化艺术创作,其中的个人识见和判断,处处都有惊艳之感。如她在《“90后”写作如何敞开》一文中写道:“不同于早前一代青年作家小说里对现代性的关注,‘90后’作家在都市景观、大众消费文化、媒体资讯、商品经济等生活区块和价值体系作文学呈现已不作‘是什么’的情景描写,有关城乡关系的表达也已在庞大的文化网络视域中逐渐脱离一种标准化的矛盾呈现。”
逐渐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们,几乎从一出生,就面对勇不可挡的现代性,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递进和拥塞,使得他们潜意识里觉得,这本就是人间和世界的模样,本就是人类生活的氛围。以至于他们的文学创作,早已远离了农耕文明和前一个世纪普遍的人类生态环境。赵依的发现使得我再一次确认了时代、人、环境的关系,也领悟了环境之中,人类精神乃至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本质性的变迁与挪移。”她的观察是建立在“理性的现实”与自我的研判基础上的一种精准论断。
文学艺术始终有其大道,每一代作家都是在前辈的基础上站起来的。作为写作者和批评家要做到既向后看,从经典和杰作中汲取和学习,又要向前看,当然,还要环顾周身,一边抬头看路,一边闷头写作。赵依的眼界和阅读的范畴宽阔而又精细,雄浑却又能够深入肌理,她的《我们时代的文本细读——乔伊斯〈死者〉叙事爬梳》便是极好的一篇文本细读。赵依的分析,让人看到了一个写作者对于经典之作的虔敬、耐心与“领略的精到”“论述的义理”“解析的新颖”,使得人从中受益,也体现了赵依自身所具备的深厚学养。如赵依在该文中所说:“在《死者》中,与加布里埃尔精神成长相关的语料形式,除了潜隐的叙述者以框架叙述提供背景,还嵌有对话式的直接引语、意识流式的自由直接引语以及自由间接语。”
正如纳博科夫所说,小说乃至一切文学艺术创作,也是一门精密的科学。赵依在解读乔伊斯《死者》的时候,对其艺术特色、故事叙述方式、政治、时代、文学等诸般关系,也做了全面的解答,这一种“聚焦”于单一文本的文学批评方式,想必是大有裨益的,不论对读者还是作者。再者,赵依身在北京,又做文学编辑工作,她所关注的层面,是点面的高度统一,其中有我的“介入”(编辑),也有旁观者的“清醒”(批评者)。所有的文学批评,也有其严谨的“道统”。在阅读《物色》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惊异地发现,赵依几乎关注到了当下最优秀的作家及其新进的主要作品,如对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莫言的剧作《高粱酒》,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等作品“别具只眼”的批评和阐发,其中独到的“判断”是赵依文学批评才情的绝好表现。
在对阿来的长篇小说《云中记》批评中,赵依说,“阿来独特的叙事时间观控制着叙事节奏和叙事时序,不完整和不确定的文本通过重复叙事填补无限可能,重述之魅就好比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六出祁山和九伐中原等,叙述者一遍遍烘托渲染,一方面深入刻画着人物和事件,同时使叙事本身获得解放。”她对诸多当下优秀作品的批评中,显示出她锐利的一面,同时也反映了她作为一个优秀文学批评家的独特性。她对班宇、周恺等年轻一代作家作品的解读,既显示出一种“心意相通”的共鸣式自由言说,又体现了她对新作家及其作品时代性的洞察。
卡尔维诺说,“阅读就是抛弃自己的一切意图与偏见,随时准备接受突如其来且不知来自何方的声音。这个声音不是来自书本,不是来自作者,不是来自约定俗成的文字,而是来自没有说出来的那部分,来自客观世界中尚未表达出来而且尚无合适的词语表达的部分。”这句话可以视为对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家的基本要求。《物色》令人看到一种欣喜的景观,那就是,文本细读是文学批评的首要条件,赵依的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是“带领的深入”,另一方面,则也在做着“深入的开阔”。正如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其《金蔷薇》一书中所说,“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或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