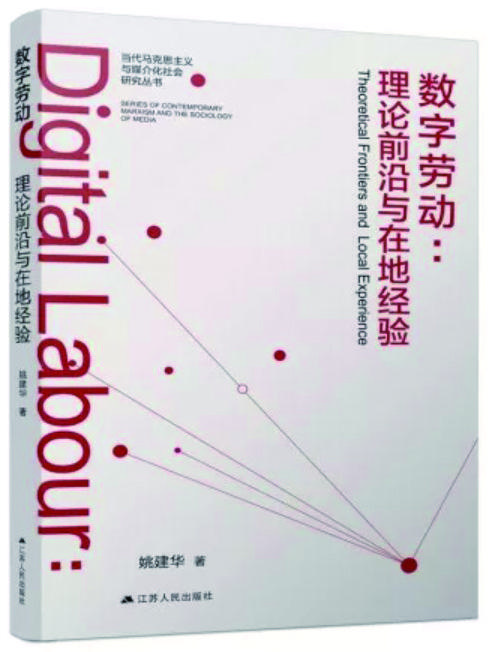为什么我们在互联网上的每一次浏览、发布、转发、点赞与评论,都是在为资本“劳动”?这是姚建华著的《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这本书尝试回答的问题。
在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将劳动数字化、数字技术使用者“劳工化”的趋势下,数字劳工作为新的分析范畴,逐渐成为传播劳动研究领域的前沿。本书通过对数字劳动研究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两个维度的系统性分析与探讨,希冀建构经典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场域。一方面启发读者深入思考数字劳动问题,充分发挥经典理论的思想潜能,以此来穿透实践与现实,同时为相关研究者打开广阔的想象空间,也使本书具有更强的反思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让读者切身感受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张力,以实践引导对理论的理解,更为深刻地洞察资本、技术与劳动三者之间多重复杂的勾连关系。
数字劳动概念的提出,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学界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热潮,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度反思,处在数字信息时代下的新劳动形式——数字劳动,成为了关注焦点。随着世界加速网络化,人们不再停留于被动接受,一跃成为产消合一者,而当大众窃喜于“人人都有麦克风”之时,其实已经不知不觉深陷于数字资本主义的陷阱。国外有学者将商业资本剥削“数字劳工”的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强迫,随着日常交流与社会关系的网络化与数字化,人们不得不使用互联网;二是异化,互联网公司而非用户自身占有平台,并从中获取利润;三是双重商品化,使用者本身成为商品,使用者所生产的信息也是商品。
不过,具体到中国语境而言,单一的剥削理论框架似乎无法解释当下如火如荼的数字劳动:义乌经济新模式下的“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打造,“人人是主播”的东北“新经济支柱”的出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电商助农”运送偏远山区滞销农产品的快递小哥;电子竞技成为年轻一代新的职业选择……网络经济催生了新型的劳动实践,也就是数字劳动,其灵活多变、个性化的用工形式最大化地激发了劳动者的自主性,为底层群体拓展了新的生存机遇和空间,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底层群体在传统劳动场域中较为被动的境遇。《人物》公众号的一篇爆款文章《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让外卖人员的劳动保障问题成为外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不过,文章中的一个细节也令人印象深刻,外卖小哥从电瓶车超速和逆行中体会到了一种顺畅感,以及对身体、生活和工作的掌控感。他们对每个路口的信号灯了然于胸,他们通过超速,超过了城市的白领和上班族,超过了那些循规蹈矩的人,成为这片领域的王者。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利润而超速,也是为了掌控感而超速。这篇非虚构作品带给人们超越刻板印象的新鲜感,因为这种描述使得外卖员不再仅仅是被同情怜悯的“他者”,或是资本链条里纯粹被剥削的“可怜的人”。这种价值实现感和“被看见”的成就感,其实也同样存在于那些在抖音、快手上发短视频的建筑工人、赶海女、跳太空步的村民、高速公路上的大货车司机们心中。
《数字劳动》一书作者意识到不能将自己囚困在“劳动控制—劳动剥削—劳动抗争”这一固定的分析模式中,开始探索将技术、技能、情感等要素嵌入资本和劳动的二元关系中,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对“众包新闻”和“虚拟恋人”的研究也就更接地气。作者以财新传媒旗下的“世界说”这一新闻媒体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其海外媒体专员的深度访谈,揭示他们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下如何有组织地生产国际新闻。研究发现,建制化媒体通过灵活积累策略,将海外新闻专员的在地优势、语言技能和兴趣热情转换为劳动生产力,进而为媒介机构创造核心价值。
目前国内对于“数字劳动”的批判似乎更多地集中在互联网企业。互联网大厂曾经代表着自由、多元、共享和包容,但是经过20年的发展变迁,大厂一度成为社会大众和劳动者们口诛笔伐的对象——“内卷”“996”“如厕自由”等等这些引发社会痛点的热词都发端于互联网行业。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劳动,并非通常意义上被平台无偿占有的用户劳动,而是一种“数字工作”。他们的工作可谓是数字经济的基石,也正是这些IT民工们,成为数字时代承担异化劳动最显在的群体。就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形容的那样,彻底地将劳动者作为活的附属物抛入了死的机器体系中。
在《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一书作者姚建华看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围绕剥削、控制、剩余价值等维度讨论劳资关系,在今天的数字时代仍具有很强的阐释力,但在很多国内新兴的数字生产领域,劳动者的情感因素也不容忽视,正是情感驱动着他们在网络上进行有偿或无偿、志愿或非志愿的劳动,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丰富性。这本书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魅力,而作者对经典理论的省思和在地化尝试极具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