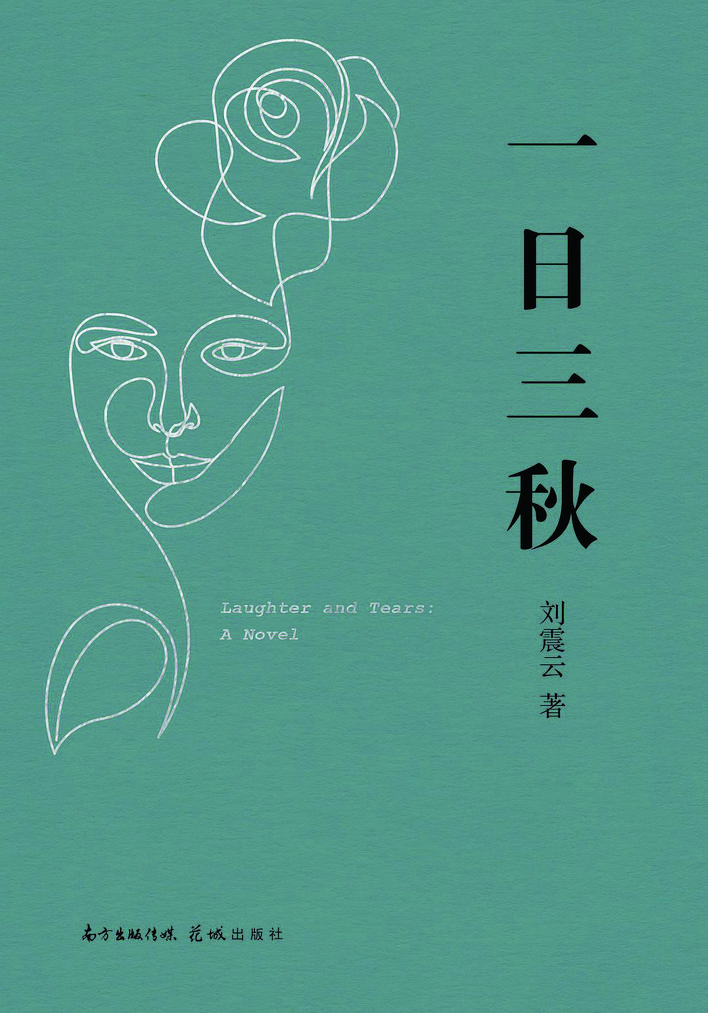《一日三秋》是刘震云在《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之后四年磨一剑,为我们重磅呈现的一部颇具魔幻色彩的长篇小说,它以延津当地花二娘梦中搜寻笑话的传说为线,铺开了这一地方两代人的悲欢。本期云友读书会的四位朋友分别从小说中漫溢的白蛇元素、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一日三秋”和“笑话”展开对话,为我们呈现进入这个故事的多种维度。
@李杨:《白蛇传》与日常生活的变形
刘震云的写作路径大致可分为两条:一是写世俗日常,以处女作《塔铺》为起点,凭借《一地鸡毛》确立“新写实主义”代表作家的文学史地位,而《一句顶一万句》可以说是此类写作的集大成者;一是写民间历史,相继出版的“故乡”系列占据“新历史小说”风潮的一席之地。质言之,前者注重日常生活经验的提炼、描摹与协调,后者则以变形、夸张与戏仿的方式重新解读历史。在最新推出的《一日三秋》中,刘震云力图“以日常生活为基调,把变形、夸张、穿越生死和神神鬼鬼当作铺衬和火锅的底料”,某种程度上或可视为其融合两条写作路径的一次创新之举。而完成此次创举的关键,正在于对《白蛇传》的个人化叙述。
《一日三秋》故事的开始,即安排豫剧《白娘子》中白娘子的扮演者樱桃和法海的扮演者陈长杰结为夫妻,构建起戏里与戏外的强烈反差。不过,戏里的演绎却不断渗透进戏外,主人公明亮的乳名即来源于戏里“有出息”的翰林,而伴随着李延生前往武汉拉开的故事主线,则与葬在乱坟岗上的樱桃被强奸杀人犯逼着扮成白娘子“假戏真做”有关。贯穿全书近半篇幅的樱桃灵魂的飘游,更是与《白蛇传》脱不开关联。从门市部墙上的《白蛇传》海报,到明亮口袋里的折子戏剧照,直至被抛入江中,樱桃化作的仍是戏中的白娘子。可以说,因一把韭菜自杀后,樱桃始终是以戏中的白娘子形象出现并借戏“活了下来”。事实上,作者还有意打破戏曲与民间传说本身的界限,肉身压在乱坟岗等待陈长杰拯救的樱桃,不免引人想起被压在雷峰塔下等待法海释放的白娘子。而被打捞上岸的樱桃去到的,正是冯梦龙《警世通言》所记载的白蛇故事的发生时间——宋朝。传说、戏里和戏外三个世界的跨越,充分发挥了小说作为虚构艺术的魅力,而明亮对花二娘说的“负负得正”,则暗示着在文本阅读过程中收获的体验与感悟是真实美妙的。这样辩证看待虚实真假的思维方式,延续着刘震云在“故乡”系列中有关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思考。
作为历代相传的“集体共享型”故事,《白蛇传》中的白蛇处于“人是什么”与“人应当是什么”相对立的情境之中,也即本能欲望与社会观念之间存在冲突。对此,书中借陈长杰之口一语道破:“《白蛇传》的戏眼,是下半身惹的祸。”而支撑文本主体内容的明亮与马小萌的情感困境,恰与《白蛇传》中白蛇所处境遇形成对照。马小萌之所以被逼上吊,同明亮逃往西安,后又遭孙二货羞辱威胁,直到晚年儿子鸿志仍因为其出头与同学大打出手,都与借钱不成的香秀曝光她在北京做过五年妓女的事情有关。明亮选择接受马小萌的过往,但两人的婚姻关系却不容于延津的世俗道德,一如许仙接受了白娘子的蛇妖身份,却难逃法海以人妖殊途为由镇压白蛇于雷峰塔下。不同于民间传说的是,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之外,日常生活更是由无数的平淡时光构成,而这份时间的力量足以淡化或消解观念的碰撞。不难见出,刘震云借《白蛇传》隐喻了《一日三秋》所要展示的人生困境的主题,又以日常生活书写暗示着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1924年9月24日,雷峰塔的倒塌,为反传统人士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一度成为五四知识分子推翻封建秩序的隐喻。鲁迅即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有言:“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及至田汉创作于20世纪中叶的革命现代戏中,法海所住寺庙成为腐朽制度的象征,承担着剔除封建糟粕的历史使命,延续着五四以来的反抗与斗争意识。而在20世纪末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1992)和电影《青蛇》(1993)中,文本里的情与欲得以放大,满足着大众有关情比金坚或纸醉金迷的世纪末幻想。到了2021年,刘震云推出《一日三秋》,在革命与欲望的叙事之外,将《白蛇传》的戏曲与日常生活书写相融合,以夸张变形的方式重新演绎白蛇传说,实现了写作风格的突破与自我的超越。
@赵志军:魔幻中原的意义指向
刚才李杨谈了《一日三秋》与《白蛇传》的同构性,他对故事的琢磨很细腻,我想接着谈谈小说打破魔幻、现实边界的手法在文本层面的意义。大概可以断言,多数读者对刘震云会用此种形式重写人们已然熟悉了的河南没有准备,这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为中原核心的河南在中国文化中长时间表征着一种正统,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学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现实精神已成为我们关于河南的一种格式化想象,一种排斥与压抑巫神鬼怪话语的固化印象;二是作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刘震云的作品一贯延续着一种冷静的、刻意风干了温度与水润的语言风格,生活总是以破碎、干扁、缺乏价值的“本原”样态呈现。《一日三秋》神话与现实、梦境与日常互相穿梭渗透的魔幻现实格调,无疑与我们惯性的河南印象及熟知的作家风格形成了不小的反差。这种反差又恰恰说明,这部作品在河南的地方书写与作家的生存思考方面有着特殊意义。
关于地方书写。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形式的产生及流播(被边缘、民族、地方、宗教书写借用)本身代表着被压抑的声音以非正常方式进行突围的尝试,故此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被规约为中国传统(甚至正统)之表征符号的中原(河南),在惯常的文化表述中被抽象与单一化了,这不仅掩盖了其本有的斑斓色彩,更使得作为中国部分的河南(中原)很少被视为“地方”,而是整个中国或正统中国的不再被天马行空地想象与创造的模板,以致河南形象总体上比较刻板、单调。《一日三秋》里的延津小城非常难得地恢复了“河南地方”本来面目,无论是戏里戏外纠缠人间的地方豫剧《白蛇传》、梦里梦外界限不清的卖羊汤的吴大嘴、记忆与现实里真切却又模糊的卖枣糕的奶奶,还是传说与现实难以界明的花二娘、沟通阴阳两域的算命人老董,都显示了民间文化及民间话语本身的巨大丰富性。围绕着老董的,也不再是“不语怪力乱神”的负载着文化包袱的“河南人”,而是一群我们所熟悉的现实又迷信的市井俗人,他们使抽象的“河南”不再正统、陌生。在延津人梦中寻找笑话的花二娘的地方传说,也让延津成为与众不同的“独一个”。即是说,经由魔幻现实手法对地方符号的广泛勾连,《一日三秋》使中原(河南)拥有了鲜明的地方性。
关于生存思考。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对弥漫于个人、族群命运之上的无形禁锢进行形象描绘和具体解释的努力,无疑是对于人此在生存的变形化观照,这种逸出现实逻辑的观照并不指向问题的最终解答,而是以唤起对于存在的注意为目的。在刘震云以《一地鸡毛》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中,许多人物在严肃、破碎的现实中没有波澜地消磨生命,人的存在被笼罩于意义缺失的平面的物理牢笼中,除去袒露人及其生活、历史、社会的残酷本相,作家似乎对精神崇高、灵魂救赎等范畴缺乏兴趣。但在《一日三秋》中,人物对前世、今生、来世间因果的执着,至少证明了作家对笔下人物的精神性存在有了呈现与解释的欲望。无论是将《白蛇传》中角色关系与现实人物关系的倒错作为诸多人物悲剧宿命的源起,还是将明亮与马小萌今生的相守解释为前世恩怨的延续,抑或是老董基于来世光明的愿望而有的种种善举,都是作家对人的种种生存予以“同情之理解”的尝试性解释,这使得本来仍然破碎、冷静的故事在叙事行进中逐渐拥有了难得的温情。以此观之,《一日三秋》或会成为刘震云创作谱系中的某个关键转折,如果这种对存在进行解释的努力能在今后的创作中得到延续的话。
当然,刘震云已经明言,穿越生死的神鬼叙事只是为了将六叔的画铺陈为一个完整故事,这些突破了作者预设框架的意义或许只是“作为内容的形式”在作家创作中潜在进行的自我意义生成,但这种“偶然性”无疑也表征着前述重要转折的可能到来,对此我们可以在刘震云将来的创作中进行验证。同时也须指出,作家一贯的写实风格与魔幻现实手法的扞格,确实造成了这部小说诸章节风格、氛围的不一致,一些颇具戏剧性的线索(如两个孙二货)之未能充分打通,也给小说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崔涛:“一日三秋”的宿命
李杨就《白蛇传》隐喻指出的人生困境主题与赵志军就生存思考提及的人物悲剧宿命,我认为都可以在“一日三秋”的表达中获取线索。虽然小说已经指明,这既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意思,这在人和人之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也更是“人和地方的关系,在这里生活一天,胜过在别处生活三年”。但吊诡的是,这种对人以及对地的亲切感在小说中却被无情地拆解了,以致“一日三秋”本身成为一个反讽的“笑话”,进而呈现出笼罩在各类人物身上的无力挣脱的宿命感。
这首先体现在花二娘与延津及延津人的关系上。三千年来,延津人都知道花二郎已死于延津,但无人对花二娘坦承,使其在等待中困于延津并望(忘)延津之外。延津人为之付出的代价则是世世代代都要在睡前准备笑话,以备花二娘于梦中索取,否则会有生命之虞。这宿命般的“三秋一日”,于花二娘而言是“一日三秋苦日短”,对延津人来讲却是“一日三秋苦日长”。其次,“白蛇”樱桃的命运也是如此,戏里戏外终究受厄于“法海”陈长杰之手,甚至死后也受困于“笑话”不得轮回,困顿解脱全不由己。除与明亮短暂的共处外,“一日三秋”的亲切感对樱桃来说几乎不存在,戏中的宿命与延津人的苦途成为她人鬼一生的羁困。
似乎所有突破或调和宿命的希望都汇聚于明亮身上。但即使定居西安,他也未能逃脱花二娘梦中索取笑话的苦运。他的一生,仍在隐隐地延续着父母一代的《白蛇传》故事继续演绎,幼年拯救樱桃暗合“许仕林救母”,成人后与长舌头的蛇妻马小萌的结合然后背井离乡,成功后重返延津面对的却是物是人非故人凋零。他在延津、武汉和西安三地的空间转圜中尽量调适以图冲破宿命的牢笼,但终究没能逃出延津人的困局,“故乡一日胜过他乡三秋”的亲切感只能在梦中编织。对记忆有选择地过滤与筛选不过是一种徒劳的自欺,本意味着亲切感的“一日三秋”最终在诸般希望破灭后呈现出一种荒诞的反讽意味。
延津人的“一日三秋”承载着“神界鬼界、戏里戏外、历史当下、梦里梦外和故乡他乡”的多种宿命与困境,展露的正是人对命运的无奈和屈从。作者剥开日常生活“一地鸡毛”的表象,将神鬼世界融入了跌宕起伏的人途,但故事背后仍是那波澜不惊的一江宿命池水,仍是那无形之力不动声色地对生活与人性的挤压。
@丁永杰:“幽默”背后的关怀
刘震云对“幽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2020年底,刘震云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谈到“幽默”,认为真正的幽默是不幽默的,应该关注笑话背后的道理、道理背后的道理。新作《一日三秋》便是对“笑话”“幽默”本质的进一步思考和延伸。
不妨看一下《前言》中的几个镜头:“见他画中,月光之下,一个俊美的少女笑得前仰后合”;“又见一幅画中,画着一群男女的人头,聚在一起,张着大嘴在笑”;“其中一只盘子里,就剩一个鱼头,鱼头在笑”,甚至“画中的阎罗也在笑”。花二娘在延津人梦中寻找笑话这条线索贯穿整部小说,但不难发现,全书几乎没有一个能让花二娘真正满意的笑话,连最会讲笑话的人也是如此。如果说《一句顶一万句》《我不是潘金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作品中确实有许多令读者忍俊不禁的片段,《一日三秋》则几乎没有什么能令读者发笑的情节。三千多年来,花二娘找寻“好笑”的笑话而不得,明亮为求生讲述的妻子在北京的“事情”,这藏在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痛楚,却成功逗笑了花二娘,其间的分裂和悖论令读者心头颤动。
《一日三秋》交代了两代人的生存轨迹。上一代人进入读者视野没多久,便笼罩在了死气沉沉的生活中。陈长杰和樱桃在县豫剧团演戏的时候风光无限,剧团解散后就陷入一地鸡毛的生活,以至樱桃因为一把韭菜上吊自杀;李延生在婚后不久就变得沉默不语;吴大嘴整天不苟言笑,最终被“心事”压死……这一代人的一生大多被“笑话”捉弄:老来不得志的陈长杰自认“把自己活成了笑话”,李延生也同样感叹“我算把自己活成了笑话”。刘震云将“笑话重返于延津”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忧郁少年明亮早早辍学去“天蓬元帅”饭馆学习厨艺,却意外地为后来的身份转变创造了条件。马小萌靠自己不光彩的“事情”攒下了10万元钱,却为自己和明亮换取了生活转机。上一代人樱桃、吴大嘴未能躲过的来自花二娘的笑话考验,也被明亮看似巧妙、实则充满“矛盾性”的幽默笑话消解掉了。想必,这就是作者在小说中试图给我们寻找面对人生的态度与方法。
这让我不由想起沙夫茨伯里关于“幽默”的论述:幽默是对真理的最佳检验方式,也是防范狂热、伪善与教条顽固(bigotry)的最佳手段。在他看来,经不住打趣的主题必然可疑,假正经经受不住一个笑话的考验。“幽默”不仅仅是单纯博人一笑的“笑话”,它往往和“真理”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暧昧关系。刘震云擅长在这部小说中着力营造一种“幽默感”,但与其说作者在通过两代人的故事帮我们追寻“失去的幽默”,不如说他是在强调每个“幽默”的小人物都应当被予以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