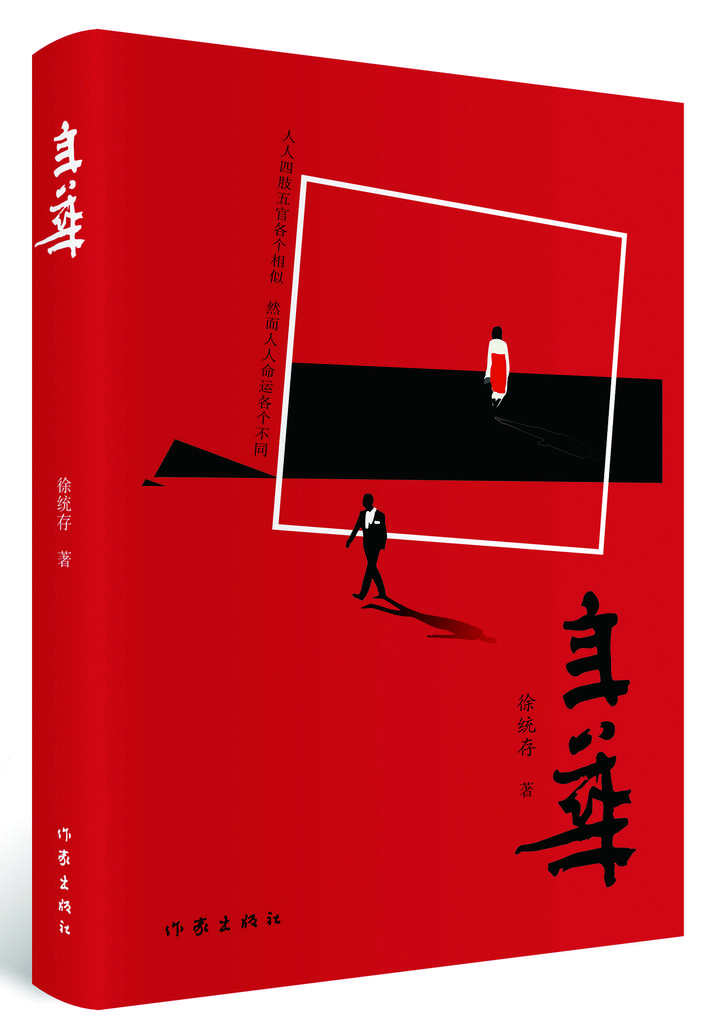“人人五官四肢各个相似,然而人人命运各个不同。”这是受到作家蒋子龙、影视导演尤小刚倾情推荐的基层作家徐统存长篇小说《年华》的开首语,使人想到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幸福的家庭各个相似,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的开篇句。作家无意与托翁在造句上比高低,而是借此表达自己对人们命运差异的深度关切,实际上是聚焦小说中的主人公余统华的部队和地方职业生活之路,通过他的风雨旅程,折射出他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嬗变中的人生奋斗和生命感悟。阅读全篇,不由感到书中军地题材的发掘、耕耘风景独好,时代风骨的淬炼、传扬风光无限。
我们所希冀和强调的时代风骨,是充满人文关怀、健康向上、催人奋进的。文学作品能否产生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与作品的时代风骨息息相关,我们可以从中窥察到作家的思想修养、家国情怀与文学担当。《年华》及其作者的审美信号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特质。
作品中,在从农村走出来的军地干部余统华的身上,不难发现他逐梦人、边缘人、觉悟人的人生轨迹,在他的乡情、亲情、爱情、友情的情感世界中,始终贯穿着在时代大潮推动下体现自我价值、实现个人目标的主线,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个人命运与历史命运在某种程度上维系在一起。这使得他在历经坎坷,把将军梦、仕途梦束之高阁后,突破了内心苦闷和思想挣扎,学会了以辩证的、历史的眼光洞察社会、透视人心,把今天的“我”放到过去与未来中去衡量和剖析,从而在人的“实现”与精神“回馈”方面有所收益,达到了“踏破铁鞋无觅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人生境界。从中不仅看到人生风景、社会背景,而且感受到时代的脉络和风骨。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人学不仅勾勒外表,而且反映内心,淬炼个人风骨以体现时代风骨,这在《年华》里得到了相应的反映和验证。作者注重发挥自己和平时期生活积累的优势,在叙事冲动中让包括主人公在内的各种人物形象,以素描简约的形式自然地呈现,人物对话和动作成为立人处世的主要元素。主人公余统华生长在黄海之滨的东台农村,与其当过新四军、受伤返乡务农的父亲,还有勤劳的母亲、兄姐及周围的乡亲们,过着物质匮乏的穷苦生活。穷则思变,怎么变?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庄户人带来了改善生活的希望,也给一些土里刨食的年轻人展示了寻找出路的机会。高中毕业回乡的余统华就是其中一员。他干农活、寻短工、上补习班,最终选择了参军入伍。当时的中国,参军与上大学、下海经商一样,可能改变年轻人命运,这是农民家庭的大事。对书中的主人公来说,由此开始了逐梦路上奋斗进取的新征程。
我国古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风骨和文采兼备的作品才是理想完美的作品。他对风骨的解释是气血充盈、润泽有力、才力丰赡,只有具备如此特质的作品,才能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打动读者。《年华》着重点放在人的“实现”过程中的诸种表现和事物碰撞,通过简洁有力的叙事风格,不断培养、锻造、展示作品中的时代风骨,使人的性格、作品的风格与时代的风骨逐渐走近、融为一体。所谓“人的实现”,即人的发展、人的奋斗等,这在徐统存的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人公余统华初入军营,便以拿破仑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为座右铭,私下绘制了从战士、军校学员到军官、将军的“路线图”,把个人的职业发展、价值追求与从军报国的宏伟理想有机融合。经过艰苦努力,他有幸考上了军校,成为他谋求人生发展道路上的转折点,他为此激动不已。此后,他回到军营,在工作中屡创佳绩,受到部队及首长的高度认可。此时,他在部队的个人“路线图”进展缓慢甚至停顿,曲线晋升,他从江南县人武部调到邻县人武部晋职正科长。为了进一步实现人生的理想,余统华搁弃了“将军梦”,历经曲折,由正营职科长转业到江南县委办当秘书。这时候,他绘制了从秘书、副科长、科长到更高职务的“路线图”。给县委副书记当跟班秘书,虽然十分辛苦,但这个岗位发展的机会多、潜力大,也能锻炼人,是个令人羡慕并看好的职业。余统华几经曲折,在职场中略有进步,却在一次文字把关的技术性疏忽中丢掉了秘书科副科长职务,至此仕途停滞。其婚姻也因他帮助朋友筹资失败、承担还款责任而解体。面对职场和小家庭的两次“滑铁卢”,余统华的人生进入了低谷,由当年的逐梦人向社会边缘人转变,似乎与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奥涅金有相近之处。尽管如此,作家并没有放弃对人物的正向塑造,如余统华帮助女儿改写关于春天的作文,对前妻及其父母依然给予关照,对家乡亲友和老战友的惦念,以主任科员身份参加机关中层干部竞岗,逐步履行还债的计划。这些看似平常的故事情节,在这特殊异常的人生困境中,以其真实和真诚,牵动着读者的心。作家徐统存并没有把笔下的主人公写成“高大全”的完美稻草人,而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把余统华的成长置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的热流中,在展开其个人优点和特长的同时,也不回避其缺点和不足,如有时过度追求个人目标、对成功与失败的敏感、遭遇困难后的消极心态,这些在小说的描述中均有真实、微妙的反映,为完成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文学史上不乏逃离生活、远离时代的创作主张,但实践证明这是一些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梦呓和幻觉。文学作品一旦缺少了风骨,便如同无根的浮萍。风骨是对作家和作品的思想与情感的导向要求。社会前进需要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力量的作品,这是文学作品不能回避的社会功能。可以说,风骨是作品的血脉与魂魄。优秀作品的血脉总是沸腾的,魂魄总是飞扬的。这样的作品即使艺术手法略有瑕疵,也不影响其旺盛的生命力。
法国作家雨果在《海上劳工》里说:“脚不能达到的地方,眼睛可以达到,眼睛不能到的地方,精神可以飞到。”关于精神的话题非常广泛、众说纷纭,却与人物命运的走向、故事情节的拓展以及由此冶炼铸造的时代风骨密不可分,息息相关。在《年华》这部当代军地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各种人物的出现,虽然有限度地借鉴了新闻主义和纪实文学的表现手法,有的用笔轻描淡写,着墨不多,然而都或多或少、或现或隐地反映了各色人等的性格特征,反映了其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活动。较为突出和典型的是陈小娇这个出生贫苦、婚姻崩盘、拥有千万资财的女商人,在小说的后半场登台亮相,她的出现并非偶然,应属必然,因为她出现在小说主人公余统华职场和婚姻走下坡路的关口,有效推动了主人公人性及欲望的展开。陈小娇利用各种关系和机会经商谋利,在市场化浪潮中似乎无可厚非,然而急功近利的投资行为反映了她及这个时代一部分人的不安全感,致使其沉埋了灵魂深处曾经泛起的知识、智慧之光,在逢场作戏、尔虞我诈的演技中重蹈覆辙,深陷泥潭。她借助“情人”余统华的人脉资源和中介办成了商务大事,却又找借口用手机录下与余统华云雨之欢的镜头,试图以此要挟对方以求更多不当利益。当得知对方早已离婚单身,并不构成“道德缺失”和“行政错误”,这个外表美丽热情、内心阴暗多变的商场女人,才打了退堂鼓。不过,从后来她与小自己10岁的副主任的儿子谈恋爱,也可想见其心机很深。正是这样一个女人,与前面的刘爱玲等女性对主人公青春情感的影响不同,她对处于人生低潮、需要还债资金和情欲慰藉的中年余统华,在将来的追寻精神基地的探索中,完成了痛定思痛、酝酿发酵、临门一脚的转折性铺垫和最后过渡,使他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摆脱“边缘人”的格局,走向了“觉悟人”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坦途。其重要标志是他投入大量时间来阅读、思考和文学创作,拿出了一系列具有一定分量和社会影响力的小说著作,成为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的现实主义代表性作家。作为一个凡人,他曾为自己的得失而计较,为自己的仕途不顺而埋怨,对一些社会弊病心生不满。而作为一个党员,他终于突破了个人“委屈”、待遇“不公”造成的思想彷徨,从袁隆平等科学家的伟大奉献中获得了摆脱“小我”的力量,从参观烈士陵园陈列馆、深刻学习和思考先烈的事迹中,汲取了精神生活的源泉。他意识到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在世俗社会遭遇到自认为的那种“不顺”“不公”“不幸”,但这不应当成为个人消极绝望的理由,更不能成为否定人生与社会的依据。如何调整自己的认识视角、心态,如何看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如何把握和摆正私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位置,才是最重要的。他从人性和社会机制的角度,意识到包括先烈在内的革命者都不是完美无瑕,生前在人际交往中也可能会遇到误解和质疑,但这丝毫动摇不了他们为信仰而斗争的英雄主义精神。这说明,主人公的思想几经周折、几度徘徊,终于在对历史与人性的透视中去伪存真、去芜存精,力所能及地超越了现实中个人价值观的局限,在有所看、有所思、有所悟之中,战胜了自己,走出了人性和精神的迷宫,成为一个可以站在生命制高点上看人世的觉悟者,从而达到了尝试返璞归真、唤醒初心、重塑灵魂的“精神回馈”,也应验了罗曼·罗兰大声宣告的简约而不简单的名言:“精神就是光明。”这种个人风骨的千锤百炼、时代风骨的浑然天成,何等浓烈,何等壮观!
时下有些文学作品,充斥着一种小情怀、小摆设、小情调,满足于个人小思绪、小经历、小感受的宣泄,这类作品多了些情绪和修饰,少了些格局和风骨。《年华》却反其道而行之,注重从小人物、凡间事中挖掘精神宝藏,冶炼时代风骨。譬如,在人的“实现”与精神“回馈”的求索路上,“母亲”形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主人公的生母尽管经济拮据,仍给付算命先生较高费用,因为这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认可了其给儿子指出的报考军校必有好运的人生方向,这为余统华离开农村走向外面的世界、努力践行人的“实现”提供了最大的可能。小说进入尾声阶段,生母病重直至辞世,给挺过了职场和婚姻挫败难关的他带来沉重打击。但他没有消沉,通过写诗的方式抒发了对母亲的怀念和对生命意义的探问。几乎同一个时段,余统华早年参军后与其结为母子关系、代牺牲的战友行孝的那位烈士母亲朱妈妈又生命垂危,他立即奔波动员相关力量开始了千里营救,护送朱妈妈来总院手术治疗,使其转危为安,获得新生。这两个母亲的不同结局,似乎存在着关于命运因果的某种玄机,这使得已经在精神产品劳动中取得显著业绩的主人公,把更多的审视眼光由物质转到精神上来,投注于对生命本质和哲学的思考上来。这无疑为这部小说以主人公为中心,进一步深化、强化从人的“实现”到精神“回馈”提供了更多的催化剂。小说结局,主人公依靠自己的努力还清了债,又与刘爱玲复婚,预示着他的生活在崭新的精神层次上回到了令人欣然的新常态。
徐统存的人生经历和创作之路证明,写出文学作品的时代风骨,需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扎根生活,增强文学的使命感,善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主流、看本质、看方向、明是非,在变革发展的征程中汲取源源不绝的动能。他的《年华》还在文体的增量写作方面有所实践,在长篇小说的文学范畴中,不时契入散文体和新诗体,借助中国古代诗词、名人典故加强主人公身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共鸣对接,有力地推动了剧情发展,有效地丰富了创作形态,更好地展现了从逐梦人、边缘人到觉悟人的主人公余统华的艺术形象,为当代军地题材文学成功提供了一个真实可感的审美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