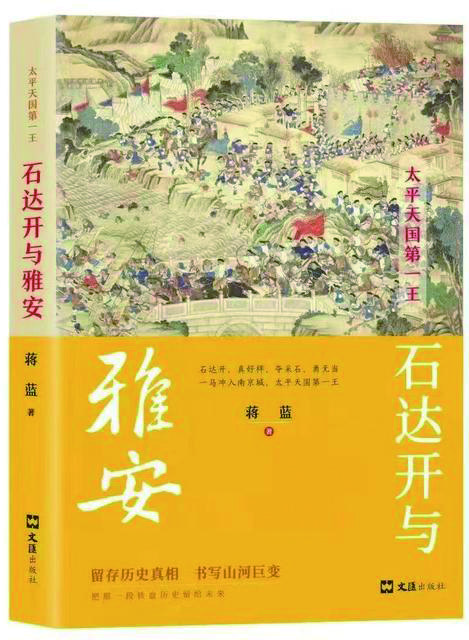蒋蓝是一位才华横溢而又能努力下苦功、不怕艰难的作家。他如果写抒情性的散文,一样会写得很出色。但从2011年开始,他开始着手《踪迹史——唐友耕与石达开、骆秉章、丁宝桢、王闿运交错的晚清西南》这样一部长篇散文的调查与写作,这就决定了他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写作之路。倏忽十年过去了,他再接再厉,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同一题材的《太平天国第一王——石达开与雅安》。在我看来,这不是重复,而是思想精进与史料反复厘定、文学深化的可喜结果。
我知道,这几年蒋蓝在研究太平天国石达开的晚清挥师突进西南之余,还在着手古蜀王朝以来的四川历史的系统思索,他也在写工程浩繁的《成都传》。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接合部的许多地方,蒋蓝一直跋涉穿行其间。他前后购买了太平天国以及地方史料上百种,反复阅读,条分缕析,然后采用纸上史料与出土文物、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把历史研究最后落脚于文学的非虚构写作畛域,为我们复原出一段段鲜为人知的西南生活史与风物史,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西南空间的认知。
《石达开与雅安》是一部读来津津有味的长篇纪实作品,也是一部有历史意义、历史价值,又具有生动文学笔法、叙人叙事、动人心境的长篇非虚构。蒋蓝曾经说:“用几年时间来全力完成一件事,长期奔波于田野山河间,在我生命中估计没有第二次!”“写作中,我必须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官场文牍、稗官野史、江湖切口、烟帮密语、袍哥茶阵、天国客家用语等等构成的专属空间与特定时间,我才可能竭力成为一个文学与文化的福尔摩斯。”“我相信,我追踪的四川提督唐友耕与翼王石达开的踪迹,所带出的1850至1900年之间的四川官场史、军事史、民俗史、植物史、道路史、城建史乃至风化史,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再现努力……”
我赞赏蒋蓝这种有大气魄、有雄心、知难而进的创作态度与风格。他无心取悦于文坛,但取得的效果却必然使对这种作品有兴趣的阅读者得到赞叹与满足。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蒋蓝是能真正深入到他要写作的那种生活中去的,尽管艰苦而且艰难。事实上,今人写过去的旧时代和旧人物,总比深入今天的生活写今天要困难,但他是努力深入了,而且确有所得。他的作品感染了我,我仿佛能看到他站在大渡河边面对大风呼啸、波涛滚滚,遥想当年石达开在此艰难作战的情景;又仿佛能看到他在寂静的深夜里钻研白天采访到的散乱资料;或是在大雨滂沱的夜晚、在孤寂简陋的客栈小屋里听春雨声奋笔写作……
书里写到过一件使我感动的事。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凌迟,关于其殉难的地点,蒋蓝采访收集到五种说法。当他向成都两位学者发去求教电邮后,一个寒冷的冬夜,在家里回复来了,他突然发疯似地对妻子说:“走,穿厚点,我们开车出去!”从成都九眼桥家中到达督院街口的“院门口”,已是深夜十一点半了!把车停下,面对深夜一个人都没有的清冷的大街,他对妻子说:“相传这里是翼王石达开被凌迟处,当时翼王等人从科甲巷省臬台监狱被押到总督衙门受审,必须经过这里……”妻子在寒风中忍不住说:“你这个疯子呀!来看什么?鬼影子都没有一个……”这其实不是笑话,而是痴心于创作的蒋蓝沉迷于创作踪迹史的正常表现。
有时候,文学创作也是需要一些这种“疯子”精神的。书中的翼王石达开,写的只是兵败大渡河直到被杀害就义的那一长段,但分量厚重,尤其是被残忍地一刀一刀凌迟处死,蒋蓝写得淋漓尽致,使我看得心悸手冷、血压升高。他引用的资料详尽而可靠,对历史上一些这方面的争议,大有“钥匙开锁”的意义与作用。涉及石达开的字数,占本书约四分之三,但分量厚重,大气磅礴,感人至深,能引人浮想联翩,亦能使人热血沸腾、唏嘘长叹。
唯有作家写历史,才可能这样淋漓尽致!
蒋蓝不仅是一个“写书的人”,也是个“读书的人”。他博览群书:正史野史、诗词歌赋、中外典籍直至写作本书时所能觅到的一切文史资料、四川典籍、地县方志、信函日记、档案文件、民间传说、地图照片、老人回忆以及书中人物后裔的叙述等等,均在阅读研究及考据之列。于是,此书得以丰满、得以完整、得以可信、得以成功。
我想,《石达开与雅安》如果不是作家来写,而是纯由历史学家来写,可能不会像蒋蓝这部述作感人而且吸引人阅读。这部长篇出自一位有思想的作家笔下,是集文、史、哲于一体的作品。书中插有数十幅照片、图画,也为内容增色不少。文学作品重于塑造人物,尤其是典型人物,当然也要同时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优美的文学笔法及文句、叙事、写景、状物等。史学家重在发掘、研究,重在实地考察及潜心考证,有所发现和前进。哲人则从学术角度体现人之才能识见,从自然知识与社会知识之累积及体悟中寻觅出规律、法则及正误之道。蒋蓝在处理文史哲的问题上做得很出色。他是作家,文采斐然,他写踪迹史,自然要去伪存真;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想象力的作家,于是自然而然在美文中并不揭橥什么主义,但常常在叙史叙事时颇多哲思,或诗意盎然。文笔锋芒,有时甚或带有“野”气,但这些都是在既尊重史实又尊重文学性的基础上写踪迹史的必要和可贵之处。
分析历史可以发现,自从1862年2月20日石达开从湖北利川进入四川石柱,与清军拼死一搏的十几次大小战役,实际上就是强渡与反强渡之间的博弈。我们以往均记载,1863年3月石达开是从巧家县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的。但蒋蓝的考据结果不同,从他书中的史料可见:浩大的金沙江竟然千里冰封,翼王部队是从结冰的江面,踏着被冻硬的将士身体,走着进入四川境的。冰封金沙江!一定是石达开平生仅见,也是我们从史料里发现的唯一一次记载。
蒋蓝说过:“人迹是构成史迹最重要、最深切的痕迹。”我同意这个观点。写《踪迹史》已经太过艰难,而接着完成《石达开与雅安》更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挑战。但蒋蓝这部作品应该说是一部成功的述作。
我以为,有的书会过时,蒋蓝这本书是富于生命而不会过时的!他吃的苦、受的艰难太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