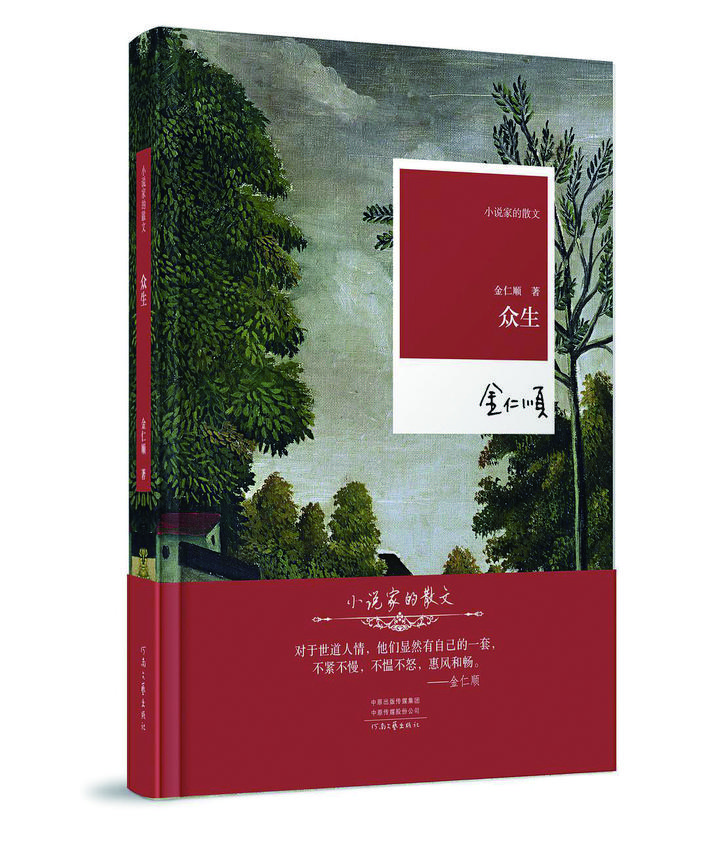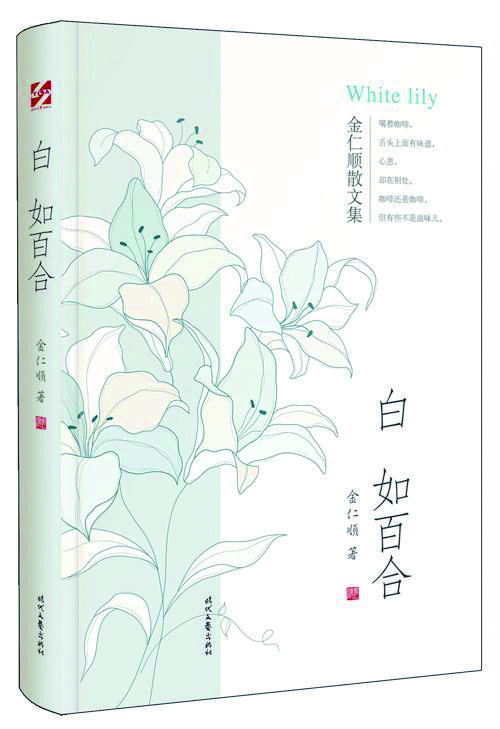这种写作有点儿像老摄影底片,能看到上面模模糊糊的影像,但没有像纸和显影剂,底片上面的人和物,以及风景,它们真实存在,但我们却看不到真面目和细微处。
艾 伟:你的近作《宥真》《小野先生》《众生》《为了告别的聚会》这批小说或散文,似乎和以前在地理空间上有所改变,往往有一个国际化的背景,《宥真》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和韩国,《小野先生》则发生在日本和长春,《为了告别的聚会》讲的就是一次国际笔会,你把自己放入到这些作品中,使得这些作品和你的经历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性,在这些作品中,你试图打破纪实和虚构的界线,“我”一直在里面,像一个亲历者娓娓道来,有一种散文化的倾向。我们都知道,散文一般来说是不能“虚构”的,小说却要虚构,你决定用这种方式写作时,你是想创造不是虚构之虚构的效果吗?
金仁顺:你这么一说,还真是的。虽然不是故意为之,但近期这几个作品确实是有这么一个共同性,“不是虚构的虚构”,概括得很精准。
写完《纪念我的朋友金枝》后,差不多有三四年的时间,我没写小说。写作是一种本能,同时也是一种技艺。久不写,难免生疏;而生疏,会让人生怯。这和刚开始写作时的状态不同。那时候也生疏,但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故事都敢想,什么饼都敢画,偶尔还妄想着,自己在白纸上画得挺新挺美。人到中年,知道天高地厚,个人渺小,开始有世情苍凉的心境,开始审视生命经验。《宥真》《众生》《小野先生》有相同的特质:即小说是虚构的,但故事、人物,很多细节是非虚构的。这些真实的经验方便我快速回到小说写作的状态中来。这三个短篇小说,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我身在其中,以旁观者的立场目睹人事浮沉变迁,悲喜交集。这种写作有点儿像老摄影底片,能看到上面模模糊糊的影像,但没有像纸和显影剂,底片上面的人和物,以及风景,影影绰绰的,它们真实存在,但我们却看不到真面目和细微处。我把这些人和故事写出来,我的视线就是像纸和显影剂,很主观,所以,这些故事是小说不是散文。《为了告别的聚会》里面人物和故事不乏曲折和传奇,但确是实打实的“非虚构”。“地理空间”,是不是意味着“中年心境”?年轻时写作,只看前方;但人到中年,“开来”的力量日渐消减,倒是频频回首“既往”,好奇自己如何就成为了今天的模样,一个人的变迁是不是能代表一群人的沧海桑田?
《众生》里面的12个人物,都是我30年前认识或者见过的人;《小野先生》的原型是我20年前见过的一个日本教授,而宥真也是10年认识的朋友了。倏忽之间,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艾 伟:《为了告别的聚会》是以散文的面目出现的,可以认为是你的亲身经历,但是我们写作的人都明白,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纪实,所有的书写都是选择的结果,事实上,读《聚会》时,有些场景,特别是最后喝酒闲聊部分,非常像一篇小说的结尾,所以这个文本非常奇特,几乎具有小说的元素,人物、经历、情感、甚至不经意的故事,当然形式上完全是散文的,我想你也是当作散文的。你觉得散文可以虚构吗?可以多大程度“虚构”?
金仁顺:《为了告别的聚会》是个非常特殊的、值得把全部过程记录下来的笔会,会议之前我注意到此次笔会的主题是:沟通与交流的平台。到了首尔我才知道这个“平台”是为了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有朝鲜血统的作家诗人们举办的。我在这篇文章里面记录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包括一汤一饭。它们有力量。我在会议现场,经常会被某位讲述者的经历震撼到,我要记录下来这种震撼。
你可以说它像小说,但它不是。如果是小说,那这个故事完全是另外一个面貌。而且也不可能是一个故事啊,每个人在大会上的发言不过三十分钟,可他们身后的故事至少要二十万字。
散文可不可以虚构?答案见仁见智。我的回答是不可以。理由其实倒不是作家的写作方式问题。我跟周晓枫曾谈过这个话题,她反问我,如果事情是真实存在的,或者情感、情绪都是真实的,只是挪移了一下,那这算不算虚构?现在,我是从读者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读小说和读散文,心情截然不同。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女孩子坐着床单上了天,我们会觉得哇,这细节写太棒了,魔幻现实主义真牛!但散文如果这么写,读者会骂人的吧?作家当我们没智商吗?我们为什么读散文,不就是读那份真实吗?你现在跟我说坐着床单能上天?那是不是跺跺鞋跟就能下地狱?
我们不是为了故事去读散文的,读散文是因为文字,因为思想,因为启示,甚至因为某种调调。最重要的是真实。那些从真实事件里面榨出来的点点滴滴,如果有虚构,岂不是眼泪里面掺了自来水,不只很煞风景,还会让读者觉得受了欺骗。
因为喜欢,写物的时候难免笔端多流连;写人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节制,因为人同此心,既然是共情的,又何必那么琐碎?
艾 伟:我特别喜欢《为了告别的聚会》里关于美食的描述。我喜欢美食,但我从来不会记住美食的名字,更不知道制作方法。在描写美食方面,你非常有天赋,经常把我看得满嘴生津。在《小野先生》和《宥真》里同样也有美食的描述。我很羡慕你能把吃过的东西一一道来,并且我相信文字显然胜过真实的食物。我有时候想,其实我们浙江有非常好的美食,但这反倒让我对美食熟视无睹。当然任何地方都有美食,但你笔下的美食,活色生香,非常精细,没有“北方”的那种豪放感,反倒感到十分南方。这一方面同你的文字气息有关,你的文字有一种相当典雅的古典气息。另外我觉得你写食物相当有情感,反倒是在写人物时,文字会变得克制而冷静,这让我感到在你的潜意识里,对人和对物似乎有不同的态度。
金仁顺:我对美食一往情深。食物代表太多东西了,形而下的时候可以涵盖所有烟火气,形而上的时候又能一行白鹭上青天。食物对于个体而言,差不多是人一生成长的脉络。我常想,如果用一生吃的食物来写一部长篇小说,是不是会很好看?
我们常说,但愿人长久。人不可能长久,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山川草木,随着四季变化,但每一季都是相似的;人却是生老病死,和自然比起来,算是“速朽”的。物比人存在的时间长多了,也有意义多了,博物馆里盛载的历史是以物来设定的,人,无论哪朝哪代,都是白骨。那些迷恋古董的人,迷美迷物还是迷时间?我觉得都有。物品和美食一样,出自人手,而人会消逝,物品和美食却可以流传。和物品比起来,人多了灵魂,以及其他别的东西,人是创造者,改革家。人的不确实性太多了。因为喜欢,写物的时候难免笔端多流连;写人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节制,因为人同此心,既然是共情的,又何必那么琐碎?说重点就够了。
艾 伟:我们都知道任何文章都会有一个中心思想,《聚会》这篇散文讲的是朝鲜族“离散者”的聚会,而事实上这些人并不懂朝鲜语,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化,在我看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我看到了人们共同创造的某种致幻剂,在那一刻,他们有关于血缘关于民族的共同想象让他们开始有了一种类似“民族”的情感,但实际上,他们从本质上已经是另一种文化的人,已不是朝鲜族人,所以当我看到他们最后的行为,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和他们真实情感是有差距的,因为他们在用自己国家的文化表达这种“民族”情感,这相当不合拍,有错位,而正是这种错位,更让我感到某种生命在世的飘零感。同时我相信,这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刻,在他们离开时,回到各自生活时,也许那一刻会给他们梦境般的感觉,他们也许会在那个场景中看到一个陌生的自己。
金仁顺:是的。清醒其实从来没有缺席过。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父辈或者祖父辈有着相同血缘的作家诗人们,行为举止已经深深打上了各自水土的烙印,美国式的微笑、日本式的鞠躬、丹麦式的矜持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边界的一部分,这个笔会把大家聚集起来,寻根溯源,这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当年是遗孤,回到他们一出生就被抛弃的地方,他们内心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说实话,光是他们没有拒绝,能来参加这个集会,都是巨大的勇气。作家和诗人,都是对世界和自我不断产生质疑的群体,怎么可能通过一次聚会就有了“民族”的情感。“民族”的血缘是大家共同的,这不是自己能选择的,但除了血缘以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而主办方也没有打什么感情牌,他们选择的主题中正平和:沟通与交流的平台。让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作家和诗人们彼此之间沟通、交流,让这些人与韩国的作家诗人们沟通、交流,更有一层,是每一位作家诗人,与自己的过往、民族身份,来一场深度的沟通与交流。这个意义是渺小的,个体的,也是伟大的,影响深远的。
艾 伟:《小野先生》这个短篇很大的篇幅在现在进行时中,对长春这座城市有细微的描述,你所描述的地点和建筑显然经过精心的挑选,试图想和长春这座城市的“特殊历史”相联结,通向那个幽深的历史深处以及历史的经历者。老小野先生,这位侵略者和杀人者是通过小野先生(一位东北亚历史研究者)的转述而显现的,在这篇小说中,老小野先生的笔墨并不多,却是小说的一个核心人物。这篇小说中有三重时间,一是当下,二是战后日本,三是战争中的长春,比重是当下最重,战争最少,在三重时间的比例安排中,你显然更多着眼于当下甚至未来,你试图在这个文本中探讨过去的战争对当下或战争的后代以及经历战争的人所造成的精神困境。这个小说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小说中所展示的“历史正确”,一种中国式的关于那场战争的叙事,即两国人民都是受害者,在这样一种视野下,长春变成了小野先生的“心灵幽深之地”,而老小野先生坚定地认为他的战友不配“死在一块洁白干净的床单上”,他也不配,老小野先生因此变成了一个赎罪者。但有意思的是在小说的最后,我们看到你似乎要得更多,那个“时光隧道”(我称之为三重时间)主题再次显现,假设老小野先生从时间深处走来见到儿子小野先生,他也只好装作不认识儿子。这有很深的隐喻,一方面人总是会不自觉地不想让孩子(后代)看见自己的“恶”,另一方面在更大的意义上说,也不能不说就是反映现实的状况,一种类似于“责任的逃避”的提醒。
金仁顺:这是一篇写“痛感”的小说。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伤害和伤痛是一过性的,但对于另外一群人而言,伤害和伤痛是缓释的,时间的流逝不会让伤害和伤痛减弱,反而日渐强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些人是悲剧的,也是令人动容和尊敬的。老小野先生参加过侵华战争,做过错事,他漫长的余生浸沉在羞愧之中,无法解脱。战争有台前和台后,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但战争同时还有散场后的余韵,锣鼓喧嚣戏已了,余韵进入了个体生命,有些人转头遗忘,有些人三月不知肉味,还有些人,要用整个余生来消化。写《小野先生》是想重述反省的意义和价值,而个体悲欢,也能像一滴水滴折射战争的粗暴和摧毁性。另外,这是一篇写长春的小说。这是第一次我明确地把一个地点写进我的小说里面。我在长春生活了三十多年,早就成为了这个城市的一分子,我和这个城市心心相印,对它曾经遭遇过的炮火、侵略、摧残,我要为之做点什么。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是女性主义者。差一个字,谬之千里。
艾 伟:你大部分小说都涉及男女之间的情爱,《爱情诗》《彼此》《云雀》等,在阅读这些小说时,感觉到你对情爱的看法基本上是悲观的,缺乏信心的。至少在小说里,你不太相信男女之间的专一性,在情爱问题上你设置了一个宽阔的地带,你的小说里男人天然有这个地带,男人或多或少都很“自由”,他们总是喜欢用暧昧不明来对待情爱关系,他们的“前史”也相对复杂,不过我觉得在你的小说里那些男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里的女人,她们不再像古典小说中女性具有的那种“爱”或“欲”之间的清晰界定,既没有了像《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式的“专一”性,也没有了在“爱”的幻想下沉于“欲望”的包法利夫人的自我欺骗性,在你的小说里,女性在对待情爱时似乎不再需要安娜式的精神性,也不需要像包法利夫人那样自我制造一种虚幻的“爱”,我想说的是,你的这些女主角的行为经常被瞬间而来的情绪所俘获,她们的生命经验里“爱”和“欲”之间不再那么经纬分明,它变得很复杂(即我前面所说的宽阔地带),比如在《彼此》里,曾受到郑昊伤害的黎亚非在自己再婚的婚礼上再次扑到前夫郑昊的怀抱中。这看起来像是女性某种晕眩的时刻,实际上我觉得深藏着你对女性的个人洞见。
金仁顺:也没有“大部分小说都涉及男女之间的情爱”吧。在说起我的小说时,经常有人这么评价我。每次我都觉得有些困惑,我有那么专注地写男女情爱吗?并没有啊。我想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关系中形成的微妙。《彼此》里面的郑昊和黎亚非,固然有郑昊前女友在他们结婚时的恶意设局,但他们之后在婚姻生活中,没有积极的沟通、和解才是他们婚姻解体的关键。在我看来,现代婚姻里面的“冷暴力”极其可怕,是一种新的“傲慢与偏见”,傲慢让人懒得去追根究底,偏见让人选择不原谅。在《彼此》里面,大家都看到了黎亚非的婚外情,却没有几个人注意到她婚姻内部的悲剧。换言之,我们总是注意到了大声说话的人,而忽略了那些沉默的人,而沉默中负载的东西比喧哗深沉得多、悲剧得多。
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是世界文学史上两个闪闪发光的人物。托尔斯泰和福楼拜,两位男作家把女性写得如此动人、深刻,很了不起。如你所说,她们是“爱”与“欲”的形象代言人。在今天,女人的“爱”和“欲”变得没有那么强烈了。对于部分高知阶层和白领女性而言,甚至可以说可有可无。越来越多的女性把生存质量的高低从依附男人的状况中转移出来,“我命由我定,”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才是女性的刚需,爱和欲不过是陪衬。“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独立让女性活得有尊严,让她们的视野更宽广,对社会的抚恤和回馈也越来越多。
艾 伟:你的回答印证了我的判断,即你在写你笔下的女性时,表面上看有所谓的情绪“俘获”时刻,其实基本上她们一直保持一定程度的理性和优雅,也因此你的小说文本总是非常节制和暧昧不明,而我认为暧昧不明是特别好的品质,关于节制问题,可能是因为短篇小说的篇幅和长篇小说有根本性的不同,短篇确实需要节制。但是即便你不承认你的小说更多涉及男女关系,那么在具体的男女关系中,你还是省略了某种如安娜所需要面临到的尖锐的问题,无论把它归为精神性问题也好,还是情爱问题也罢,我觉得这其中一定有着你对女性的根本看法在,作者总是照自己的理解去想象人的,不是吗?从这个意义上,我特别喜欢你的《喷泉》,这篇小说里我看到一股野性的力量,从人物的情感深处爆发出来,也因此我感到人物有那种特别强悍的生命力。我个人觉得在你的写作中这个文本有一种“质变”,或者某种异数般的存在,它没有你此前小说里一种酷酷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这里的“小资”仅仅是指风格,而且我认为是一种蛮迷人的风格),而是回到女性更本质更粗野的内部。在《喷泉》里,我感觉到所谓“安娜”式问题的存在,而正是这些“问题”带给文本更深入的力量。
金仁顺:我少年时代是在一个煤矿长大的。在我刚刚写作时,我写了很多煤矿为背景的小说。但后来写城市题材比较多,“小资”兮兮的比较多。(我这也不是自嘲,是客观描述)。在《彼此》《云雀》这批小说写出来后,大家对我的“标签化”归类好像更确定了,仿佛我的题材就是在城市里,就是情感关系,就是阳春白雪。被这么归类当然有些不甘心不服气啊,我想给大家来一篇接地气儿的,我的地气比谁都深,一接就能接到地底下几百米。这就是《喷泉》的由来。煤矿生活虽然是在我少年时代,但影响深远,矿区里的人,都有股野性,有股义气,有玩命的狠劲儿。这种性情打底,人与人的爱恨都是强烈的,大开大合。《喷泉》虽然是个悲剧,但调子却异常明亮,爱和恨、欲望,浓度和纯度都非常高,相比之下,其他的小说优雅或许有,但温吞也是真的。但这篇小说的气质还是未能跳脱出多远,也可能写作久了,真的就有了某种腔调吧。去年年底我把《喷泉》改成了一个小剧场独幕剧。对故事做了很大的调整,但三个人物的性情、性格以及行动逻辑没变,这个剧演出之后,差不多人人都爱上了吴爱云,她身上的明亮非常动人。
艾 伟:总的来说,我觉得在你的小说里一点都不女权。而且我认为你对男性特别宽容。你小说里的男人,是一种有力量的存在,他们通常优雅得体,生活优渥,出轨或移情别恋当然也是经常的事,但在你的文本里男人身上发生的这些事只是“现象学”,你把他们当作天然如此,你没有抱怨,当然也没有批判,在你的小说里,从来不追究男人的道德问题,对女人也是如此,不追究。这一点很好,我认为这是小说家应该做的。所以,我觉得你是个对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没有挑战或反抗的女作家,而只是细微观察这一秩序下男人或女人这一古老关系的现代模式。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你的访谈中谈到你是个女权主义者时,我不能认同。我觉得你不是。你在小说里对男人宽容极了。我认同你前面所说的话,你其实是一个女性独立主义者,在你的观念里,女性独立比什么都重要,没有男人也可以活得很好。这也是长篇《春香》的基本观念。在《春香》里,倒确实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女性中心主义,我视之为一首关于女性独立人格的赞美诗。总体而言,无论《春香》也好,还是你那些关于两性关系的短篇也罢,你对男女关系的基调是悲观的,也许真是这种悲观让你心怀宽容。
金仁顺: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是女性主义者。差一个字,谬之千里。《春香》这部小说也不是女权主义小说,而是女性主义小说。或者如你说所,“女性独立小说”。《春香传》是朝鲜半岛流传了三百多年的民间故事,那个时候的朝鲜男尊女卑以及门第划分极其严苛,女性生活没有尊严,更谈不上自我。在《春香传》里面,女人对男人要绝对顺从,勇于自我奉献和牺牲,那么最后会有男人来救赎她们,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样的内容,居然是半岛最著名的民间故事,南原地区现在还有个“春香”小姐的选美活动。我想写另外一本《春香》,我的春香没有传,不是用来流传的,只是证明一种可能性:女人有能力靠自己过上也许说不上幸福、但却自由的生活。《春香》里面的女人没有女性中心,恰恰相反,香夫人被男人抛弃,春香是个非婚生女,银吉被夫家嫌弃退婚,小单是个罪犯的女儿,这些女人是当时社会的“负面”人群,她们集合在香榭,香夫人利用自己的智慧,让她们衣食富足,自由开明,实现了“负负得正”。但即便如此,香夫人也忧虑春香的未来,因为她知道,她们的美好生活是个意外,是当时严苛社会制度下偷来的浮生半日闲。因此她处心积虑,安排春香嫁入豪门,但春香最终选择留在香榭,豪门固然可以遮风挡雨,但自由更可贵,而且在香夫人生病后,她要担起护佑香榭的职责。对于女人而言,如果生存问题自己能够解决,爱情不过是锦上添的几笔花花草草。你说得很对,我对男人没有褒贬,我从来没抹杀过男人的影响力,但我对女性确实是偏爱的,我愿意花费更多的心思和笔墨让女人们摇曳生姿、楚楚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