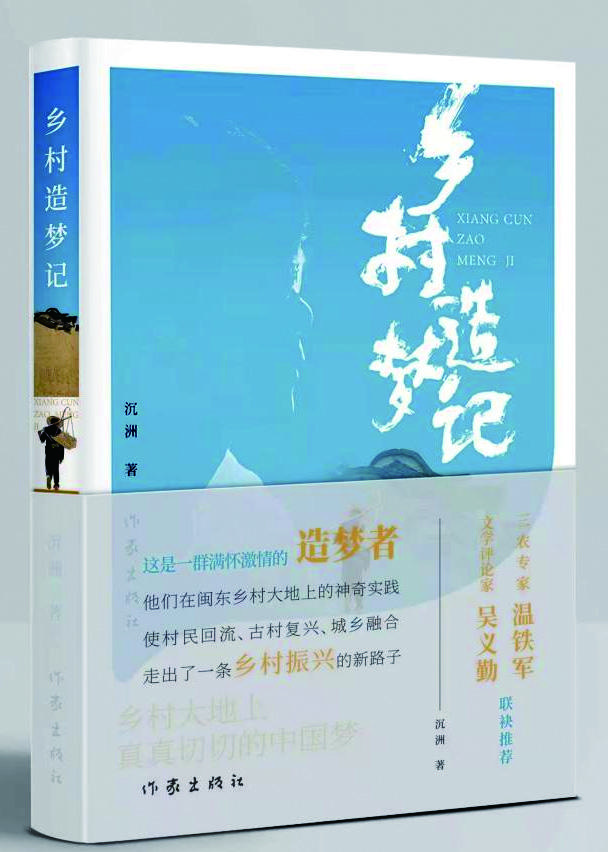陈 涛:2020年我去宁德拍摄反映脱贫攻坚的纪录片时,曾多次听当地人讲到龙潭村的神奇,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感受,现在通过阅读你的《乡村造梦记》对这个地方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为何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
沉 洲:2019年6月,我和一群作家赴闽东高山县屏南采风,那时我正为三联书店写一本闽地饮食的文学随笔《闽味儿》,想以该县的药膳饮食为题材。抵达当晚,老朋友来叙旧,除了聊药膳,他还讲了个奇葩事:有位艺术家在偏远的龙潭村教农民画画,引来100多位城里人常住,村民也回流了300多人,“空心村”变成“网红村”。他的理念是发展文创产业,凭借畅达的网络鼓动年轻人创造文创产品。
这引起我的兴趣。此前,通过各种资讯,耳闻目睹的乡村振兴进行时就是雄浑的钢琴交响曲,这个地方居然用二胡、唢呐演奏,不同凡响,还充满了在地文化。这事有天方夜谭的感觉,居然发生在一个空心村?当时心里也纠结了一下,是不是换个选题,去采访这个人这个村?
陈 涛:你为人相对散淡,怎么会突然想投入两年时间来介入这个主旋律题材的创作?
沉 洲:我的确不轻易一朝为某人某事感动。屏南的事只是偶尔会在脑海跳出来,与我热衷大自然游走的经历自行链接。记得曾经在游人如织的闽南云水谣古镇,当地朋友说: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别小看这一间间小店铺,一年挣10万元不算事。也曾经走访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村落,村主任介绍:年轻人都不去城里打工了,按人头分到各家的茶园,单卖茶青一年10万元打底。
前者靠自然人文景观,土楼申报世界遗产成功,成为多部当红电影的外景地,遂成旅游打卡点;后者依托独有的物产资源,以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品位,获得高附加值。
这触动了我的神经,广袤的乡村大地上,还有多少自然人文景观和物产资源不见特色甚至匮乏的乡村,在摧枯拉朽的城市化进程中,等待它们的命运必定是人去楼空,乃至消亡吗?
无意中我看到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据冯骥才先生调查,2012年之前的10年间,全国自然村每天以80到100个的速度消亡。这个数字让人触目惊心!这时《闽味儿》书稿交了,屏南乡村发生的事,冷处理半年,居然还惦记着。感觉自己与那里的人和事“确认过眼神”,是对的选题,于是不再迟疑,马上联系老朋友周芬芳获取资料,查阅并深入学习。自从决定写这部书,我便认定它进入了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深宅大院”,而屏南文创复兴古村的特别在于,它是从侧门走回廊再绕进正厅的,并非媒体宣传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一个非体制内、毫无背景的艺术家,以其对当下时代的宏观预判和个人智慧,通过艺术教育直接把乡村系统换成智能基座,就地现代化,让农民变成文化创意的贡献者。事后反思,我是被这个人和他竭力去推行的事以及那些县乡村干部们的情怀感染了,才情不由己地踏入这座原本离自己生活非常遥远的一座大院。
新年伊始,周芬芳电告,几位外地艺术家年前都在。我立刻动身,先做粗线条采访。10多天后回来,武汉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我窝在家里昏天黑地整理采访录音,阅读屏南方面不时传来的资讯。到了4月底,屏南疫情防控警报解除,立刻赴那里的文创村采访了近两个月。
陈 涛: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从籍籍无名到声名鹊起,肯定经过了一段异常复杂的时光,根据你刚才谈到的采访,你肯定拥有非常多的采访素材,如何使用这些材料,如何完满地展示这段历程,在艺术上有哪些考量?
沉 洲:整理近百G采访录音的同时,我开始考虑结构问题。对长篇文学作品,一个好的结构是它不可或缺的艺术之美。但从掌握的资讯又苦于无从下手。五年多来,屏南传统村落文创产业进程架构庞大,“现身”的人物彼此纠缠,发生的事纷繁杂沓。我想到做减法,其他几个村落的人和事只得忍痛割爱,仅留下林老师这一条主线。即便如此,梳理起来依旧千头万绪。我提醒自己,结构只是外衣,应该为所写的人和事量身定制。
为了让人看明白文创理念怎样一步步兑现,大的结构上,我采取顺时间轴的方向往前推进,分三个文创村镇展开,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讲述清楚。屏南文创振兴乡村一直在健康地丰富和壮大,它的内生动力使之不会停滞下来。这个结构的时间轴缘起林老师到漈下村开展公益艺术教学,此前发生的人和事全部倒叙插入;截止于疫情发生后的五六月,这是因为如何激活一个空心村的原理已然成型。
全书选择了第三人称的叙述基调以求客观。写作中偶现第一人称,这样可以变换一下节奏,丰富层次;其次有些人亲历的事多、时间长,选择第一人称可以简洁笔墨。下部写到8位城市来的新村民,全部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对这些区别于主流观点的逆城市化者,“我”的叙述角度有带入感,亲切可信,同时也揭示出他们的复杂心理,更有说服力。
陈 涛:通过阅读这部作品,以及你艺术化的处理方式,我可以感受到你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与心血,尤其是看到其中许多性格各异的人物,你跟他们有比较深入的交流,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比较深的触动?
沉 洲:8月理好大纲,进入写作状态时心里急起来,恨不能转瞬成书,快快把这件让人脑洞大开之事告诉天下人。时常白天无流畅思路,躺上床要写的人物又在脑海里轮番登场,想写的故事也一幕幕上演,还不时借梦排闼闯入,让人夜不成寐。我只得昼夜不分地写,白天困了睡,深夜睡不着起床执笔属家常便饭。100多天的写作时间里,身体备感煎熬,最后失眠成瘾。
那些用生命激情为一方农民谋幸福的人,那些不指望因此得到提拔、为乡村振兴义无反顾的人,那些冒仕途风险、勇于工作创新的人……写作时活灵活现地在眼前晃动,我被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经常鼻头一酸,双眼便泪水盈眶,这在我相对理性的写作经历里是不曾有过的情状。
写作过程中,我思考了很多现实中难以解开的结,对那些基层干部开展工作之难感同身受。
按理说,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可是很多地方,今天的城乡学校师资配比依旧同一标准,有执业资质的教师也沉不下去。两三年前,起码在我采访的行政村还有拆点并校的现实存在,希望留在乡村创业的中青年为了孩子只能进城,这无疑加速了乡村的空心化。
我所采访的行政村,村两委里只有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基本工资加绩效补贴是1900元,其他十几位村两委干部月津贴200元。乡村留不住人才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化,使得艰苦的付出待遇反而更低。但凡培养出一位优秀老师、医生什么的人才,都会往条件好的城市流动。人才是乡村造血机制的核心,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农村老宅通常聚集了三四代人口,原本就不够住。城市工业化进程加速后,很多人进城务工,甚至成为城市人口。如今乡村振兴了,一些想回流的村民没房子住,而配套农民新村又与土地红线相左。
空心村的山垄田、山坡地,因为与他处工业用地统筹置换,变成十八亿亩红线内的“农保地”。这样的地,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力成本高,种一亩水稻要倒贴几百块钱,不少土地已经抛荒了20多年。如何在生态植被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发挥更大效益?
写完这部书,我这个原本散淡的人也变得忧心忡忡起来。
陈 涛:也正是有这些现实困境,我们的乡村更需要不断地“造梦”。《乡村造梦记》是一个既形象又有着丰富内涵的书名,在你看来,龙潭村所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怎样的“梦境”?
沉 洲:这本书的最初名字是《我那山清水秀的乡村》,从主观感情上讲,是想把自身融入进去,乡村发生的人和事与我有切肤之感。用第一人称介入和收尾,就是希望产生带入感。正文前的楔子,是我初次进入龙潭时对匪夷所思的现实发出的众多疑问;尾声是我最后一次到龙潭采访,发现林老师对疫情后的龙潭现象又有新解。但这个书名太宽泛。
屏南的文创振兴乡村在外人眼里就是一个梦幻,而造梦不是做梦,是有目标地把梦想一步步呈现出来,整个过程犹如造屋,一块砖一片瓦,在时光里耸立蓝天下。而且,复兴中国百年梦,乡村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也是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的意义所在。
陈 涛:结合你这部作品的创作,你觉得在乡村振兴当中,我们作家何为?应该如何去做才能更好地展示出文学的力量与魅力?
沉 洲:乡村振兴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中国的乡村振兴是在举国体制背景下登上国际舞台的,有不成功的经验等待甄别,有向成功萌芽抽枝的经验等待总结和业已成功的经验等待传扬,文学作品特别是非虚构类文学作品不应在此缺席。作家应投入火热的现实生活,采撷、收集始料未及的素材,让川流不息的生活来感动自己,激发抒写能量,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