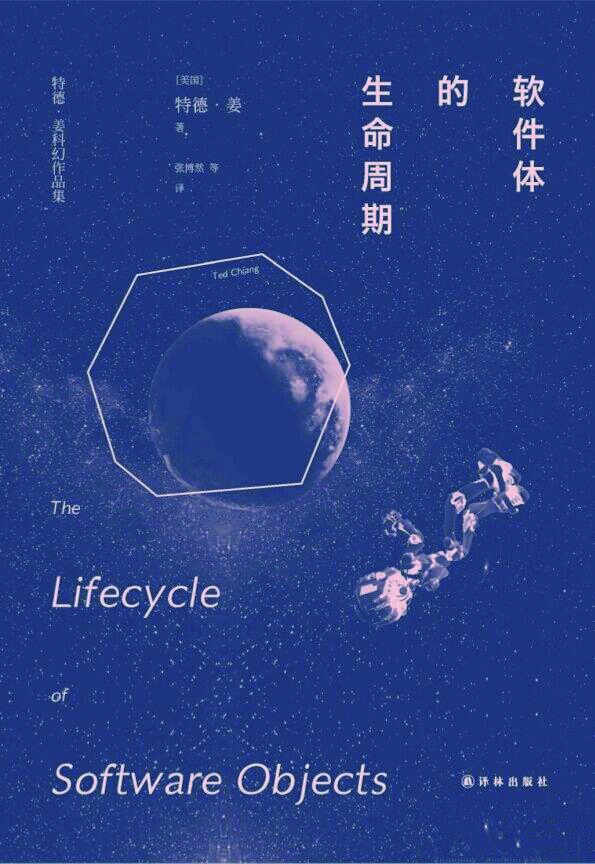科幻人工智能主要是一种图像志式的研究,通过确定科幻人工智能的一些相对稳定的类型元素和主题元素,解开反复出现的类型密码。科幻人工智能真正发展起来的标志不是从历史中钩沉而出的某个旧例,而是相当数量的当代科幻文学或者影视创作实践的积累。我们要寻找的不是一个历史线索,而应该对看似爆发性增长的科幻人工智能作品进行批判性考察,思考为什么在某个时间段,人工智能形象开始大量出现,成为科幻的标配,甚至成为主角。
最近一些年,人工智能题材成为科幻作品的一个耀眼类型,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科幻作品不断涌现,人工智能不仅在生活应用中成为焦点,在科幻小说和电影中也成为颇受瞩目的主题。然而,在这样的人工智能科幻热潮中,我们又会产生一些混杂无序的感受,似乎“人工智能”成了一个高流量的IP,只要跟人工智能有关,大家就愿意观看,而不管内容怎么样,实际上讲的什么。尤其是,过往的一些科幻作品也重披人工智能外衣,这虽然没有什么不好,毕竟一种科幻类型能够容纳的成员越多越好,但是如果不对一个科幻类型进行一些必要的限定,就找不到恰当的定位,而这一科幻类型最核心的特征和性质也容易从我们的眼前溜走,对这一类型的创作和进一步研究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人工智能的奇观性与未来感
通常议论的人工智能科幻包含多样,一些著名的科幻作品可以归入科幻人工智能范围,比如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我,机器人》及同名改编电影(2004),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及改编的电影《银翼杀手》(1982),沃卓斯基兄弟执导的《黑客帝国》(1999)等等。这里当然没办法列一个详细的清单,因为再详细的清单都可能出现遗漏,而且由于所持观点不同,这样的清单也可能有变化。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些科幻作品都属于科幻人工智能范围吗?为了做这样的澄清,首先需要反省一下我们所持有的科幻人工智能观念。科幻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并不等义。现实的人工智能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观念型的,指通用型人工智能,这主要是理论研究和阐释;一类是工业型的,指的是在现代科技领域中的具体使用,目前最成功的人工智能主要集中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科幻人工智能更多集中在通用型人工智能上面,当然也会涉及具体的工业制造。科幻人工智能天然就要超出人工智能的实际发展,这是科幻人工智能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引发观众对作品的兴趣。相对来说,科幻人工智能更倾向于通用型人工智能,这主要在于它更能提供一种奇观性的东西,引发我们对于生活的新奇感,这也是科幻作品所塑造的文化意义和价值所在。
我们可以看到,科幻作品对未来场景的想象和描述充满魅力。很长时间以来,科幻作品所描绘的未来技术基本都可以用“人工智能”代替:所有那些超越现代技术,达到更高级、更便利的技术应用都是人工智能。由于当代技术本身就具有相当的智能性,科幻构想更要超出当代技术,迈向与人的某种能力可以比拟的复杂功能,而这又代表未来技术方向。人工智能带有的想象特征隐藏在各种社会表述当中,是构成社会文化心理的有机部分。可以说,在科幻作品中围绕人工智能所展开的种种未来性的讨论,无论我们是对它恐惧,还是对它持乐观态度,都是我们通往人工智能的必由之路。
科幻人工智能叙事中的未来深深地打上了当代文化烙印,因为这里的“未来”不是真正的时间维度上的未来,而是经由文本想象的概念性存在。因此,它从来不是单纯的未来,而是隐藏着当下科技发展的基本方向与文化欲望,包裹着多种元素的形式化的复杂未来显像。由于它与当代科技发展的关联非常密切,并且某些科幻作品具有极高的思想实验价值,提出可以付诸实践的新的科技形式,反过来也促进当下科学技术的进展。尤其是科幻中的人工智能叙事,直接挑动当代文化的核心关切,影响我们对当代人工智能的深层理解。
科幻人工智能的定义与归类
回到这个话题,那么,科幻人工智能到底指什么呢?我们将用它指一些特定的科幻作品中存在的人工智能形象,它们表现出与人相近的某些素质,比如外形像人,或者心智表现像人,我们将其视为现实中的人工智能的同类。从这一角度,我们看到,晚近的一些科幻小说和科幻剧集更接近工业型人工智能,比如特德·姜的系列短篇,《黑镜》的部分剧集等;但因为科幻本身的目标并不是生活中的人工智能应用,而是我们的人工智能观念,所以更多的科幻人工智能形象接近通用型人工智能,更直接地说,利用我们目前的文化心态,用人形人工智能形象来进一步刺激我们的想象力和观念,以强化或推动人工智能的某种预期。
哪些可以归入科幻人工智能呢?科幻人工智能这一类型的真正开始是以两个条件为基础的,一是标准,二是规模。前者解决判断的尺度,后者表明事实的依据。提出标准问题的原因是,既有的科幻人工智能分类比较混乱,几乎所有非人类的科幻人类形象都可能被划入科幻人工智能范围,但这并不能带来一个清晰的分类,对于科幻人工智能的整体类型分析也会带来混乱。因而,可供鉴别的标准是必要的。一个较易受到公认的标准是图灵测试,即科幻作品中出现的人工智能形象要关涉图灵测试,而图灵测试有两点是关键,一是机器,二是智能,简单地说,就是探讨机器能否进行思考的问题,由于科幻总是比实际理论要更泛漫一些,所以会把机器思考推广为机器具备了人的某种意识或心灵,而展现这一测试的形象就是人工智能形象。依此标准,还需要此类科幻作品成规模出现,这标志科幻人工智能类型的有意识确立。
从这两个标准看,虚拟人明显是可以归入的。最标准的就是特德·姜的《软件体的生命周期》和电影《HER》,当然此前大量的计算机自我意识觉醒作品也可以放入此类,比如克拉克的小说《2001:太空漫游》(1968)。一般划入人工智能的生化人和克隆人则不容易归入。生化人主要是生物合成人,直接具有人的外观和智能,他们往往具有特殊通力,所展现的内容与智能问题无关,而更多与人类未来相关。克隆人同样天然就具有人的智能,此类形象更多与人类危机有关。一般来说,生化人和克隆人已经默认其存在智能,智能现象并不是显现的主要方面,更重要的是,生化人和克隆人都是有机体,而人工智能首先强调的是非有机体的智能问题,所以这两者从根本上是不适合的。
机器人科幻可以直接划入科幻人工智能吗?乍看起来似乎可以,但仔细想一想也不尽然。机器人也要分具体情况。机器人题材可以不关注智能问题,毕竟外形上的相似性已经具有奇观性效果了,比如一些早期的机器人形象有些像人,但又有些粗笨,这样的形象已经足够给当时的人们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了,或者当时的文化想象只达到这一程度。1927年弗里茨·朗格拍摄的黑白片《大都会》可算是最早将机器人搬入银幕的科幻片,机器人玛丽亚有着金属外壳和女性面庞,可以操纵站立和行走,可惜,她更多是反面性质的,只是影片中一个小角色,但毕竟代表了一种想象形式。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系列影响巨大,对后来的机器人科幻树立了模板作用,但如果细读,就会发现,并非其笔下的所有机器人形象都可以归入人工智能,只有早期的机器人,比如《我,机器人》(1950)中的小机才涉及机器智能问题,《曙光中的机器人》(1983)中的机器人丹尼尔则已经智能超过人类,《基地》系列中出现的升级版丹尼尔机器人则已经接近神人的地步。1977年《星球大战》中机器人R2-D2、C-3PO的形象憨态可掬,语言简单可爱,同时,步履蹒跚,配上金属质感的外壳,外表流畅。相对来说,早期阶段的机器人动作表现较好,但智能并不太高,有些呆头呆脑,这其实是与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相关。虽然所谓的人工智能概念早就提出来了,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一概念追溯到图灵1950年发表的创世纪性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1956年麻省理工学院约翰·麦卡锡在达特茅斯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一概念,但这只是观念化的进展,工业化还没有跟上,这也限制了科幻人工智能的想象。
将机器人划入科幻人工智能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进行历史性的追溯,比如上溯到1927年。但是这可能并不具有真正的意义,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机器人这一形象,并非以人工智能出现,人工智能的头衔不过是我们从当代角度的回看而赋予它的。
勃兴中的反省与期待
科幻人工智能真正发展起来的标志不是从历史中钩沉而出的某个旧例,而是相当数量的当代科幻文学或者影视创作实践的积累。我们要寻找的不是一个历史线索,而应该对看似爆发性增长的科幻人工智能作品进行批判性考察,思考为什么在某个时间段,人工智能形象开始大量出现,成为科幻的标配,甚至成为主角。
2016年AlphaGO战胜围棋棋手李世石,无疑是一个现实触因,它所导致的震惊远超电影中展现出的未来人工智能状况。这场对弈背后科学观念的成熟、文化氛围的酝酿在此前已经准备就绪。从此开始,未来之事不再遥远,人工智能大量进入生活,与人相融。大致从2000年左右开始,科幻人工智能作品就开始出现,比如2001年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人工智能》,这部影片描绘了普通家庭中出现机器人的故事,借用皮诺曹这个木偶男孩变成真正的小男孩的童话故事线索,讲述机器人小男孩重寻他的人类母亲之爱的故事。在电影中,机器人男孩从外表上看已经跟真人无异。《人工智能》最后的场景放在两千年后,那时人类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度进化、能力强大的人工智能,他们几乎拥有神一般的能力,可以进行生物再造。电影讲述的是机器能否获得人性的问题,呼应了当时时代的氛围。虽然《人工智能》探讨了与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伦理反应和人性想象,展现了人工智能的远景格局。但究其本质,这部电影也只是借人工智能的名义讲述了一个类似生化人的故事,并没有把机器智能特性凸显出来。2016年的国产科幻电影《人工智能:伏羲觉醒》同样打上了人工智能的名号,虽然内容质量上有些勉强,但主题却是关于机器觉醒问题,反而更接近科幻人工智能电影的内涵。
真正的科幻人工智能类型的兴起,需要把人工智能当作主题和书写对象的作品大量出现。2010年之后,这一类型的发展明显成勃兴之势,特德·姜的小说《软件体的生命周期》(2010)讲述的是虚拟智能的数码体如何“成长”的故事,它们虽然无法离开环境母体,但最终具有了自身的判断力;斯派克·琼斯编剧并执导的电影《HER》(2013)展现无形象的代码程序萨曼莎与人类恋爱的故事;亚力克斯·嘉兰导演的电影《机械姬》(2015)是标准的图灵测试场景,机器人骗过人类、获得自由,这似乎表明机器人进行真正思考的可能性;科幻电视剧《黑镜》(2016)受到现实人工智能发展的鼓舞,不少集涉及智能出行、智能控制、智能觉醒等主题,当然这些科幻智能状况远远超出现实的人工智能可实现的水准,还触及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复杂的情感与伦理困境问题:面对一种具有完整人意识的有机综合体的时候,人或者“人”,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而科幻电视剧《西部世界》(2016)更讨论了智能仿生人这一群体与人类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展现更冷酷的杀戮世界,讲述人工智能的反叛。这些科幻文学和影视作品刺激了科幻人工智能类型的成熟,真正将科幻人工智能推向高潮。
实际上,确立一个科幻人工智能的标准只是一种研究方式,它并不像实际人工智能技术一样,可以进行数据上的硬性衡量。科幻人工智能主要是一种图像志式的研究,通过确定科幻人工智能的一些相对稳定的类型元素和主题元素,解开反复出现的类型密码。同时也应注意,任何一种科幻叙事都有为适应读者和观众需求的目的,划定一个人工智能形象的范围像是解开一把旧锁,但新锁还可能在形成中。只有以一种变动的标准来对待科幻人工智能类型的发展,我们才容易较为准确地把握这一类型,从而更准确地找到适应阅读者需求的形象形态,以及突破这一形态的内在潜能,从而不断创作出优秀的科幻人工智能作品。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