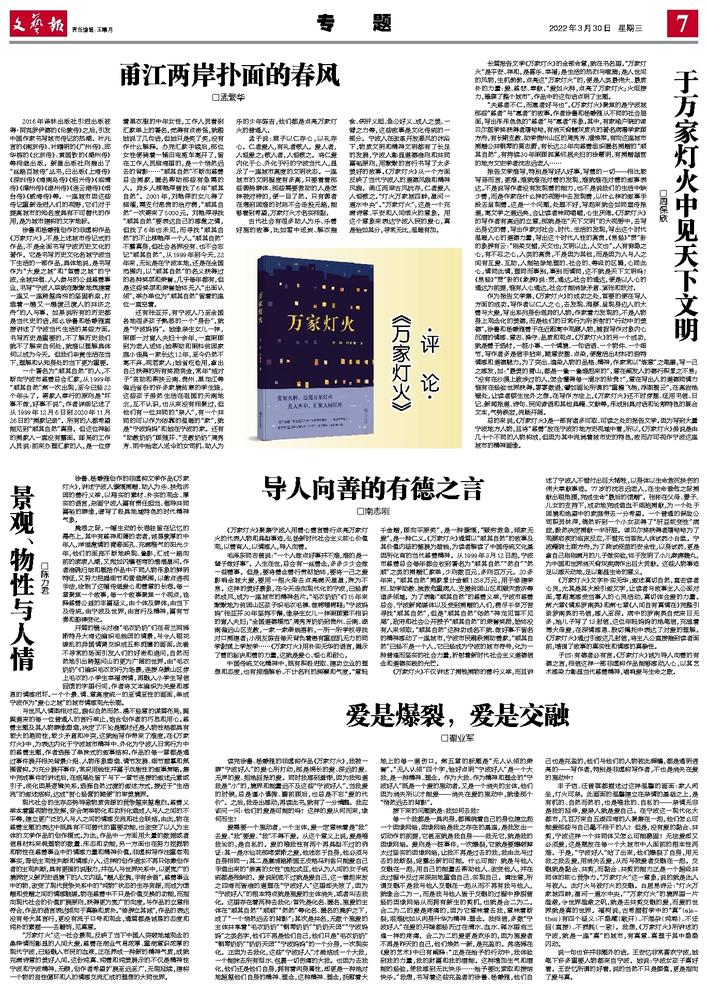读完徐鲁、杨静雅的非虚构作品《万家灯火》,我被一群“宁波好人”的爱心所打动,那是绵长的爱、深远的爱、无声的爱、拒绝回报的爱。同时我感到羞惭,因为我知道我是“小”的,境界和能量远不及这些“宁波好人”,当我爱的时候,总是谨小慎微、瞻前顾后,也总是不忘“爱的代价”。之后,我走出感动,再读此书,就有了一分清醒。我应该问一问:他们的爱是可能的吗?这样的爱从何而来,缘何而生?
爱需要一个施动者,一个主体,爱一定意味着是“我”去爱、“我”要爱、“我”不得不爱。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是唯我论的,是自私的。爱的唯我性有两个再典型不过的例证:其一是水仙花那喀索斯之爱,他迷恋于自身,他必须与自身相同一;其二是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只能爱自己手造出来的“崇高的女性”伽拉忒亚,他认为人间的女子统统都是残缺的。爱说到底不过就是爱自己,这一看起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在“宁波好人”这里却失效了,因为“宁波好人”的根本特点就是施爱的主体消失,或者叫去我化。这里存在着两种去我化:首先是化名、匿名,施爱的主体在“顺其自然”“顺顺”“然然”等化名、匿名的掩护之下,成了“一个悄然远去的背影”;其次是共名,无数个施爱的主体共享着“毛衣奶奶”“钢琴奶奶”“奶奶天团”“宁波妈妈”之类名字,他们不再是他们自己,他们只是“毛衣奶奶”“钢琴奶奶”“奶奶天团”“宁波妈妈”的一个分身,一次现实化。正因为去我化,这些“宁波好人”才凝结成一个大我,一个能抹去所有泪水、包裹一切伤痛的大我。也因为去我化,他们还是他们自身,拥有着肉身属性,却更是一种绝对地超越他们自身的精神、理念,这种精神、理念,抚慰着大地上的每一道伤口。第五章的标题是“无人认领的荣誉”。“无人认领”四个字,恰好点明“宁波好人”是一个大我,是一种精神、理念。作为大我、作为精神和理念的“宁波好人”既是一个爱的施动者,又是一个消失的主体,他们因为消失所以才能爱——消失在爱的施动中,就像那个“悄然远去的背影”。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如何去我?
每一个我都是一具肉身,都围绕着自己的身位建立起一个因缘网络,因缘网络是我之存在的基座,是我发出一切动作的前提,它甚至就是我自身——我无它,就是我的因缘网络。爱则是一桩事件,一次爆裂,它就是要爆破掉太过坚实的因缘网络,让我不再是过去的我,我由此与过去的我断裂,绽露出新的可能。什么可能?就是与他人交融在一起,用自己的能量去帮助他人、改变他人,并在此过程中反过来深刻地重造自己、实现自己。请注意,所谓交融不是我与他人交融在一起从而不再有我与他人,就像合二为一,而是我与他人皆于交融的过程中挣脱曾经的因缘网络从而拥有新生的契机,也就是合二为二。合二为二的爱是疼痛的,因为它意味着去我,意味着断裂,艰难犹如从肉身升华为精神、理念。我相信,多数“宁波好人”在爱的开端都经历过在清水、血水、碱水里泡三遍一样的疼痛。合二为二的爱更是欢乐的,因为施爱者不再是昨天的自己,他们焕然一新,是充盈的。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已有阐释:“正是在给予的行动中,我体验到我的力量,我的财富和我的潜能。这种增加生气和潜能的经验,使我感到无比快乐……给予要比索取和接纳快乐。”我想,书写着这些充盈者的徐鲁、杨静雅,他们自己也是充盈的,他们与他们的人物彼此辉耀,都是通明透亮的——写作者,特别是非虚构写作者,不也是消失在爱的施动中?
丰子恺、汪曾祺都描述过这样温馨的画面: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此画面的温馨建立在亲情的基础之上,是有机的、自然而然的,也是唯我的、自私的——亲情无非是我的延伸,爱亲人就是爱自己。在宁波这一现代化大都市,几百万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怎么可能爱那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但是,没有爱的黏合、共契,宁波这样一个共同体又怎么可能稳固?无法爱却又必须爱,这是摆放在每一个大城市中人面前的根本性两难。于是,“宁波好人”站了出来,他们爆裂了自身,用无我之我去爱,用消失去爱,从而与被爱者交融在一起。交融就是黏合、共契,而黏合、共契的能力正是一个超级共同体的核心竞争力。“万家灯火”这一意象,说的就是此人与彼人。此灯火与彼灯火的交融。白居易诗云:“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万家灯火”的境界里一片澄澈,令世界澄澈之矾,就是去共契交融的爱,而爱的世界就是真的世界。福柯说,古希腊哲学中的“真”(alethes)有四个涵义:不隐藏(敞开)、不混杂(纯粹)、不迂回(直接)、不损耗(一致)。我想,《万家灯火》所讲述的宁波,就是一座“真”的城市,有真意、真理于其中隐隐闪动。
说一句也许并非题外的话。王安忆非常喜欢宁波,她笔下许多重要人物都来自宁波。她说:宁波女孩子真好看。王安忆所谓的好看,说的当然不只是颜值,更是指向了爱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