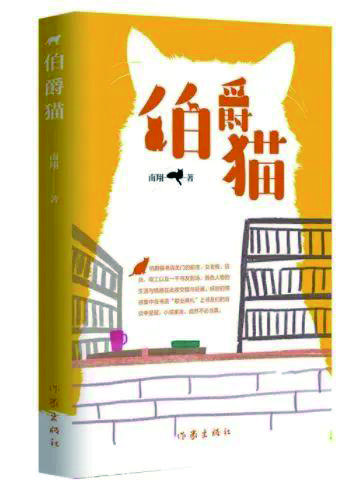日常诗学,或情绪的传记
□于爱成
读南翔的小说,总会自觉不自觉想到契诃夫、钱锺书、汪曾祺,当然在读《伯爵猫》这部最新短篇小说集的时候,我也会想到同在深圳且近10年来专务深圳题材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邓一光,想到诸如吴君、蔡东、盛可以等深圳小说的中生代代表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深圳题材的作品,试图发现南翔这位学者型作家的独特之处。
南翔的短篇小说创作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以《女人的葵花》作品集(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为界之前的作品,尚有传奇和奇观的追求,之后尤其是从《绿皮车》(花城出版社,2014)及《抄家》(花城出版社,2015)开始,便开始发生风格的变化。这一风格的变化,实际上可以从创作主题上分成三个方向,知识分子题材、“文革”反思题材以及自然主题题材。三个题材形成三种主题,不过呈现在最新作品集《伯爵猫》(作家出版社,2021)也即2017年以来创作的作品,可以看到作者最钟爱、最典型的主题已经明确,即个人的生存与存在困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又隔膜,以及试图理解和走近彼此的努力等等。一言以蔽之,即现代城市人的生存之境地和存在之省思。
《檀香插》写的是背叛(出轨),《乘三号线往返的少妇》写的是寂寞(情感缺失的煎熬),《玄凤》讲的是孤独(丁克难守),《痛点》讲的是不安,《车前草》《选边》讲的是沦陷(底线),《回乡》《疑心》讲的是伤痛(历史的后果),《曹铁匠的小尖刀》讲的是思念(悼亡),《伯爵猫》讲的是分子化的人抱团取暖相濡以沫,《凡·高和他哥》讲的是成全(亲友之间的互相成就),《珊瑚裸尾鼠》《果蝠》延续了作者对生态问题的持续反思,《乌鸦》写成了一篇寓言:人情淡漠,人不如乌。全书的压轴之作,也即华彩乐章,《钟表匠》不负重托,名副其实。我们在这篇作品中,看到了作者最性情的演绎,最欣悦的礼赞,最深情的祈愿。
应该说,《伯爵猫》小说集中的作品,除了寓言《乌鸦》和官场讽刺小说《苦槠豆腐》,都立足于捕捉、挖掘现代城市人心理状态和生存难题这一理念,这也似乎成为了南翔当下创作的主旨。这批短篇小说作品场景相同,大抵是在深圳,正是作者南翔的生活场所;叙事者即观察讲述见证思考的当事人,第一人称为主,部分第三人称,无论是“我”还是第三人称的某某,基本都设定为教师的身份,有些作品中更是直接大学教授的南翔本色出场,亦真亦幻,像极了非虚构;小说结构如同双声部的奏鸣曲或者更复杂一些的抒情变奏曲,日常生活化取材,散文化叙事,抒情性强,氛围感强烈,形成了南翔短篇小说结构的特点,即南翔的短篇小说,书写了一个个他的“情绪的传记”。表面看来,作品的讲述多貌似漫不经心,经常还枝蔓横生旁逸斜出,作者掩饰不住把故事打散的倾向,但这样的散点透视,作家不想过于聚焦某一点的背后,是作者在作品结构方面的一种用心。
也就是说,一则为了探索小说文体的可能性,让小说摆脱各种八股,南翔祭出了“无不可入小说”的独门法宝,让自己的生活直接进入小说叙事;二则为了让小说更像小说,南翔对每个作品的处理,实际上是极具匠心的,大多作品像极了奏鸣曲和变奏曲的音乐结构,一个主声部或者说一个明主题的后面,总会跟着一个副声部或暗主题,比如说,《檀香插》背叛主题后面的美丑错位,《乘三号线往返的少妇》寂寞背后的伦理失据,《玄凤》孤独背后的情感替代,《痛点》不安背后的人自私无力共情,《车前草》《选边》沦陷背后的忏悔净化,《回乡》《疑心》伤痛背后的人性暗昧,《曹铁匠的小尖刀》思念背后的执念坚守,《伯爵猫》相濡以沫背后的城市公共空间塑造,《凡·高和他哥》成全背后的励志自救,《钟表匠》情义背后的成败故事等等。
这些小说汇总起来,我们已能看到南翔最为典型的一个手法,即他在钱锺书开拓的现代知识分子小说的文脉上,融入汪曾祺的散文化美学风格,在西方现代小说尤其是契诃夫短篇小说传统谱系内,中西兼容,所创造性探索的一种当代中国短篇小说范式:骨子里是文人气的,趣味上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指归是自由主义的,情怀是民间社会的,道德感是宽容平和的。南翔笔下的深圳是实存的,他不避为深圳人,尤其深圳的知识者,写下“情绪的传记”。
既然是“情绪的传记”,也是人物的心灵素描,是时代氛围的塑形,南翔的作品就显然具有比较强的心理艺术特点,或者说具有捕捉把握和理解展示人物内心的强大能力。《伯爵猫》中的每个作品,都有对人物内心隐忍不发的分析判断,但作品并不明说,所以几乎所有的人物之间的关系,都呈现一种心理的隔膜,不能也无意互相理解,无论夫妻还是恋人,无论师徒还是兄弟朋友,很大程度上都是自说自话,心意只是依靠猜测。哪怕是《钟表匠》这样的都市情义,其实两位老者之间,也是各取所需的,并没有达到一种完全的平等。
散文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氛围营造在小说中的吃重,并承担了整体性诸如中国文论中所说的“赋比兴”中的“兴”的功能,不仅仅是烘托,更像是象征。在南翔的大部分小说中,因大量使用富有情感意义的细节,营造出丰富而复杂的氛围,使得小说的变奏曲式结构和情绪传记的手法,在叙事者的情感基调和环境氛围中展开,呈现出来浓郁的情感色彩。其效果就会是诗意的,甚至抒情的,既然小说偏好是非线性的、非戏剧性的、反高潮的,甚至是反性格和反情节的,那么读者的兴趣点就已非关注情节的发展、人物的性格、故事的跌宕或者短篇小说擅长的“反转”技术桥段,而是放在了叙事者情绪的“感染力”上。
我们能记住的,大抵是作品通过渲染却最终一个个无解的结局,比如崩溃的女教师(《檀香插》)、万箭穿心的舞者(《痛点》)、颓唐离世的才子和负疚终生的导师(《车前草》)。而饶是作者语言的干净精确,多白描而少修辞上的渲染,我们也仍能在有些作品中,见到作者少见的喷薄的激情,比如《果蝠》中的蝠阵,比如《钟表匠》结局在老周面前骤然响起的钟鸣,也比如《痛点》中失去一条腿的舞者状若死不瞑目的伤痛。甚至,作者还用上了奇幻的技法、变形的处理,比如让已然灭绝的珊瑚裸尾鼠出现在甚至孩子的鼠笼里(《珊瑚裸尾鼠》),让天坑东中栖息了若干世代的果蝠忽然全部迁徙(《果蝠》),这本来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作者使用了这样的神话叙事或者说卡夫卡式的荒诞手法,让读者陷入了猜谜,但这样的处理未尝不显示了作者深味的荒诞感,从而这两篇无中生有的故事,就真的生于虚空而终于虚空了,两个作品也因此成为了两个巨大的隐喻,连同《乌鸦》这篇寓言式写作,是为集子中三个巨大的抒情整体。
从人物性格、作品主题、情节、故事结构、视角等来看,南翔的“手艺”显然都是经得起细读深究的,他的手艺已经炉火纯青,“飞花摘叶皆可伤人,草木竹石均可为剑”,无不可入小说的生活,无不可入小说的人物,读者不用担心南翔这样的作家会有讲不明白的故事、讲不出意义的内容,也不用担心会尝到一锅夹生饭或者吃到缺盐少油寡淡无味的一道菜。写什么和怎样写,在南翔这里早已不是问题,存在的问题只是你我,我们读者会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什么,感受领悟到什么,或者理解同情了什么。这样的对于主题和意义的追问和要求,其实是作者和读者的一种约定。短篇小说总体来讲,总是要言之有物的,总是要承载点什么,坚持点什么,传承并传扬点什么的。正如黎紫书所认识到的,“我写的只是一群平凡不过的人和他们凡俗不过的人生,要把这样的平凡小事写得好看,必须加入一些精神性的向度,在一群人怎样生活的表象底下,还要有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可以打动读者。”确实如此,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的奇迹,哪有那么多的故事可讲出“奇情”?尤其是如王安忆、骆以军等所说的当下经验匮乏或者说高度同质化的时代,平淡、雷同、碎片化也许才是故事或者事件的面目。
读者的主题期待或作者的主题设定,当然不是主题先行,而是一种问题导向,是作品中人物所携或所现的问题意识。主题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却也是千锤百炼的,经过经验和智识理性审视而后得的。作家看到了现象,想到了问题,敷陈了事件,连缀了细节,编织了情节,塑造了人物,结构了故事,最后小说完成,主题凸显,大概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完成创作过程。比如熟识南翔和南翔学生的朋友,可轻松在《选边》中对号入座。不过像这篇小说这样清晰的并不多,更多作品我们很难简单分析,因为作者也要考验我们的审美和价值判断能力,不会写得一马平川一览无余,作者与读者,何尝不可以是且不常常是一种猫与老鼠斗智斗勇的关系?
在这部集子的16个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三大类(知识分子、生态、历史)十小类(两性、良知、感恩、生态、历史、情感、包容、官场、家庭、情义等)的主题,也能梳理出来教师、台湾老兵、手艺人、毕业回乡的研究生、舞者、官员、单身少妇、中产白领、打工者、画家、官员、修表匠等主人公和更多职业形态生活形态的人物。就小说类型而言,有的重情节,以情节推动,如《痛点》;有的重人物,以人物推动,如《曹铁匠的小尖刀》《凡·高和他哥》;其他篇什就都是重主题,以主题推动。可见主题性创作是这部作品的一个突出特征,当然这里所说的主题性只是主要特征,并不意味着没有人物和情节的共同进入。从视角来看,取第一人称视角的有五篇,占到了集子的三分之一,其他都是第三人称全能视角或者限制视角,第一人称视角有亲历感的可信度,也容易拉进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即使第三人称视角,故事中的人物,也经常会有一位教师或者知识者身份出现的人物,隐隐然也搭载裹挟了作者的知识分子写作偏好,并巧妙利用了自己经验和知识储备的优势。最是有文化的主人公,才是作者的最爱,这样可以让自己附体于斯,感同身受,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亦中亦西、偏于书面语传统的腔调,以及学者作家的对于知识和文雅趣味的偏好,形成了南翔小说的腔调,他偶有自创文言风格的新词,也会时不时在文中引用或通过人物之口吟诵古诗词,且我行我素,不低估读者的阅读能力或者不屈服世俗的阅读惯习制约。一方面是充分简洁精确的白话,一方面是掉书袋式的知识;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底线的坚守,一方面是民间伦理的守护;一方面是一本正经悲天悯地,一方面是插科打诨不避世俗;一方面居殿堂之高,一方面行江湖之远——他是个丰富至极的人,写出了丰富至极的文,说出了他的很多时候其实是悲天悯人的语调。与此对比,邓一光的语调更忧伤,杨争光的语调更反讽,莫言的语调早期更多狂欢新近则多幽默,鲁迅自然是冷峻等等,不一而足。语调笼罩全篇就成了基调成了氛围成了全篇的情绪,使得作品产生足够强烈的情感力量。
日常生活中的深沉和爱意
□杨璐临
作为一门叙事的艺术,叙述性已成为小说公认的评判标准之一。简言之,一部小说的可读性,往往是其叙述策略的整体反映。有趣的是,在南翔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伯爵猫》里,那些所谓的叙事经验、技巧仿佛统统隐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密迩亲切,人物、情节在叙述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一笔一笔地晕染开来,直至曲终笔封之际让人抚案长叹、回味无穷。
与小说集同名的《伯爵猫》,讲述了深圳一家书店在疫情期间行将倒闭,店主娟姐姐邀请铁杆书友一起举行告别晚会的故事。小说以到店维修的电工视角展开叙事。于是,我们看到窄小局促的书店成了书友们寄托情感和记忆的“伊甸园”。在每个人充满深情的回忆和叙述中,温暖和爱意伴随着淡淡的忧伤逐渐蔓延开来。晚会结束时,“伯爵猫”三个字终于重新亮起,仿佛在提醒人们:纵然城市生活变幻无常,理想和情感的烛光却在心灵深处默默点亮,温馨而笃定。那些擦肩而过的匆匆路人,因为心灵的交流,也建立了生命的某种内在联结。小说叙事总体清丽流畅,也不乏悬念,比如门店招牌灯箱是何时修好的,娟姐姐有无恋爱对象,书店因何歇业,伯爵猫何故第一次主动飞身而下等,一连串的疑问如涟漪般弥散,成为吸引读者阅读的动力,然而小说直至结尾也未给出答案,书店倒闭成为无可逆转的事实。但这些都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娟姐姐和书店的曾经存在,以及伯爵猫在黑夜中迸发的灼亮之光,已深深刻印在读者记忆之中。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的深圳,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每天上演的深圳速度、深圳奇迹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在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革的同时,人们的生命情状也在悄然地发生改变,相比前者常为世人所觉察和标榜铭记,后者往往被淡化乃至忽视。为此,在纷繁杂芜的现实中洞悉和呈现那些被宏大的现实遮蔽淹没的声音和表情,哪怕是幽微琐碎的存在和变化,已然是现代小说家创作职责的一部分。在深圳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南翔,做过记者、教师,进过工厂、干过企业,此前还在宜春当过铁路工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早早地目睹人生百态,更对现代化进程中人们面临的精神压力和困境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悟,其小说创作也往往以城市生活为据点,通过现代人的婚姻、家庭、职场、情感等侧面,展开精神维度的审视与思考。
《伯爵猫》借一个书店的倒闭指向城市人普遍的人文理想和精神危机;《乘三号线往返的少妇》通过少妇在高铁上的一段“艳遇”,揭示单亲妈妈的艰辛孤寂以及对被爱和肯定的渴望;《钟表匠》以一对老男人之间的友谊影射老年人的孤单落寞和对温情的向往;《玄凤》通过一对已婚夫妻领养鹦鹉的经历,展现“丁克”一族生育观念的转变等。值得注意的是,小说虽然展示了一定精神向度并牵涉一些社会问题,但绝不同于以暴露和批判为目的的“问题小说”,对此,南翔曾表示,“小说的价值标高,应该牢牢订立在普世的文化尺度上,这样既可避免重蹈文学史上随风转向、紧跟任务、图解政治的覆辙,亦可避免‘问题小说’之弊,随着问题的结束或飘移,一些问题小说便索然瓦解,徒具标识意义而尽失文学审美价值。”可见,对于小说的思想立意,南翔有着清晰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而惯常的文化尺度则是其一贯的价值追求和风格呈现。
关于这种文化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渊源有自,如孟子的“仁者爱人”、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等。作为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长期从事高校教育工作的南翔,一方面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浸染下,这种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与学院派的专家不同,不到17岁的南翔便在南昌铁路局宜春火车站机务段当装卸工,并度过7年的艰辛岁月,生活的磨砺孕育了他仁爱朴实的人生观,也造就了他“我的亲历,然后文学”的创作观。如早期的《绿皮车》《老桂家的鱼》即通过对底层生活的关注书写,展现对底层命运的悯恤和关怀。小说集《伯爵猫》无疑延续并强化了仁爱的思想。如《凡·高和他哥》中桂教授对底层青年画家向南和向北两兄弟无私的帮助提携、《乌鸦》中素不相识的监狱看守对男孩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等,无不闪耀着人性良善的光芒。即便是《疑心》中锱铢必较的大姨,《伯爵猫》里不修边幅的电工,也有内心温热良善的一面。更毋庸说《曹铁匠的小尖刀》父亲对儿子深深的爱与思念,《钟表匠》两个老男人催人泪下的友谊。由此,在爱与善的守望和呼唤下,每一个看似绝缘孤立的个体被重新联结并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小说也因此在精神的勘探之余洋溢着融融的爱意和温情。正如《凡·高和他哥》里桂老师所言,“一个带着很深感情而非冷冰冰的浮艳的城市之夜”,这是他对底层青年画家向南作品的赞誉和鼓励,也不啻为南翔对这座城市的深情解读。
时代在变迁,人文在延续,这些变迁、延续的背后是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更是纵横捭阖、丰盈辽阔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它们是人类社会得以瓜瓞绵绵的基础,更是人类文明成就辉煌史诗的重要依托。此前,南翔曾用“三个打通”概括自己的文学创作:历史与现实打通,虚构与非虚构打通,自己的经历与父兄辈的经历打通。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南翔的小说就是在阅读时代,阅读生活,阅读我们自己。这或许就是个体对于时代、民族的意义,也是南翔小说的独特魅力和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