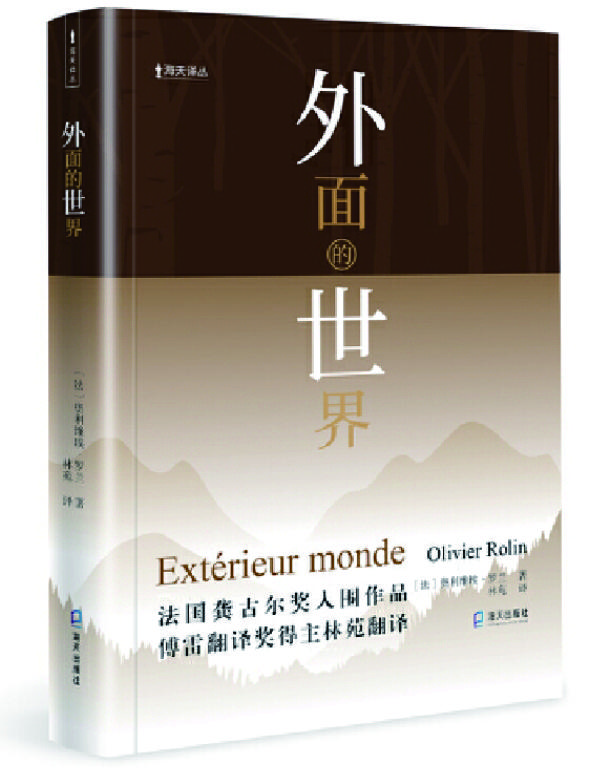5月的北京,东郊森林公园中,白杨参天,野花乱放。二月蓝、尖裂假还阳参、泥胡菜、夏至草等,各以其色香入眼,沁鼻,消魂。坐在日式风格的木凉亭下,沐浴着初夏的风,哪儿也不想去,什么也不想干,任自己迷失在树荫花海中,转眼就到了饭点。忽然很想吃比萨,半小时后热乎乎的外卖就送到了公园门口。
大快朵颐之际,我想到多年前读过的一个传说,说是比萨饼其实并非意大利原产,而是西域一带的馕饼之类,是马可·波罗通过丝绸之路把这种制饼技术带到威尼斯的。不过他忘了中国人是怎么把馅放进饼里去的,只能胡乱操作一番,让原本内卷的肉馅躺平在外了。这个传说是否可信,当然无法考证。但《马可·波罗游记》我是读过的,书中并没有写到西域馕饼,倒是记述了元朝中国许多地方的风俗和景物。全书充满了一个西方人对东方的赞叹、艳羡和崇拜。历史学家史景迁说,马可·波罗的书既可视为对中国生活的细微描述,也可当作对自己城市的批判,他以中国为道德典范,对比威尼斯人放荡的性生活。不过,他强调指出,马可·波罗留给后世的,除了他所提供的资料外,最主要的还是他所激发的好奇心。
看看外面的世界,满足不倦的好奇心,是人之为人的最深层的冲动。根据进化论的描述,我们的远古祖先走出非洲丛林,进化到目前这种状态,有两个关键的要素起了作用,一是好奇心,二是杂食性,什么都想看一看,听一听,嗅一嗅,摸一摸,最后,放进嘴巴尝一尝。于是,感官和智力都得到了满足,精神视野也随之扩张和提升。这种冲动用学术话语来概括,或可称之为,从现实世界到可能世界的空间移动。这是我在拙著《旅行文学十讲》中给旅行下的一个工作性定义。生活中,人经常徘徊在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借用英国诗人布莱克著名的诗性隐喻,我们的身体类似向日葵的枝杆,不得不扎根于混浊的大地上;灵魂却像它的圆盘般每天随着太阳的脚步转动,向往着不可企及的光明之境。但人比植物有利的一点是,他有思想和腿脚,只要愿意,随时可以将向往变成行动,从其栖居的空间挪移(哪怕是暂时的)到另一个可能的空间中。大到一方流着奶与蜜的乐土,小到一幢爬满常青藤的乡村别墅;或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大洋外一个陌生的国度、星光下一片宁静的海滩等。
离开现实世界,踏上通往可能世界之途,全方位、全身心地感知外面的世界,当然是最理想和开心不过的。但通过阅读优秀的旅行文学作品,“卧游”或“神游”其间,也不失为一条替代途径,有时还可能比具身感知来得更深刻。这是因为,一名优秀的旅行文学作家往往具有一颗喜欢探索的大脑,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哲学,以及将这种哲学付之实践的勇气。一部理想的旅行文学作品,总会给读者提供三个探索的机会,并带他同时进入三个世界:外部世界、作者的内心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
随意翻开刚到手的一本新书,扉页中的引文就吸引了我:“一个男人决意要描绘世界。一年年过去,他画出了省区、王国、山川、海湾、舰船、屋舍、器具、马匹和人。临死之前,他发现这座耐心绘成的迷宫之线条勾勒出的竟是他自己的脸。”这段文字的原创者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被当代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转引在了他新近出版的、龚古尔奖入围作品《外面的世界》中。初读之下,很难给此书归类,因为它既不像小说,又不像回忆录。把它归入游记类,可本书又不提供旅游攻略,告诉读者自驾路线和必游景点等可操作的具体细节。整本书读下来就像一场真正的漫游那样,散漫、杂乱,无头绪。似乎有目的地,但又随遇而安;经常迷路,但总会找到方向。一个个港口,一次次起程,纷至沓来的印象,不期而至的偶遇,一个个闪现的姣好面容,有些是真正有过交往的,有些则纯粹是作家的想象。整本书像万花筒般转动,让人目不暇接,又频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之感。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去过的地方你去不了,他见过的人你见不到。”
因为罗兰带我们去的地方,大多在“世界尽头”,是被人遗忘、忽略,甚至无视的角落。它们要么当下正处于战乱中,要么一直处在贫困、饥饿和绝望中。在他看来,只有“在那种环境中,人会注意到更多事情。那种环境中,也的确会发生更多事情,遇到更古怪、更加远离我们所认定的人类生活的人”。
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所认定的人类生活”?以谁(个人、地方或族群)为标准?读到这里,不禁想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本人的研究生毕业旅行,或多或少受到摇滚音乐人崔健的影响。当时,我们7个一无所有的“假行僧”,合用一个每次只能拍摄36张胶片的傻瓜机,乘绿皮火车,一路向西南,且行且玩耍,目的地是当时刚刚开发的九寨沟。在成都公交站购票时,遇见一个瑞典人挤在窗口排队。大家不禁好奇地围上去,问他来中国干吗?他说是来录鸟类的声音的,刚从峨眉山风景区下来,听说九寨沟鸟类很多,就过来了。说着,他从身上背的超大行李包中摸出一本鸟类图谱、一台录音机。一面翻书,一面让我们听各种鸟的啾鸣声。更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他并不是鸟类专家,也没有正式工作,打零工赚够了钱,就满世界云游,录鸟的声音,然后筹划下一次出行。当时,自以为我们的穷游已够潇洒了,却没想到人还可以这样生活。
不过,如按罗兰的标准,这位瑞典人还不一定入得了《外面的世界》。本书中写到的地方和人物,大都处在超出常人想象力的、更极端的生存境遇中。比如,作者在喀布尔老城区的废墟里拜访了一帮武装兄弟,其中有个不小心踩了反步兵地雷的无腿人,正在画一幅先知的彩画,并为其外孙的命运而悲伤。在俄罗斯里加的绿皮火车上,他偶遇两个可爱的粗人,他们都在阿富汗当过兵,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像鸡妈妈对小鸡那样,对他这个陌生人呵护有加。在皮库岛上,他透过黑沙滩的巨浪,听一位捕鲸手讲述惊心动魄的捕鲸故事,感觉自己“似乎穿越到了创世之初”。
罗兰写道:“说到底,之所以去喀布尔、贝鲁特或萨拉热窝……是因为我们对世界好奇,而且世界也就是这个样子,充满那么多远离我们的喧哗与骚动。然后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不再满足于在广播里听到,我们想去那里,去远方,看看这片巨大的嘈杂到底是什么样的。看,学着去看,是作家这一职业的基本功。”每次出行和重返,冒险采访或冷眼旁观,他都见证了生存的各种可能性及人性的丰富多样性,豪宅和废墟、伟大和卑微、野蛮和仁慈、温柔和残忍、荣耀和耻辱……而所有这一切,也是他的自我镜像的映射、反射和折射,令他产生共情感和悲悯心。因为他是人类的一分子,正像我们一样。想起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写下的名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
《外面的世界》中,最打动我的是书中一位小人物说的一句不起眼的话“那时我们还能旅行”,其中隐含着多少惆怅、遗憾和期盼。自2011年起,国家旅游总局将每年的5月1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这是为纪念徐霞客,这位世界级的徒步旅行家和行走文学的先驱而设立的。1613年5月19日(明万历四十一年三月三十日)他首次出游,写下了《游天台山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步履遍及中原、华东、中南、西南等地。要不是洪武四年(1371)始实行海禁政策,说不定他早已踏出国门环球旅游,或许会留下一部《阿尔卑斯山日记》之类的作品呢!今年的“中国旅游日”刚刚过去,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能除下口罩,走出家门,再做一回“假行僧”,用自己的脚步,丈量一下外面世界的深度和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