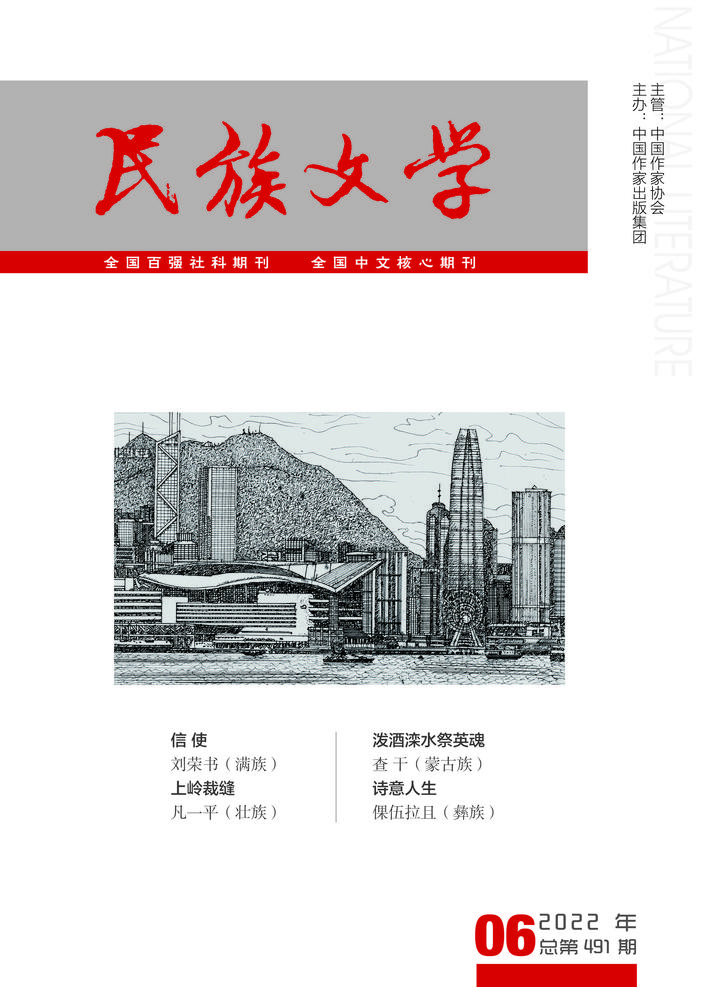关于小说《信使》(刊发于《民族文学》2022年6期),作者刘荣书说,他想将一个破案故事中的戏剧性和悬疑感写得好看、好读,更想在这个过程里探讨和呈现自己对于罪恶、爱和救赎的思考。
《信使》显然是一部颇具可读性的案情小说。是的,阅读它的过程中,我始终提着一口气。小说开始于退休刑警曹河运对一桩命案的回忆,整部作品开篇第一句便是“故事开始的时间是1986年”。穿越岁月的一桩旧案,因为当年的办案刑警曹河运和死者遗属——其孤女江一妍——内心深处始终不曾释怀的执念,并在一系列偶然和必然的驱使下逐渐拨开迷雾、距真相越来越近。“翻案”的过程,在作者节奏舒缓、绵密的娓娓道来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平静水面之下的汹涌与沸腾,我们知道一定会有一个出乎意料的谜底在等待读者,但《信使》叙述节奏所营造出来的悬置感以及不落俗套的情节设置,又让人实在猜不出那个最关键的“包袱”会在哪一刻突然抖落。刑警曹河运多年以来的念念不忘和惴惴不安,身边不断增加着新内容的案情笔记本,江一妍恍如隔世的童年记忆和谜团重重的当下生活,二人多年后再次相见的相互敞开心扉,以及他人讲述中另一个涉案人陆小斌的前世今生与心路历程……这些情节中或隐或显地透露出来的点到为止半遮面的案情线索,刺激着读者的戏剧与悬念期待,即便我们知道谜底早晚会揭晓,但又实在猜不透会在哪一刻揭晓,始终提心吊胆地提着一口气在等待。作为案情小说,《信使》情节跌宕起伏的同时在常识和现实逻辑上并无明显的硬伤,这并不容易,传奇性、戏剧感与符合逻辑性在写作实践中往往容易顾此失彼,而这恰又关乎小说叙事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可以说,《信使》在故事层面,是一部叙事扎实且现实感与戏剧性、可信度与可读性平衡得恰到好处的案情小说。
然而我们对一部小说的期待,也许不仅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和阅读过程中的“爽”之所在。案情小说一直是类型化写作中非常主流和畅销的门类,“纯文学”写作中也不断出现相关题材的佳作,比如近年来广受好评的《平原上的摩西》(双雪涛)、《借命而生》(石一枫)、《太阳黑子》(须一瓜)等。一部以刑案为基本题材的小说,它的阅读吸引力和文本魅力究竟在哪里?文学意义上的独特审美价值又是什么?除了前面谈到的戏剧性、悬念感所带来的阅读快感,案情小说更大的魅力和文学价值大概源自其间穷形尽相的人情和人性,一种极端情境下人情的闪耀或黯淡,以及人性中善与恶的集中交汇和交锋。在每一桩罪案背后,围绕它的种种遮蔽和探究过程,人性中那些复杂微妙的因素更容易彻底显形和淋漓抖落,而这正是文学最关注、最擅长表现的东西。
作为读者,我在阅读过程中始终提着的那口气,不仅来自情节的跌宕和波折,更源自小说字里行间弥漫着的一种无形却又分明令人感觉拥塞、庞大的东西。当小说的主人公们多年后试图再次回到历史现场去重新探求谜底,翻查旧案,不仅仅是尘封多年的被遮盖的真相大白于世的过程,还是涉案诸人与外部力量抗拒挣扎、与自我内心缠绕搏斗的艰难过程,更是被遮掩的正向人性不断复苏的过程。当年主理命案的曹河运,在“成功”结案后顺利受奖升职,但他始终“心里有鬼”,结案后仍未解开的诸多疑点在随后的很多年里一直成为其竭力逃避又无法释怀的内心折磨和等待。命案受害夫妇留下的孤女江一妍,虽刻意选择了背井离乡的屏蔽和遗忘,“她愿意做一个没有来路的人,自此改头换面”,但年少时的记忆仍然坚固地存留在她的内心深处,甚至会突然以某种方式倾泻和爆发,严重干扰着正常的人生节奏和状态。少年时无意中充当了信使的陆小斌,怀揣着双重秘密,在赎罪和爱慕的复杂心理驱使下用假冒身份以非正常的方式走进江一妍的生活,却始终不能真正舒展自己正常的情感和世俗人生。小说中陆小斌跪在江一妍床头深情注视她的“令人动容、却又不乏诡异”的画面细节,就是他“像忏悔,还是爱得不知所措”的内心写照。而涉案的其他人,陆家良、谢战樱、赵局长等等,小说关于他们的笔墨较少,但不多的情节中亦在表现这些人多年来内心或多或少的不安甚至罪恶感。一桩尘封多年的旧案,之所以能重新回到视野中来,始于江一妍最终想要与现实生活和真实过往的和解,更是曹河运、陆家父子多年来或等待或逃避的对真相的真正了解。人们曾经的爱与罪以及救赎的可能,此时此刻汇集在这桩陈年旧案的重新侦查和审判中,来自现实和法律层面的审判和拯救,更是灵魂和内心的审判和拯救——小说的人物塑造和主题呈现,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
小说名为《信使》,“多么雅致而富有神圣感的名字”。而“信使”在这部小说中有时是邮递员带来的一封信,有时是自己亲手送出的一张字条,有时是神秘的突然来信和汇款,又或许还可能是一个身份、一种使命。在整个故事中“信使”扮演着颇为复杂的角色,对曹河运来说,他这辈子的好运气都是邮递员带来的;对江一妍来说,曹警官曾是一名专门向她递送亲情的信使,而另一封不明来路的信函成为自己绝望中阻止自杀念头的幸运之神;而对陆小斌来说,他曾经在完全不知情中去送达“将要降临的厄运”,又带着爱和罪的双重重负一次次送出救赎自己和江一妍的希望和可能。又或者,在这些具象的“信使”之外,它还隐喻着生命和人生当中无法预期和阻挡的到达,命运的到达,带着或强烈或微弱的希望,或温煦或冷冽的气息。如同小说中江一妍哲学意义上的领悟:“在她成长经历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就是被信函,以及类似信函的东西所左右的。”
多年前偶然在《人民文学》读到刘荣书的一个短篇《浮屠》,以及后来在《十月》遇到的中篇《珠玉记》,两篇小说读来皆是惊艳,由此形成了我对刘荣书小说创作的基本好感。虽同在河北,然而我和他并不算熟悉,一起参加过多个文学会议,交流基本也就限于每次见面时的寒暄和席间的碰杯。在我印象中,刘荣书的面相和性格皆是典型北方汉子的豪爽、质朴甚至有点北方的粗粝。但读他的小说,那种叙事语言的诗意和优美、叙事节奏的缓慢与舒展,那种对“北方”精细却又全不做作的雕琢,又让我猜想他应该是热爱南方的,或许还曾迷恋过苏童与余华的小说。一直认为刘荣书是一个在当下被低估的小说家,或者说,他是一个足够成熟同时又颇具潜力的小说家,其新作《信使》再次展现出来的讲故事的功力和对人性描摹探究的能力,令人对他以后的小说创作更怀阅读的渴望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