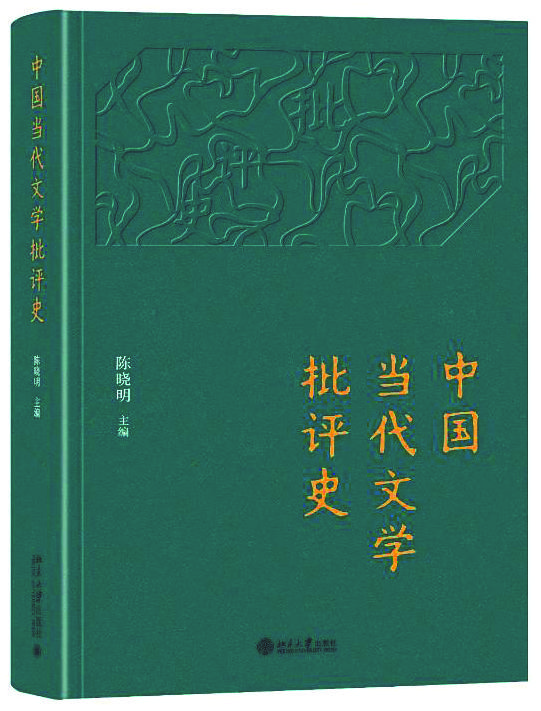在2022年第7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发表了《漫长的20世纪与重写乡村中国——试论〈平凡的世界〉中的个体精神》一文,文章谈到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肯定性的个体精神等问题,对当下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富有启发意义。本报记者日前对陈晓明教授进行专访,邀请他分享了关于路遥创作以及新时代乡村题材写作的见解。
记 者: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从农村走向城市的知识人与农村的关系,都是《平凡的世界》要处理的重要课题,也是它在广大读者中受到欢迎的原因。今天仍有大批的农村学子进入城市受教育、找工作,在经受磨砺之后,其中也诞生了一大批有理想的年轻人。您觉得今天的“孙少平、孙少安”们应该是怎样的青年形象?近几年读到的乡村题材文学创作中,您看到了哪些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向?
陈晓明:这个问题看似是一个学理的问题,但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实很复杂,也很尖锐。我们还是谈谈文学,湖北作家刘醒龙当年就是新乡土文学的一个代表。乡村的脱贫致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要体现在乡村的文化和教育上。刘醒龙1992年写的《凤凰琴》中的主人公张英才在界岭小学当代课教师,很有意思的是,孙少平也当过小学代课教师,后来职位被人挤掉了,只好出去打工。《凤凰琴》里的小学教师可以看作是另一个孙少平,但刘醒龙不像路遥写得那么高亢,路遥的笔端呈现的是1980年代特有的激情,到了1990年代涌现了很多更加现实的问题,作家的态度也更为冷静客观。刘醒龙把他的笔握得更紧,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孙少平之后一代农村青年张英才们的苦涩,他们在乡村的土地上,一点一滴地用自己的坚韧、宽容和坚守,体现出了乡村的精神,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其实乡村的文化教育,在九十年代的小说中的确有很多表现,刘醒龙的《凤凰琴》非常突出地反映了乡村教师的困难,它的感人之处也在于写出了他们的精神和坚守。孙少平到城里是寻找个人发展机会,如果留在村子里当教师,可能就是《凤凰琴》的故事。
1996年,刘醒龙又写了《分享艰难》。假如孙少安再继续干下去,没准会成为一个乡干部,那就是《分享艰难》里孔太平的故事。《分享艰难》反映了九十年代中国乡土文学的另一个特点,那时经常把乡镇干部描写成为富不仁、霸道的形象。九十年代的乡村干部中,霸道的有没有?有,否则干不成事。坏人有没有?有,但是绝大多数还是实实在在干事的。基层工作非常困难,做起来也没有钱。贾平凹写《带灯》是源于回到老家看到了乡村中国的凋零,可以说是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做了一次对话。这部小说中,农村已经没有年轻人了,年轻人必须进城,必须走孙少平的道路。路遥是先知先觉,不管如何,孙少平必须走出去,因为中国的土地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人耕种。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说,至少有2.45亿的农村青壮年要离开土地,到城里去打工。于是在九十年代,进城找活干的农民工如潮水一般地涌向城市,他们也真的受尽了辛苦。
《秦腔》是贾平凹切实回到土地上的长篇小说,他直接关切“三农”问题。一方面他描写了乡村生活的素朴琐碎,乡村的物的世界被表现得十分充分,体现出乡村的荒蛮景象,也写出了乡土中国的新情况。应该注意,《秦腔》中写到了土地上新一代领头人夏君亭这个人物。他和梁生宝那一代领头者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时代语境也不大一样。夏天义当过村支书,很有权威,老百姓开始都跟着他,但是他的那样一套方法渐渐不行了。夏天仁的儿子夏君亭对他的管理方法进行了改革,改成了适宜的管理方法。这是摆在乡村干部面前的问题:孙少安如果成为干部,不管如何正直也好,首先得解决问题。所以贾平凹是了解农村的,他写得很真实,夏君亭本质上是一个好人,但是为了搞活经济,歪门邪道的事情也做了不少。
讲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当代表现得比较全面和有力的还有关仁山,他的《天高地厚》《麦河》《日头》被陈思和教授称为“中国农民命运三部曲”。其实可以看到,路遥很会写,在《平凡的世界》里面,他让孙少平即使离开了农村的土地,却始终离不开苦难,然而又有一种精神在支撑着他在城市打拼。但是在九十年代,中国还是面对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农民怎么去对待土地的问题?《平凡的世界》写了农民得到土地的欢欣,但是他们又要面对土地流转的问题,就是农村的青壮劳力要离开土地,参与城市化建设、城镇化建设,传统农业经济也转而采取企业化经营的方式,这是必然的道路。关仁山的作品就表现了土地流转之后,农民与土地更复杂的关系。关仁山的小说是有厚度、有深度的,它秉承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精神。燕赵和齐鲁之地的文学始终有理想主义的亮色,像当年的《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都有这样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关仁山秉持的就是这样一个传统,他的作品写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新出现的问题,写出了新的领头人形象。
记 者:您认为路遥作品主人公身上具有特殊的个体精神,他们直面苦难,并通过“坚韧”和“爱情”克服苦难,获得精神上的肯定性力量。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很多失败青年的形象,这是否意味着路遥书中所讲述的克服苦难的方式面临着一定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令人信服地写出这个时代的肯定性精神力量,特别是关于青年形象的塑造?
陈晓明:九十年代,有一段时间,其实国家上上下下都很困难,国企改制、国企职工下岗,教育也很困难。那个时候有个段子,说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某某研究院的。常常是做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有些大学教授不得不在学校里卖馅饼。但是我们挺过来了,人民挺过来了,其实大家都在默默地奋斗,在吃苦耐劳奔小康。很多做生意的是屡败屡战,10个改革家有9个破产甚至锒铛入狱,可以说改革开放,人民是付出了代价的。肯定性的形象不容易塑造,其中需要进行文学的虚构和夸张。没有夸张,哪有文学?小说就是虚构,没有虚构就无法敞开,无法创造另一种生活。菲茨杰拉德说过,如果不是那种让你撕心裂肺的东西,你写它干什么?现实主义文学有传统,现代主义也有传统,社会主义文学要塑造令人信服的肯定性形象,要积极的、正面的力量,首先要有文学感染力,要令人信服,这个是最难的。
我觉得处理得比较成功的还是贾平凹。比如在《带灯》中,主人公“带灯”一边为农村脱贫工作解决难题,一边又体现出传统乡村生活中的人情世故。小说写“带灯”到黑鹰窝村去看望卧病在床的范库荣,情景十分凄凉,五六十岁的农妇范库荣在土炕上躺着,“一蓬花白头发,像是一窝茅草”。范库荣的小叔子陪着“带灯”来看她。“带灯”平素与她十分亲近,待到这时要叫她时,范库荣只是睁了一下眼,再也没了任何反应。“带灯”看着她的老伙计凄凉,交给范库荣的小叔子1500元的救济款,并嘱咐,这些钱只能给范库荣买些麻纸等倒头了烧。这显然是不露声色的反讽笔法,农村人哪能拿这么多钱去烧麻纸,小叔子是明白人,对带灯说:“这钱一个子儿我都不敢动地给侄儿的。”贾平凹这段写得多精彩,他把农民的贫困,“带灯”对老大姐的关心和细心,乡村人伦中的道义、道德,乡村的文化风情都写了出来。好的小说就是这么结实。小说是什么?纳博科夫说,除了光彩照人的生活,小说什么都不是。这样的生活虽然贫困而绝望,但作为文学来说,它却光彩照人,令读者感到信服。“带灯”的形象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并不是说写理想化、肯定性的人物就会让小说显得夸张、虚假,关键是作者能不能扎在厚实的生活根基上,写出人物身上的理想性和肯定性,让我们作为读者能够慢慢地被这样一个形象所打动,这才是文学的真实力量。
记 者:您在《漫长的20世纪与重写乡村中国》一文中指出,《平凡的世界》“去除掉1980年代热衷的艺术探索,而专注于写乡村青年的个人觉醒、追求和命运,这就直接切合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21世纪初的基层民众尤其是青年读者群的需要”。这句话实际上指出了文学创作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呼应关系。人们对当下文学的期待之一,是能够更好地展现时代的总体性。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总体性是什么?当下文学如何展现这种总体性?
陈晓明:我们常常如此表述:在融媒体的时代,在移动终端的时代,在视听文化的时代,怎么会有总体性?在社会分层、阶层分离得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一种总体性。但是我觉得,无论对哪一个时代、哪一个社会,我们都可以用相对整体的眼光去看待。今天社会的总体性是什么?我觉得是它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矛盾性。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社会的真实性才能有比较全面的理解,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把握才能更加准确和客观。我们要看到这样一种互文性的关系,确实社会有分层化的趋势,但我们应当找到它们相互连接的方式,而不是对立的方式。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分离中的统一,文学才会更加有效地去表现对话的可能性。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有很大的城乡差距,有人要还房贷,有人要租房,有人要看病,有人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上学问题,我们要看到这种复杂性,才能够去理解今天中国的总体性是什么。
记 者:您在文中谈到:“路遥并不是要写超出环境和人群的个人主义,更不是那种超人的无根的个体,少安、少平来自乡村,始终在乡村的艰苦生活中经受磨砺。正是生活的点点滴滴,人情的冷暖,使得个体的生命那么饱满充实。这使他们的选择始终是‘现实主义式’的选择,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承担家庭责任。既摆脱命运的束缚,又有勇气承担责任。”我觉得这其实也表达了路遥写作的挑战性,他挑战了之前的集体主义的写作,而是把人物放在宏阔的时代环境中,看他是如何面对生活、改变生活和命运,并通过这些个人争取美好生活的挣扎、努力,来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整体特征。这其实是表现出了一名作家的勇气,他并没有遵循旧的写作传统,写出了普通人在拼搏中的激情,也写出了他们的孤独。这种激情与孤独、苦难与爱是否仍是今日现实主义和乡土题材创作应当重视的方面?
陈晓明:路遥的方式是非常个人的,非常有个性的。今天的乡土题材的创作应该多种多样,并不仅仅是路遥那样的方式。今天乡土文学叙事可以有像关仁山后来的那种既豪放又神秘的,也有像阎连科的那种偏执、强硬的表达,也可以像贾平凹那样越来越土气、越来越老气,但是确实越来越放任和有力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贾平凹的风格是越写越土、越写越狠。《秦腔》和《废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贾平凹自己放弃了《废都》的那一路唯美、空灵、飘逸的笔法,到了《秦腔》则完全是贴着生活、贴着土地在写。后来读了他的《古炉》,我觉得贾平凹又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莫言的小说中,那种大起大落是挥洒自如的,但《晚熟的人》就写得非常的朴实、简洁,其中写得最好的我认为是《左镰》,也有向鲁迅致敬之意。付秀莹的小说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她的《陌上》和最近的《野望》,把乡村生活写得非常绵密、细腻,有自己独到的想法。邵丽的《金枝》不一定要看成乡土文学作品,但是也写到了乡村。邵丽写了很多乡村的干部的生活情况,她是另外一种笔法。今天确实很少有作家像路遥那样,以一种孤独和激情来展开叙事,今天的作家都把自我压得比较低,把情感压得比较低,比较客观和本分,比较追求本色的写作模式。路遥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为自己立下了一座丰碑,也给这种文学立了一座丰碑。这丰碑是一座纪念碑,它意味着一种终结,它是不能够被复制和重复的。
记 者:您提到只有全面地理解“漫长的20世纪”,我们才能理解并写好21世纪。从乡村中国到城乡中国,城乡之间更加杂糅。全面小康、乡村振兴、城市生活导致我们在把握城乡关系时更加觉得很有难度。如何在“漫长的20世纪”的视野下观照和书写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与城乡互动?
陈晓明:路遥也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他那个时代总是要反观前面,比如说他读柳青读了七遍,读《红楼梦》读了七遍,其实不仅如此,他还读巴尔扎克,读《红与黑》等等。今天的作家怎么理解历史的总体性?我觉得还是要放在20世纪中去理解。我们今天要涉及的很多经验还是受20世纪的影响和支配,对于乡村社会来说,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去评价它,去揭示它,我觉得这样的视野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记 者: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通过史的梳理,您觉得当下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或者可能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在借鉴中西方文论资源的基础上,如何建构契合中国社会现实、文学实践的评论话语?
陈晓明:我在导言里面谈到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其实这本书贯穿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批评的架构。我想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五四运动以浪漫主义开始?郭沫若的《女神》、鲁迅《摩罗诗力说》也好,包括茅盾的作品在内,都有浓厚的浪漫气质。茅盾自己说,浪漫主义这个东西并不是不好,但对我们还太高级、太先进了。就像当时我们说后现代主义一样,跑得太远了,和中国的实际不符合。五四运动对传统是反抗和批判的态度,因为它要革新、要现代,所以它矫枉过正。对传统的转变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张炜的《古船》应该是那个时候最早触及到传统的作品之一,但隋抱朴一直在读的是《共产党宣言》而不是读古书。贾平凹的《废都》也想走传统美学的道路,但庄之蝶还是疯疯癫癫、装疯卖傻的。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嘉轩用乡约乡规来规训村里的人,乡村的文化大量地浮现出来。白嘉轩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代表,他的正面形象第一次被确立下来,所以《白鹿原》在当代文学中真正确立起传统文化的地位。
我觉得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在文化创造方面都要进行传统、外来、当代性三元的有机结合。没有传统,文化自身的特点和力量就不厚重;没有外来就没有挑战和刺激。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创新的认识也有很多的争论,像费正清认为是西方的挑战刺激了中国,才让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但年轻一代的汉学家,比如柯文就认为是中国自身就有变革的要求。中国过去的变革方法是借着复活传统来重整当下。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桐城派”虽然倡导古文,但胡适却从“桐城派”那里读到了现代白话文的滥觞。所以,我们要向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学习。如果说我们彻底杜绝外来的文化,只看祖宗的传统,充其量只是继承,而缺少了文化自我更新的强大的渴望和批判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特点,第一是博大精深,第二是批判精神,第三是永远的革新精神。《漫长的20世纪》一书的作者乔万尼·阿里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人,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罗代尔的历史理论进行了对话,但他的理论核心还是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的理论批评越来越拘谨,格局越来越小,气量越来越小,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所以我们要创造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情,恰恰就是需要一种向世界优秀文化敞开大门的胸怀。
记 者:文化的对话性是您今天讲的很多问题的一个关键词,无论是从1980年代以来的具体的文学形象之间的对话,还是不同时代与社会总体之间的对话,包括批评与理论、传统与外来,我们都要建立一种开放、多元的对话关系。
陈晓明:非常对,问题就在于对话性。我的导师钱中文先生今年已经90岁了,他就提出了对文学理论建设中的对话关系的关注,我非常认同。别看贾平凹受传统的影响很深,他也读现代小说,他的书房里有很多外国翻译的小说和理论。莫言受外来的影响就非常丰富,张炜受苏俄的影响,李洱读古书、读野史,麦家的作品里面可以看到史蒂芬·金的影子。刘震云后来的小说越来越像《水浒传》,但一开始是契诃夫的小说对他有很深的影响。他写的《故乡面和花朵》,多么后现代,应该说对后现代小说是骨子里吃透了,这样的作品是为未来50年写的。恰恰是因为具有多元性,能把外国文学的影响和中国本土的文化结合得很好,他们才会成为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