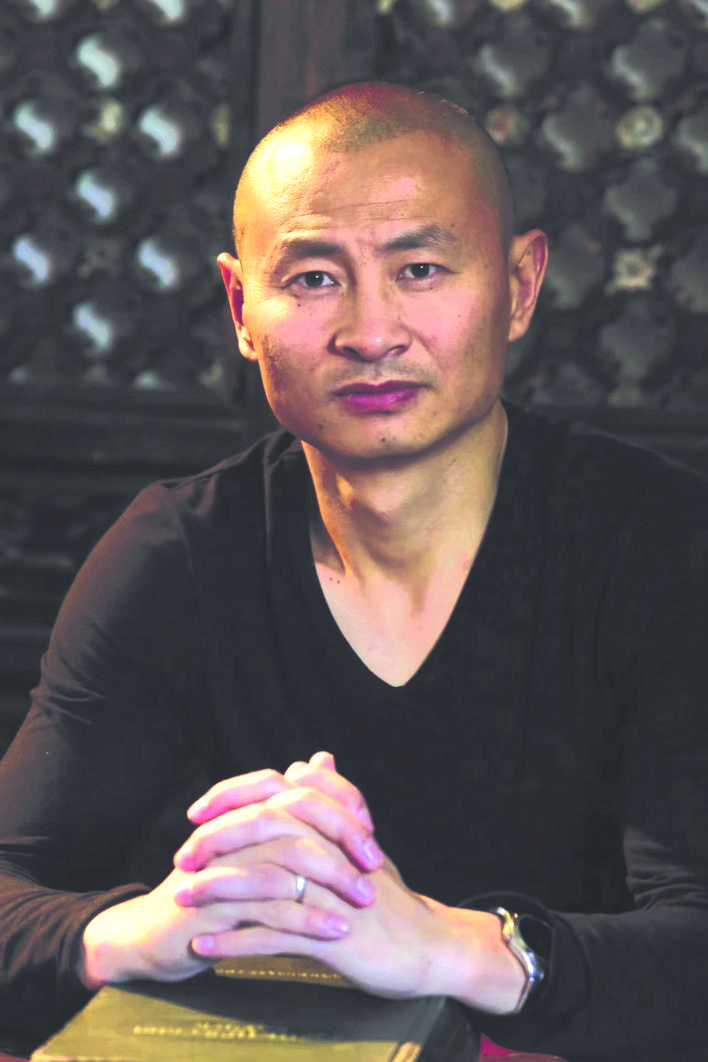十年,一眨眼的工夫。巧了,今年也是我鲁院高研班毕业十周年,我们正琢磨着如何攒一个十周年聚会,主题之一,正是“写作十年”。
一生能有几个十年?更不用说,一个作家,能写几个十年?
十年前之于我,是一个分水岭。是年我从鲁院返回新华社云南分社办公室呆坐,望着巨大魔幻的白云在蓝天上飘荡,遥想在鲁院的种种细节,猛然意识到,年逾三五直坠中年的我不该再吃新闻这碗饭了。我是多么感激新闻给我饭吃给我衣穿哪,但我深知这位衣食父母终究不是血缘上的亲爹妈,我得走,得去找找他们,哪怕带着无限愧疚和自责。谁是我血缘上的至亲?文学。当然是文学。我知道我打小就有志于此,纯粹的鲁院时光让其发酵壮大,终于不可阻挡。是啊,再不试一把,下半辈子都未必原谅自己。机会来了,2014年3月我去了《大家》,算是正式扎进“文学”,及至2016年5月创办大益文学院,我已经无法“回头是岸”了。我知道我的余生都属于文学,我知道上帝在制造每颗棋子的时候就划定了界限,或迟或早,我们都将鬼使神差地成为我们渴望成为的那一个,无论成败。
用成败衡量文学似乎俗气。是啊,多俗啊,文学确乎是有标准的,只要投入、专注,总能写出还交代得过去的小说,就无所谓“成败”。所谓“尽人事听天命”,或“爱我所爱,不计其余”,剩下的就是爱得够不够、深不深的问题了。但爱的程度深度往往很难摆脱文学的功利一面,非圈子内朋友不足以感受之。如发表、奖项、奖金、头衔、职称种种,让人精疲力竭,它们会在相当程度上衡量与影响你的成败。除非扔掉?还真没法扔掉,它们会成为你进入文学的一部分,是你从事文学的周期性指标或边际效益,永续存在,没完没了。
可以不搭理吗?
也无不可,有志气的写作者埋头写作就是。十年来我试着勤奋再勤奋,尽可能以手艺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尽量多写、多改。十年来的持之以恒还算顺利,大小刊物每年陆续有长中短篇发出来。写作似乎变成一种证明自我存在的东西,似乎唯有不停地写下去,才是自我完成的必然。我急于肯定什么,又急于否定什么,也许每个作家都有相似经历,以不间断的写作证明自己,又往往对这种“证明”缺乏判断。而专业评价、自我满足、读者眼光是让你纠结痛苦的三座大山,是你前行途中的拦路虎,凡有点野心的作者总想各方兼顾又难免顾此失彼,于是来回拉扯煎熬。问题慢慢来了,累,很累,你总想预设什么东西,总想写点出众又安全的东西。差不多写到第四个年头我才恍然明白,写作何必那么复杂,满足自己才是第一要义啊,否则安全又出众岂不就是平庸?这不是卡夫卡的启发,是来自伯恩哈德那个愤怒的老家伙,他说写作就是与一切为敌,一个精神都没发育好的巨婴怎么可能写出好作品?发现伯恩哈德于我就像发现美洲大陆,我突然在2017年前后自信起来了,更愿意写我想写的小说了——足球的故事,足球的经验,这才是我的地盘,是我的小说。反正会踢球的写不过我,会写作的又踢不过我。那些年我洋洋得意地写了一批足球小说,尽可能用极简的硬汉方式来处理这个变化诡谲的世界,尽可能用经验和想象力驾驭人性和足球。但两三年之后,问题又来了:还傻不拉叽写足球?还有更多可写的吗?你在重复自己,口袋里还有几把刷子?
还得变。
对小人物的关注、对城市生活的关注、对情感状态的关注,渐渐成为我的重心所在。我希望这些小说能表达一个不断变化的、越来越庞杂无趣的世界给人带来的严重的脆弱感和无力感,那些转瞬即逝的东西往往才是一个写作者应该抓住的,否则一味“宏大”的他(她),将不是一个合格的小说家——还得回到海明威的视野中,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方法论。我一点一点尝试:先锋的,不那么先锋的;尽力探测一个无意义世界的边界和限度;有时候,仅仅精约地呈现生活本身就能传达它的复杂多义,遑论绝大多数时候,神秘就藏在最日常的一句对话一次独白之中。于是,当你瞄准外部实则向内,当你仔细聆听内心独白,小说自会发芽成长,自会呈现张力;你必须小心翼翼地捏造、破坏、打碎,尽量让它简单和平实……后面三五年,我的小说基本上在这样的维度上游荡,不问收成,不计后果。幸运的是,它们大多还是发出来了。我忽然有了某种成就感,是的,多多少少,有六七个小说抵达了我渴望抵达的地方,呈现了我希望呈现的“神秘”。
然后呢?
又卡住了。
自去年以来,越写越痛苦。回到文章开头部分,文学确乎是有标准的,而且是绝对意义上的标准,它们永远在那里,像乞力马扎罗山的那头豹子一样安静高贵,不容置疑。让我大声念出缔造者的名字:纪德、博尔赫斯、科塔萨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海明威、福克纳、马尔克斯、奥康纳、鲁迅……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让你绝望的是当你用这份名单瞄准你的写作,你真想一把火把家给烧了,把你写下的一切烧了,让它们滚蛋,让它们匿名,让它们消失,永远别来烦你,而你也不想承认你是它们的缔造者。是你,不是别的什么人辛辛苦苦没日没夜地写出了它们。是啊,你心里忽然闪出一句锥子般的真话:垃圾制造者。除了垃圾,你没给这个世界创造任何东西。
没错,如果用这些老家伙当作我们唯一的标尺而不是无可无不可的标尺,我们的写作将出现非常大的问题。世界观的问题、语言的问题、想象力的问题、哲学的问题……一切都成了问题。你绝望得想死。而我在拆解科塔萨尔的《正午的岛屿》时,发现想象力根本无法抵达最终那个关键性的句子:“那具睁着眼睛的尸体是他们与大海之间唯一的新鲜事物。”这种句子是不可能单靠想象力实现的。靠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天赋,或直觉。是科塔萨尔的直觉,是缪斯突然吻了他一下。这一刻,这个人多么幸运哪。他毫不留情地杀死了绝大多数作家。在有如神助方面,我们分出了胜利者和失败者,写出科塔萨尔式句子的家伙正式加冕为胡里奥·科塔萨尔,没有写出的,只能是湮没无闻的泛泛之徒。
文学多么残酷。文学就是这么残酷。
好吧,让我战战兢兢地回头看看吧,天哪,哪来的胆子写了这么多!所谓“写废十年”,呜呼。
好在文学最可怕的幻象之一,就是远方一直在着,无论大江大河还是高山峡谷,你身边有无数的经典,无数次展开塞壬的歌喉,引诱你、呼唤你,往前走一步、再走一步。唯有失败,唯有不断不断地失败,也许,才是向它靠拢的捷径。这么说多矫情啊。但卡夫卡们、伯恩哈德们、科塔萨尔们就在那里,一直在苦口婆心地提醒你、呼唤你。失败不丢脸,丢脸的是你很可能为了避免失败,一步就迈向了成功。当然了,失败会让你消沉、堕落、无用直至消失,但没关系,反正选择文学就是选择荒唐的白日梦冒险,时时都有消失的可能。那就让你的写作再悲壮再矫情再认真再自私再凶狠一点吧,反正结局无非失败,不是吗?
那就像个爷们儿一样,瞄准下一个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