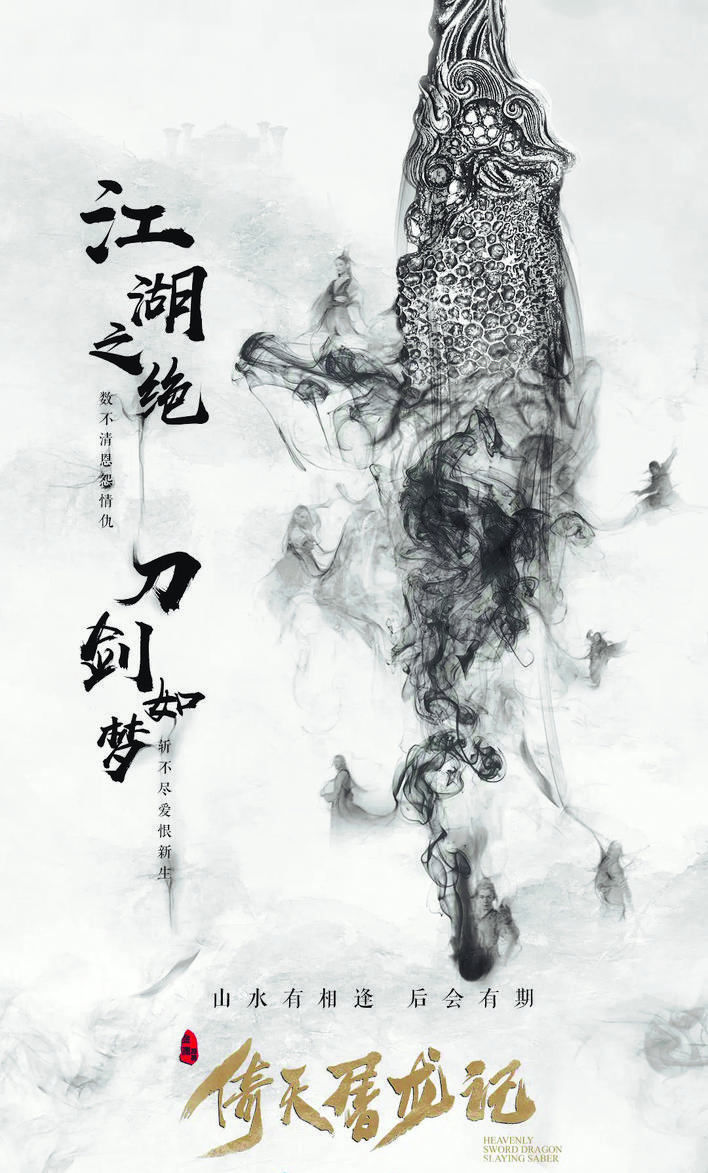近十年来,中国文学异彩纷呈,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发展一体两翼,各类型文学佳作不断涌现,共同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在这其中,武侠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创作一直都是世界认识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作为通俗文学的重要分支,从20世纪现代武侠小说诞生绵延至今,武侠题材创作已经孕育出一套相对完善的书写体系,在广大读者和观众心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记忆。近十年来,武侠创作依然延续不断,传统武侠作品魅力不减,网络武侠小说也在持续发力,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新意象与新变化。
一、传统武侠的赓续和转型
古有“侠以武犯禁”的说法,但古史典籍和古代小说尚未将“武侠”二字并举。“武”“侠”二字第一次合体,出现在日本通俗小说押川春浪的《武侠舰队》中,并由一批留学生重新诠释,将“尚武”的武侠概念引入中国。20世纪初期蒋智由为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作序,强调了“武”的重要性,以期激发民众的拳拳爱国之心,并宣扬民族精神中的力量感。1915年包天笑将林纾所写的小说《傅眉史》命名为“武侠小说”,渐渐地,“武”和“侠”开始在创作中一同出现。
不过,在“武”和“侠”并称之时,还有一类以“侠”为主体的小说存在,他们并没有在目次和分类中接受“武侠”的“名义”,而是选择以“侠情”代之。1914年在四川成都创刊的文娱杂志《娱闲录》中就曾有小说栏目,在此栏目中,侠情小说是重要的题材之一。这些小说大多保留着古典小说的韵味,但在内容上有新探讨和新想法,“侠”的论述主要以“情”来推动。事实上,谈起武侠书写,“侠”的精神意旨不仅体现在“武力值”的比拼和武学的传承上,也表现在很多情感纠葛中。以个体的情见众生的义,是众多武侠小说的惯常写法。纵观现代武侠小说创作,基本是围绕着“武”“情”“侠”三个方面展开叙述,郑证因、王度庐、金庸、古龙、温瑞安等人更是将“武”“侠”“情”三者巧妙融合,“武”中有“侠义”,“情”中有“武学”,开创了中国武侠小说的三重空间和叙事形态。
相较于“武”和“情”这两方面,“侠”具有抽象性,在叙事上更不好把控。将“武”和“情”融入其中,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搭建出“侠”的展示形态和感悟方式。我们可以借由武打的表现力以及武功竞技的方式去感受虚构江湖世界中的“侠”的威力,也可从“情”的维度去体味类现实空间里的生活日常和人生际遇,甚至可将三者混融在一起,探讨侠客在精神世界和俗世生活中的挣扎与坚守。例如金庸写“情”,“武”能与之匹敌,“侠”也寄居其中,杨过的黯然销魂掌,既是他勘破的情,也是他练就的武,更是在襄阳大战时助他实现大义的制胜奇招。古龙笔下的“武”也是每个人身份与机缘的化身,傅红雪的“天移地转大移穴法”一如他的人生轨迹,他的人生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交换出去,而当他复仇的信念坍塌之时,他又一次体悟到了天移地转的妄诞与彷徨。
可以说,“武”“情”“侠”的综合,使得“侠”更加具象化,也开辟出了武侠叙事的双层线索,侠客们在“情”中见“众生”,于个体的“小我”实现中参悟历史洪流中“大我”的价值意义,拼接了侠士生活的微观世界和精神层面的宏大叙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三者交互的文学空间中,“侠”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形态。20世纪上半叶,“仙侠”小说《蜀山剑侠传》横空出世,开辟出仙侠小说的文化传统,塑造了仙侠的文学模型,但这样的写作传统在一段时间内却销声匿迹。随着以“武”“情”“侠”为标识的历史江湖系列陷入瓶颈,“仙侠”传统被再次召回,2005年改编自单机游戏《仙剑奇侠传》的同名影视剧上映,拉开了仙侠影视剧的改编序幕。如今在网络小说及影视IP改编中,现代传统武侠慢慢减产但余威尚存,叙事形态依然围绕着“武”“情”“侠”三方面展开,而在这三重空间之外,以“仙”为形容词的文学世界观和文化体系也被重新拾起,仙侠创作的产量多于武侠作品,受众圈层也广于武侠,武侠文化的表现形态发生了变化。曾经被特意提出的“武”被“仙”替代,甚至重新混为一谈,诸如男频的《诛仙》《雪中悍刀行》《将夜》《择天记》等都有玄幻和仙侠元素,而女频则在仙侠中嵌套了一项程序完备的“虐恋”体系,《花千骨》《重紫》等小说都是用仙侠的框架去谈情、去认世。在近十年的仙侠创作发展过程中,“武”的方面融入了“仙魔”体系的“法器”“轮回”等专业术语,写作者试图以重新塑造和建构的儒释道思想体系来解释“侠”的精髓。
二、武侠小说的网生性
近十年来“仙侠”的流行,正源于“武侠”的衰退。金庸作为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已经将武侠小说的整体构造锻造得十分清晰完善,后来的创作者想要超越他的格局和写作方式实属难事。在今天的影视改编中,金庸的武侠小说依然占有一席之地,在一些观众心里,金庸的武侠世界代表了武侠文化的全貌。为了打破这种焦虑,很多创作者纷纷投入到被遗忘的仙侠模式中,企图创造出新的创作形态。一些创作者更从媒介变革中借力,在形式和内容上重塑武侠小说的表达方法,新媒介平台的出现也为武侠创作带来了新的视域,使得武侠小说及其影视改编在样态上具有网生性特点。
首先,在形式上,相较于传统的武侠小说,网络武侠小说更注重网络小说的连载特点,强调手机端、PC端阅读的舒适与友好,格式上不再是以前的根据主旨内容进行的段落连接,而是讲求网络连载的排版,形成了单句成段、句与句之间空一行的格式。这种格式更有利于读者在通勤路上或晚间消遣时拿着手机阅读,能够改善读者因为字数过多、排列过于稠密、观看时间过长而造成的眼睛不适。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内容书写的转变,在传统的武侠叙事中,由于结构与情节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很多时候读者和观众记住的是整体讲述的“事”或者人与人之间的“情”,但新的连载模式却让大家在记住故事的整体架构之外,更容易被单独成段的“句”所吸引,故而很多时候句意的表达需要“直给”,或者说要写出能令人醍醐灌顶,带领读者清晰阅读,带有明显信息要素和情绪点的“金句”。
其次,网络平台使得武侠文化的展示度更高、展示范围更广,媒介变革所引发的IP理念为武侠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生机。武侠小说的IP化,直接扩大了武侠元素的表现形式,武侠歌曲、武侠电影、武侠电视剧甚至人物角色都可成为重要的IP元素,被进行重新开发和再次创作。IP孵化的连续性和多效产能等特点,使得武侠小说的生产不断繁衍,不断在大众中强化记忆。一方面,这促进了传统武侠小说与当下文化视域的融合,如金庸的小说基本已形成独立的IP宇宙,产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多部作品不断被改编为网剧或者网络大电影,以往的改编佳作也以综艺或视频剪辑等形式重新活跃在大众视野中,网络上围绕着金庸的作品衍生了很多同人创作以及相关知识科普和学术解读。网络让传统武侠的生机得以延续,并突破了代际圈层,进一步拉近了与当下青年群体的距离。另一方面,新的武侠小说在网络上连载,网友重新拼接的新的武侠故事也在各类视频平台上播放,借助网络平台,武侠创作群体向大众倾斜,开启了全民共享的大众狂欢。虽然我们常说武侠式微,但武侠文化却未从大众的记忆中褪去,只是因为IP化的生产模式使得武侠发生了一些“位移”,失去了原有的记忆中的色彩,但也因此重获了新的表现力。
最后,从叙事结构上来说,网络媒介不会改变武侠小说“武”“情”“侠”的表现内核,却能够引发新的变奏。在部分“Z世代”的消费观念中,对使用产品外观的“颜值”要求时常大于产品的实用性功能。随着影视剧的IP化和网络化,平台对于影视剧的评判已经不完全依照于传统文艺的评价体系,以量化数据为代表的评价标准使得影视剧的生产具有了商品化的效能。相较于“武”元素在影视中的投入和产出比,“情”的收效率更高,CP文化的兴起更推动了“情感”类剧情的增加。现今的武侠创作有弱“武”重“情”的趋势,而“武”的退潮、“情”的涨潮,也造成了武侠所写的侠义不再只是呈现江湖中掌握武功技能的大英雄,而是更多地去挖掘江湖中个体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变化,去探寻生活中的“侠”的多样性,以反“武”为目的去看江湖里的人间世。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现今武侠创作也有一些局限性,在快餐化的文娱生产模式的影响下,很多影视剧的主创团队并没有较多时间训练武打,“武”的展示空间逐渐缩减,进而也无法捕捉到其背后的自我探寻意识。而为了追求消费逻辑中的“奇观效应”,“情”的内容被无限放大,一些江湖中复杂的“世情”被狗血、虐心但情节单一、形式压抑的三角恋或者多角恋取代。
三、文学类型的互文生产与叙事空间的拓展
武侠创作产品化之后,网络创作者的写作更加依赖于市场,与以往传统报刊连载不同,网络的信息反馈更具即时性,为了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很多网络小说的创作者往往会及时地根据市场兴味而调整写作主题,他们的创作认同也并非像传统武侠小说作者那样更专注于武侠一隅,往往会在写武侠小说时,也开启其他主题内容的创作。
本质来说,在网络新媒介的影响下,武侠的文类特征已经不突出了,它和古代言情小说、“穿越小说”等在整体价值上并无过多差异,无论是在江湖中寻找打怪升级的“爽点”,还是在俗世生活中寻找生活的“爽感”,这些作品负荷的价值均是强调阅读快感的功能性感受。而网络小说IP化的进程更助长了此种创作姿态,很多影视改编已经不满足于在江湖世界中穿行叙事,而是试图进行空间突围和叙事进化,他们不仅将视角定格在江湖内部,更将权谋宫廷文中的庙堂,以及种田文中细碎的生活场景、玄幻小说中的奇幻景观,甚至于言情小说的爱情模式等通通纳入到武侠体系中,以谋求更多元的快感输出。可以说,在武侠创作中,叙事景观的规模在逐层递增,“江湖”的原有边界在不断向外拓展,开掘出了新的故事发生地。由于多种叙事的参与,武侠小说变得更具互文性,或与玄幻、修仙、言情、权谋等小说题材熔于一炉,或成为一种表意形态走入其他文学类型中,形成特有的符号和意象。
电视剧《雪中悍刀行》即尝试了一种新型的武侠写法,将玄幻、权谋、修仙杂糅在一起。徐凤年在庙堂和江湖、家族之间来回辗转,他走江湖是为了历练,再入江湖则是为了复母仇、为了反抗父亲,以自己的方式为家族谋事。徐凤年的个体实现是在江湖和庙堂之间,主要矛盾的焦点则围绕着家庭场域。在整体构架中,江湖和庙堂未有实质性区别,甚至基本已经合二为一,问探江湖事,答案在庙堂。而在尔虞我诈的庙堂政治和风霜刀剑严相逼的江湖混战中,因为权谋叙事的混入,造成了主要人物武力值减退、话语输出增强,心理表现被语言表达外化的情形。徐凤年并不是以习武为目的走入世间,可在机缘巧合下又不得不以习武为名义闯荡江湖,从中明显可看出此剧的反“武”意图。在剧中,侠客温华得知老黄死讯时说了一句话:“江湖有人来,就有人走。”这句话解构了金庸、古龙等人创立出的武侠形态,并不执着地将江湖设定为庙堂之外的超逸空间,它已经和世态人情融在一起,处庙堂之远已非易事。江湖不过是心灵的镜像,因而无论以哪种形式,任何人都可成为侠,侠不再单纯是一种形式、一种使命。
事实上,大量还原和复刻生活世界是近些年武侠小说影视改编的一大趋势。一方面,这是新武侠IP的探索和试验,试图以更具普遍意义和共同认识的生活日常,来唤起当代年轻观众对现代“武侠”的移情;另一方面,由于杂糅了过多的日常生活情节,导致武侠主体叙事产生混沌,很多故事想要面面俱到,却往往事与愿违。太多的日常细节、过多的心理描写和语言输出延宕了武侠叙事本该有的快节奏,忽略了快意恩仇的意象表达。
将武侠的书剑恩仇和着意刻画平淡琐事、生活温情的“种田文”风、职场叙事相结合,这在网络小说中数见不鲜。将几个原本关联不大甚至相悖的叙事逻辑糅合在一起,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大众渴望逃离现实生活的烦忧、在虚拟想象中以过来人的姿态重建日常生活的时代情绪。在这些创作中,传统武侠最后的“处江湖之远”的结局被续写和扩写,江湖和庙堂共同组合成为江湖侠客们打怪升级的“职场”,家庭空间也成为武侠小说中的重要景观,武侠被写得更具有当下体验感。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武侠创作的网络互文性虽然打破了家庭、庙堂、江湖的空间界限,融入了不少其他文学类型的要素和特色,但这也使得武侠中“侠”的主旨含混不清。在很多杂糅了庙堂权谋叙事的武侠故事中,主人公大多以天潢贵胄的身份游走江湖,所要解决的不过是皇庭和家族之间的政见矛盾,他们一面借由游历江湖逃离出家、反抗父权,可也不过是高手相伴,在江湖上为家族存立招兵买马,让江湖人为己所用。名义上反抗家庭,可江湖纷扰、庙堂诡谲,家庭和伦理亲情反倒成了很多人的温柔乡和避风港。“侠”文化中的除暴安良、拯救苍生被裹挟在个体的功业实现之上,江湖与庙堂都不过是这些人宏图霸业的试炼场。侠客的“游”也更像是成长小说中的设定,另换空间以谋求个体知识和视野的提升,很多人物初入江湖的身份都并不是普通人,他们更多地是裹挟着古代庙堂的政治情绪,他们的难题并不能代表所有普通人的生存困境。武侠的根底最终指向了家族的守卫,平凡众生们的意义则被深深掩盖。
对言情剧情的收编,则让一些武侠陷进三角虐恋的叙事套路。在“爱情价更高”的言情原则中,很多复杂的讨论最终都被“情”字给稀释。剧情里几乎所有的冲突矛盾都因爱而不得而起,人物弧光反而被脸谱化了,人性的挣扎与彷徨也只限定在小情小爱中,这不仅使得故事里其他人物的理想主义光环大打折扣,也使得侠的意义混沌在了情爱中,即不是以纷繁的情感关系去梳理出“侠”的真正含义,而是以各类“侠”道来填补情感沟壑。“侠”的大爱为“小情”服务,爱情成为“不侠”的合理化注解。
纵观近十年武侠小说的变化和发展,有新意也有传承,整体来说,武侠小说的新设定既是媒介技术演进过程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创作者们试图跳出武侠传统框架的积极尝试,但由于武侠概念的特殊性,无论如何改变,在叙事上还是无法颠覆“武”“情”“侠”这三重基本空间。无论武侠还是仙侠,其终极意义都应体现在“侠”的塑造上。在“武侠”“侠情”的称呼中,“武”和“情”均是形容词,它们为精神层面的“侠”赋予了具有实感的行为动作和施展空间,无论偏重哪一方,“武”“情”都不过是“侠”的表现手段。若在创作中一味只强调“武”或者“情”,不过就是一场买椟还珠的表演,一如近年来不断生产的“仙侠”故事,“仙”也只是提供了“侠”的实现场景和具体身份罢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武侠创作保持“武”“情”“侠”这三重叙事空间的稳定时,一些新的文学母题和素材也出现在了武侠小说中,可无论有何种新的演进,写“庙堂”、写“爱情”还是复刻凡俗生活,绝不能是只为了增添主角的烟火气,或是为他们寻找人物“黑化”的合理化解释。“武”和“情”并不是“侠义”表达的主要矛盾,并没有限制“侠”的发生,而是要透过“武”和“情”的锤炼,让人物识小情、通大义,写出“侠义”的精神气,并以多重视角展现人物的内心冲突,重现人类普遍意义的心灵真实。
可以说,近十年武侠小说的发展有其变也有其不变,这样的发展态势不仅赋予了武侠创作与中国其他文学类别合流的可能,让它能够与世情小说、历史小说、神魔小说不断对话,也能够与当下的时代情绪、社会热点话题融合,敏锐地捕捉社会大众的情绪点,而“侠”的格局和意义又能够让它汇入到文学的主体脉络中表情达意,焕发出自己诗意与辉煌。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