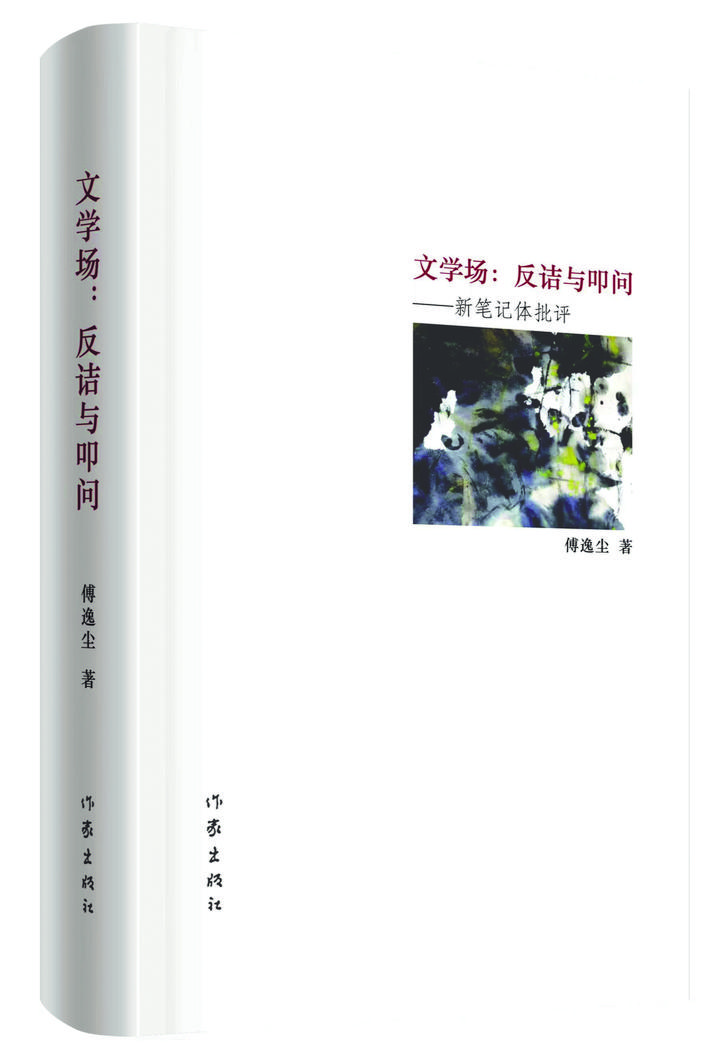傅逸尘寄来批评文集新作《反诘与叩问——新笔记体批评》,勾起了我对一些往事的回忆。2002年,原军艺文学系面向社会招收本科学生,2月份就进行了专业考试,初试考“文学基础知识与鉴赏”。那年的鉴赏题是我出的,内容是简析鲁迅《野草》里的《雪》。这篇文字不难懂,但要领会意义及其语言艺术并不容易,对应届高中生来说难度还是相当大的。我们的初衷是,如果能看懂字面并说出好处,就算合格;如果读出象征且完整表达出自己理解,就是优秀;如果吃透精神并以文学化的文字指涉原作意蕴,就是出类拔萃了。结果,在众多考卷中,有两篇脱颖而出,其中一篇就是傅逸尘的。我们招生小组商议,专业考试重在发现人才,假如在初试就看出苗头,后面就要加以关注。对此,系领导高度重视,对初试崭露头角和报考时提交有分量作品的考生,加一次当面考核,一来对其考试成绩和所交作品加以验证,二来也探测其文学方面的潜质。参加这次考核的一共4名考生,都达到了我们的预期。后来二试三试,傅逸尘稳定发挥,顺利通过专业考试。6月高考,成绩优异,就被录取为文学系2002级本科学员了。
原军艺文学系教学有优良传统,鼓励学员施展才能、早出成果。傅逸尘有较好的文学功底,入校不久便开始发表评论文章,到了大二就有了不少成果。那时候,其他各系经常搞教学“展示”,比如音乐会、剧目汇报、舞蹈示范课、画展、广场晚会等等,文学的教学成果该如何“露脸”呢?系领导和老师们商量,决定设一个“军事文学新人奖”,再办一个经验交流会。当时有几位学员写作势头看好,丁旸明同学创作并出版了抗战题材长篇小说《悲日》,祖若蒙同学在《北京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对于本科生来说,都难能可贵。经验交流会如期举行,学院非常重视,院领导悉数到场。举行颁奖仪式后,傅逸尘和丁旸明、祖若蒙同学都作了发言,邢军纪教授代表教员发言。最后学院主要领导讲话,对这次活动以及文学系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会议的效果相当可观,同学们紧接着都相互砥砺、发力写作,学员队开辟了自己的文学阵地《红星文坛》。不久后,丁旸明的《悲日》获得了共青团“五个一工程”奖,其他同学也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那是文学系学员写作势头最好的一段时间,算是向人才辈出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致敬。当然,这也得感谢学院创作演出红红火火的大局面,音乐系学员蝉联“青歌赛”团体金奖,戏剧系师生的话剧《我在天堂等你》斩获国家和军队各种大奖,舞蹈系学员把“桃李杯”“文华奖”以至于国际赛事的金银奖拿了个遍。那时节,很像戈蒂耶描绘浪漫主义思潮所说的:“生活中涌动着新的活力,势不可当。各种东西同时萌动、发芽、破土而出。鲜花开放,散发出醉人的芳香。”
本科毕业,傅逸尘顺利考上研究生,师从朱向前教授,主攻方向是当代文学批评和军旅文学研究;名师高徒,“百尺竿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三年研究生,我除了担任文学理论的课程,对他的专业学习关注不多。后面的进程是按部就班,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工作。毕业后,我们联系渐少,只是听说他被评选为“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并出版了第一本批评文集《重建英雄叙事》。此后,又陆续出版了《英雄话语的涅槃》《叙事的嬗变》《“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等多部理论和评论专著。到如今,他已经是比较成熟的青年批评家了,文章、著述都颇见规模和影响。眼下这本《文学场:反诘与叩问——新笔记体批评》文集,应当是他从事文学批评近20年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傅逸尘把他近期的写作叫作“新笔记体批评”,应当包含了为当代文学批评寻求创变与突破的用心。麦克卢汉说过“媒介即讯息”,批评文体的嬗变一定影响到批评的功能。我不太清楚这种“新笔记体”的当代背景,但放到批评史上看,它是有传统的,比如中国古代文论里的“诗话”和“评点”。“诗话”就是笔记,许多都被编入笔记体小说(比如《说郛》);“评点”主要用于小说批评,其中“回评”“总评”和“读法”的文字较多,也有笔记的意味。简单地讲,笔记就是读后感,是第一时间把阅读的感受记录下来。当然,这并不是单纯的感受,而包含了批评者的思考、鉴别和判断。这种批评方法在中国古代非常流行,林林总总、蔚为大观,是传统文论里内容最为丰富的那一部分。逸尘的“新笔记体批评”跟传统的“诗话”“评点”有关吗?或许没有。但我仍想用传统“笔记体”的特点来说说“新笔记体批评”的优长。
一是敏锐。但凡用“笔记体”进行批评,总是要抓住阅读之初的感受和反应。古人用“诗话”和“评点”的方式,而且每篇的字数都不能多,就是这个原因。而“敏锐”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又非常重要,别林斯基就认为“敏锐的诗意感觉,对美文学印象的强大的感受力,才应该是从事批评的首要条件”。可见没有这个特质,很难从事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逸尘的批评文集里,大部分是作家作品专论,其中大多数是“第一时间”的捕捉和表达,因而让人感到鲜活、及时以及“亲在”。这种“亲在感”不仅体现在时间,而且从他的文字中也能嗅得出来:毕竟刚从地里采摘的蔬果跟冰箱里放了多日的蔬果在成色和味道上都是会不同的。
二是节制。既然是“笔记体”,就不能放笔铺陈,面面俱到。中国传统批评里的“诗话”大都很简约,唯一一部长篇大论的《原诗》,被数落为“非评诗之体”。这当然是偏见,但“诗话”因体制所限,的确是要求批评者在文字上精简、精简、再精简,简到极致,就成了“无”,就是所谓“摘句”:只列举批评对象,不发表自己意见。逸尘的“新笔记体批评”自然不会这般“大音希声”,它仍然是文章,但笔法洗练、用语讲究,有意识地避开“研究式”而亲近“文学性”。其实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尤其是“笔记体”批评的显著特征。在西方文论里,也多有人倡导批评的“文学化”,比如施勒格尔认为“诗只能通过诗来批评”,波德莱尔认为“最好的批评是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法朗士认为批评是批评家“让自己的灵魂在杰作中探险”,这些意见虽然不是主流,但批评的文学性却是很得人心。从总体讲,文学批评的文体和文字的自觉是普遍要求;从局部看,如果开创一种融会了传统与现代的“散文化”的批评方式,应当对当代文学批评功莫大焉。逸尘的“新笔记体批评”有这种预设,亦做出了初步的成功实践。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这种文体层面的创新和探索有着强烈的自觉和主动的追求,对此我深表期望。
三是灵动。文学批评跟文学理论不同,它要体现出悟性和“机锋”,它的话语要能够腾挪收放、变化自如。批评不是报告,不是推理,也不一定是论辩,它是一种类似“拈花微笑”的“点破”和启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批评先要动人以心,然后才是晓人以理,或者说是把“明理”融化到“会心”当中去。刘勰所说的“知音”,正是这个意思。逸尘的文字灵动、细腻,追求现场感和散文化。他在“跋”中谈到中国传统诗、书、画的格调和境界,谈到文学批评“写意”的可能,想必这都是对更加空灵、更加诗意的批评文体的探寻和努力。他还年轻,相信会有达到预期的那一天和“那一部”。
我是学习古代文论的,所以多从传统文学批评的特性出发去揣摩他的“新笔记体批评”,实则他追求的成效并不止于此。比如,批评文本的背后具有清晰的理论思考的脉络;又比如,吸收了许多当代的批评观念和术语;最重要的是,他的批评虽为“笔记体”,但完全没有传统“诗话”或“评点”的习气和短板,如拉杂、迂腐、偏颇以及章学诚所声讨的“文人相轻之气习”。逸尘批评文集的下编,收录多篇宏观的和理论性较强的文章,思索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以及军旅文学研究的建设性和方向性问题,立意高,视野阔,思理深。这无疑是他追求“新笔记体批评”的坚实基础和强大后盾。这也显露出一种姿态,表明未来成熟的“新笔记体批评”会是怎样一种“新批评”。
逸尘目前以及今后很长时间都会在批评一线,作为年轻有为的批评家,要更加专心、更加进取,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记得当年王蒙先生为批评家撰文,题目叫“当代作家的爱与知”,就把这句话送给他吧。还记得当年叶帅题写过的义山诗句“雏凤清于老凤声”,也一并相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