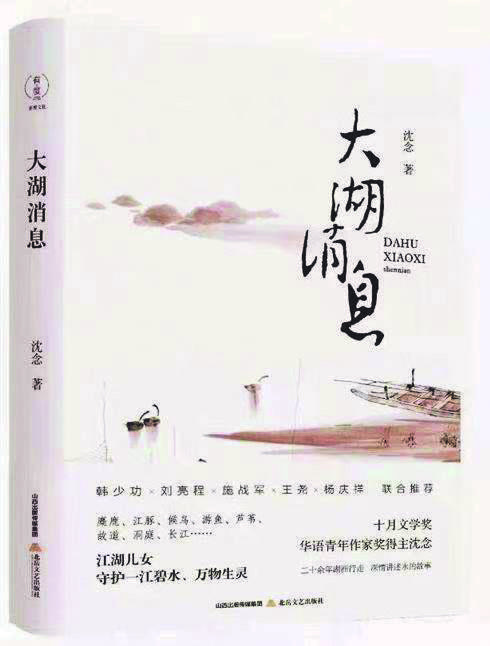教鹤然:在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之前,您的散文《大湖消息》已经引起文学界的关注。能否请您谈一谈这部作品的创作历程?
沈 念:《大湖消息》去年12月出版后,入选了很多新书榜单。有人问,这本书写了多久?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从我开始写作,就一直是在处理洞庭湖这片河汊众多、江湖川流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地方性格、地方经验和地方故事,各种耽搁,迟迟未能集中精力进行系统地书写。缘起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到了我的家乡岳阳,提出“守护一江碧水”的要求。2020年下半年,疫情稍有缓解,湖南省启动“青山碧水新湖南”的创作活动,我把写作提上日程,又选择性地回访洞庭湖和长江,多数篇章是在2021年上半年的时间里写完的。写了一年左右,但感觉又是写了很多年的湖区生活经历。
洞庭湖是湖湘大地上的母亲湖,这是一个宏观上的认知。我对它的认知也是逐渐加深的,越了解它的过去和现在,就越加关注它的未来。我曾经有一种深深的愧疚,这种愧疚来自我对这片土地索取的多,回报的少。当我再次回去,似乎所有的积淀都发生了化学反应。这就变成了一个写作者与故乡的“归去来”。每一次折返,都是一次发酵、一段情话、一种碰撞,更是很深程度上的灵感激发。
这本书的写作凝聚了我对故乡的深情与眷恋、忧思与憧憬。我与那些候鸟、麋鹿、植物、鱼类、渔民、研究者、志愿者的相遇、相识,我选择的人物,也是我遇见的人,这都是一种缘分。我特别看重这样的遇见。我和他们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江湖儿女。我在“打捞”他们的人生往事时,其实是将属于江河、湖泊的时光挽留,是在感悟并学习承受艰难、困阻与死亡,是尝试以超越单一的人类视角,去书写对生活、生命与自然的领悟。我的初衷是还原一个真实的湖区生存、生活世界,书写一个有情有义、有悲有喜的人世间。
教鹤然:承接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到五四时期的杂文、小品文,再到新时期以来散文写作的转向,当下散文创作受到非虚构写作的影响,也出现了美学风格的新变,据您观察,当代散文的整体现状如何?
沈 念:我是当代散文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的一片叶子。我没法用几句话去谈论散文的当下整体状态,只能是从我的阅读偏好中,从我所能感受到的枝条颤动、树木摇晃中谈一点认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种文体有一种文体的渐变与丰富,当下语境里,现代性叙事意义上的散文写作已经越来越为人所跟随、认定。表达现代生活的复杂经验,说别人没说过的言语、感受、逻辑,才会有真正意义上个人性的呈现。没有个人性的东西,就没法标识出你的风格特征,可能就是所有人在写同一本书,这样的创作是必须警惕的。
谈到《大湖消息》,有人可能会谈到非虚构或虚构的话题。任何写作只要进入一个主观表达时,它就会发生位移。只要是站在一个主体真实情感上的写作,就不应该被虚构或非虚构所困囿。我反而会觉得,通过文体的开放性,小说、诗歌、戏剧这些元素加入进去,作品就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它变得不一样,产生一个跟过去、跟很多人的写作不一样的新面目。不管写什么、怎么写,每位写作者笔下的人物、命运、故事,那种现代人复杂经验带给他人的共鸣、共情,这才是最真实、最重要的。
教鹤然:您的《大湖消息》有很多“标签式”的评价,比如“青山碧水新湖南”主题创作非虚构作品、比如生态写作理念下的散文作品等,对您个人来说,这部作品应该也有着比较重要的意义,您觉得,这些评价是否贴切您的创作初衷和核心理念?
沈 念:我没有过多考虑过被贴什么标签,因为一次写作完成了,需要考虑的是下一部作品。但从评论和媒体的反馈,有不同角度的解读。山可平心,水可涤妄。《大湖消息》凝聚了我对大湖的书写理想,折射出我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与万事万物的态度。
任何一个地方的元素和精神内涵,归根到底落点还是在人和物的身上呈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不可能均等的取与舍。从这个意义上出发,每一位投身自然生态文学书写的写作者,必然要去直面欲望带来的责难,要去书写反思与自我拯救。而我就是要从水流、森林、草原、山野以及大地所有事物之中“创作”一个未来,那里有对大地上、人世间最坦诚的信任和依赖,也是写下献给未来的“洞庭湖志”。
教鹤然:还记得您曾经提到过“鱼腥味”与南方写作的文化性格,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南方气质与“岛屿”经验是地方性经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您的作品中,“水”似乎是很重要的意象,语言也充满了潮湿、细腻的情感质地,的确与带有北方风格的写作者有明显差异。那么,您是怎么理解地方性经验与个人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沈 念:洞庭湖是我创作的原产地。我在洞庭湖的水边生活了很多年。水,给了这片土地灵性、厚重、声名,也给了人刁难、悲痛、漂泊,更是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和源泉。长久以来,我睁眼闭眼就能看到水的波澜四起,听到水的涛声起伏,水的呼吸所发出的声音,是液态的、颤栗的、尖锐的,也是庞大的、粗粝的、莽撞的。水能把一切声音吸入胸腔,也能把声音挡在它镜子般的身体之外。我原来以为岸是水的疆界,但在行走中我懂得了水又是没有边界的,飞鸟、游鱼、奔豖、茂盛的植物、穿越湖区的人,都会把水带走,带到一个我未曾想到达的地方。还有那些曾经没有户籍的渔民,沿着水流四处飘零的人,他们所赖以生存的是真正的江湖世界,他们是本源上的江湖儿女,他们的流动性所孕育出来的地方性格,是走到哪里,就传宗接代在哪里。他们相信神意、邂逅、善良、浪漫,有把自己交付给陌生人的勇气,这与水的流动性天然地关联在一起。
我在写作地方性经验时,是保持着“小地方人”的谨慎的。这种谨慎,是提醒自己要把记忆中最深刻的经验和细节,融入到对世界和自然的看法之中。一个人写作的落实过程,就是要把一个地方写实写透。地方性经验于我,既是熟悉的写作,又是有难度的。《大湖消息》于我是一次有难度的挑战,面对湖洲之上的生命,我的书写视角是多维的。鸟不只是属于天空,鱼不只是属于流水,水不只是属于江湖,植物不只是属于洲滩,人不只是属于大地,它们所组成的生命有机系统,任何一个环节的塌陷和破坏,都可能导致系统的紊乱。文学要呈现的就是为这个有机的生命系统立心、立命,要把生命中难以表达的情感传递出来,在“所见”与“所信”之间,让个人的写作被生活与美学“双重验证”。
教鹤然:您是散文和小说的双面手,包括在《人民文学》发表的《长鼓王》、在《十月》发表的《空山》等作品,而后又结集出版《灯火夜驰》。您选择以“文化扶贫”“易地搬迁”等主题作为表现扶贫攻坚成果的切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写作方法是否也影响着您的散文写作?尤其是您之前的基层经验和多年记者工作的积淀,想必也为您的文学创作打开了一扇窗。
沈 念:前面提到过,为了写《大湖消息》,我反复地回到洞庭湖走访,这是一种深入生活,直接影响到了写作的成像。作家是时间里的人,也是改变时间的人。作家在这个时代里生活,就是在创造新的时代与生活的文学记忆。我的下乡经历、记者工作,不仅为我的写作,也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我在这个窗口盼望,看着外面的日月星辰、风霜雨雪,看着走过的足迹和擦肩而过的众人面孔,愈加会从心底告诫自己,认真对待你笔下的文字和眼前的世界,努力写出可以信任的希望和灵魂。
教鹤然:您曾经说过,写作者要找到自己的根据地,并透露过想以小说的方式书写洞庭湖,那么,您未来的个人创作计划是什么?
沈 念:“根据地”是写作的底座与依托,你不断回望它,它就会给你顿悟与创造的激情。写作者的根据地永远在同行,甚至在后面推动着往前奔跑。我今年在写一部乡土题材的长篇,散文创作停了下来。我反复在提醒自己,洞庭湖是一块丰富、驳杂的创作根据地,依然是要一头扎进去。写出与时俱进的时代之变、生活之变、文学之变,也依赖于把“根据地”扎深,写实写透。我不是那种有远大抱负的人,但也正是这种“没有”,让我能在一条认定的路上不管不顾地往前走。
人都须为选择而背负,好的或坏的,绝望的或倔强的努力。任何一条道路都不会是坦途,文学亦是如此,前面虽有风景摇曳,也得先穿过荆棘和丛林、沼泽与沟堑、黑暗与破碎。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肉体抑或精神,人类所面临的很多困境(生存、精神),那些纠缠不休的问题,大多是相似相通的。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围绕着“人”进行着不同的书写,我希望我的写作是在创造一种新变和越来越阔大的可能性。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洞庭湖是我生命中最有力量、最富情感、最具意义的一块福地。未来我会写一部关于洞庭湖的长篇和系列中短篇,这既是一个创作规划,也是我心底的文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