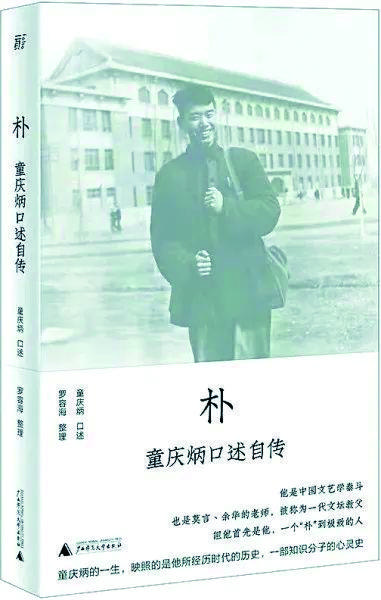曾国藩曾这样论及读书:“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敢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读《朴:童庆炳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不由感慨,童庆炳先生正是这样一个有志、有识、有恒的读书人。
童庆炳先生读书,首先是出于热爱。家境窘困,不得已而辍学在家劳动的一年,在别人都去玩耍的夜晚,他却在小小的煤油灯下,将村里所有的书都搜罗来读;在战火纷飞的越南,他早出晚归,撰写了备课讲稿与作品注释,从《诗经》到《红楼梦》,近60万字;在地拉那,他从大使馆“偷”古籍来读,从《诸子集成》看到《二十四史》,又读巴尔扎克与《鲁迅全集》,有书为伴,不觉寂寞;行政、教学、科研三大重担压在身上的四年,他依旧要求自己每天早晨六点坐在书桌前读七个小时的书;“冷冻”两年,他的床头桌上和枕头边永远放着一尺多高的书籍和笔记本,夜深人静时仍神采奕奕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无论贫困或富有,忙碌或闲暇,无论在家乡还是远方,是学生还是老师,童庆炳先生没有一天放弃过读书。他很小便意识到:“不读书就没有文化,你的思想是贫乏的,你的见识是狭窄的,无外乎就是周围亲眼看到的这些有限的现实;只有书本才能给你提供想象,提供新的知识,让你看到新的世界,让你知道,在你之前有很长很长的历史,在你之后,还会有很长很长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因此,他不时提醒自己:“知识一定要积累。力量靠厚积才能薄发。不厚积,靠爆发是爆不出来的。”于他而言,读书,是兴趣,是事业,更是孜孜不倦的追求,源源不断的动力。
童庆炳先生读书,又不止于热爱。在他看来,读书做学问有四种境界:第一境,看出门道所引起的兴趣;第二境,欲罢不能所引起的兴趣;第三境,获得成果所引起的兴趣;第四境,释放生命活力所感受到的幸福。童庆炳先生所赞赏的是第四种境界:“做出学问来,就会激发生命的活力。在做学问中生命的器官不但没有生锈,而是越来越敏锐。不但有学问的欲望,还引起人的感性与理性的一切力量的活跃。这样,人也就能期待生生不息,与天地相参,与万物合一……春意盎然的温暖的人生是每一个人的期待。”于是,他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到文学理论研究事业当中,又用冰一样的冷静思索问题,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
童庆炳先生的阅读史有四点让我印象颇深。
一是广博。童庆炳先生读书从不拘泥于某一方向,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西方的,理论的、创作的,课内的、课外的……只要感兴趣的问题,他都去图书馆寻找答案。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刘勰、李白、杜甫、苏轼、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黑格尔、康德、席勒、马克思、恩格斯、普希金、别林斯基、卡西尔……也正因涉猎广泛,在做研究时,童庆炳先生才能博采众长,容纳百川。他始终觉得做文学研究不能局限于文学本身,文学理论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社会学……只有各种学问都有所了解,才能真正做到古今中外融会贯通。面对这广阔无垠的世界,面对这无穷无尽的知识,童庆炳先生坦言:“我没有理由做井底之蛙。我一定要在这文学的山川中永不疲倦地跋涉。”
二是专精。求学北师大,童庆炳先生深受李长之、谭丕模、陆宗达、黄药眠、钟敬文、启功、穆木天、刘盼遂、王汝弼、郭预衡、叶苍岑、徐世年、邓魁英、杨敏如等老一辈学者的影响,“他们对作品的分析、问题的理解,以及他们提出的一些新鲜的观点,乃至他们刻苦治学的精神和方法,都变成了一种学术的血液流淌到我的血管里,使我日后无论是提起笔写文章,还是走上讲台面对学生,我都会想到这位老师或那位老师。他们的教学作为我的积淀,成为了我人生历史的一部分,成为了我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当然,童庆炳先生并非盲目的跟随者与模仿者,他始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方法。做读书笔记,他更强调对书的理解,而非简单的摘抄,因而他的读书卡片往往散落在书中,要联系上下文才能显出意义。他喜欢背原典,觉得一首诗读十遍及以上,才能了然于心,理解透彻,真正变成自己的一部分。重要的书他总会反复品味,《红楼梦》读了无数遍,甚至有些章回都能背诵下来;即便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这样不能完全读懂的书,他也要一遍一遍去看,读到书页泛黄、封面破损还在继续细细参悟。他的夫人曾恬先生说:“新名词、新观念、新视角、新论点……扑面而来。他既不会对它们视而不见,也决不会轻易地向它们顶礼膜拜,他对所读的书永远用自己的‘胃液’去消化,消化不了的决不违心说‘香’。”(《老伴儿》)正是这样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造就了代表着一代学者精神风貌的童庆炳先生。
三是思考。读书之道,要在能“悟”,有终身事其业,而不解斯理者甚多。正如朱熹所言,读书“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也”。童庆炳先生总能够钻进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去,坚持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不掺杂私念。他强调文学作品的描写不应该是简单化的,其中应该蕴含着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一种张力,单纯的歌颂与批判都不能寻找到文学的真实;他看到了中西文化生长于不同的土壤之中,虽有相似、相通之处,却又存在不完全一致的成分,相异才是主流。童先生始终关注现实、关注时代,几乎每一个所提出理论都密切联系着当代文坛、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教育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
四是融通。迥异于大多数人所谓“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论断,童庆炳先生认为,学理论兼搞创作的传统由来已久,如茅盾、周立波、王蒙等都是既搞理论又搞创作的。他意识到,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是不同的——前者依靠理性,后者需要感性,但人始终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作家创作离不开理性,文学研究也不能完全脱离感性。“一个教师要是自己又能够写论文,又能够写小说,对学生影响很大。学生会对这个老师另眼相看,觉着老师不简单——他不但是这样说的,他还会这样做。说也能说,做也能做,他就是一个文学人。”童庆炳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个“文学人”,他读书做学问,也不时从事文学创作——灵感来时,他会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回忆苦乐交织的童年,怀念善良宽厚的祖母,感怀恩师的馈赠教导,记录走过的山川大河;搞研究时,他常常把自己的切身经历融入论文,从具体的事例中感慨而发,娓娓道来。
童庆炳先生曾给自己的书斋起名“消永日斋”,它取自陆游晚年书房的一副对联:“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童庆炳先生的人生秉持“四书主义”——读书、教书、写书、卖书,始终围绕着“书”这一方小小的天地打转。但他不悔,不悔埋首书桌的日日夜夜,不悔成为一名学生、一位教师,成为一名读者、一位学者。倘若重新选择人生的道路,他说:“我的下一个选择还是这‘四书主义’,因为我感到充实。”童庆炳先生正是这样一个有志、有识、有恒的读书人,并因此而成为一个颇有建树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和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