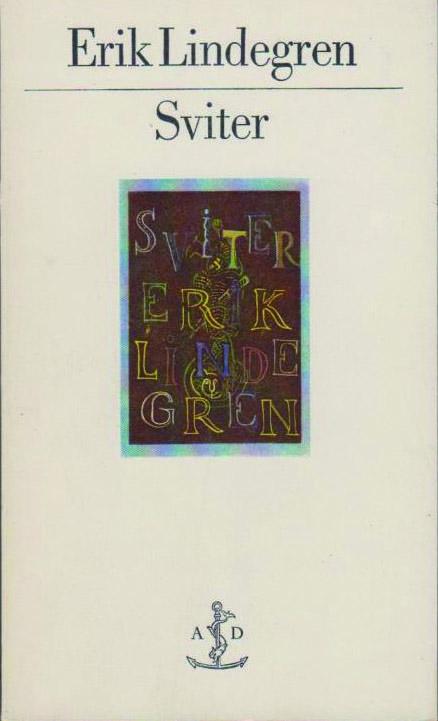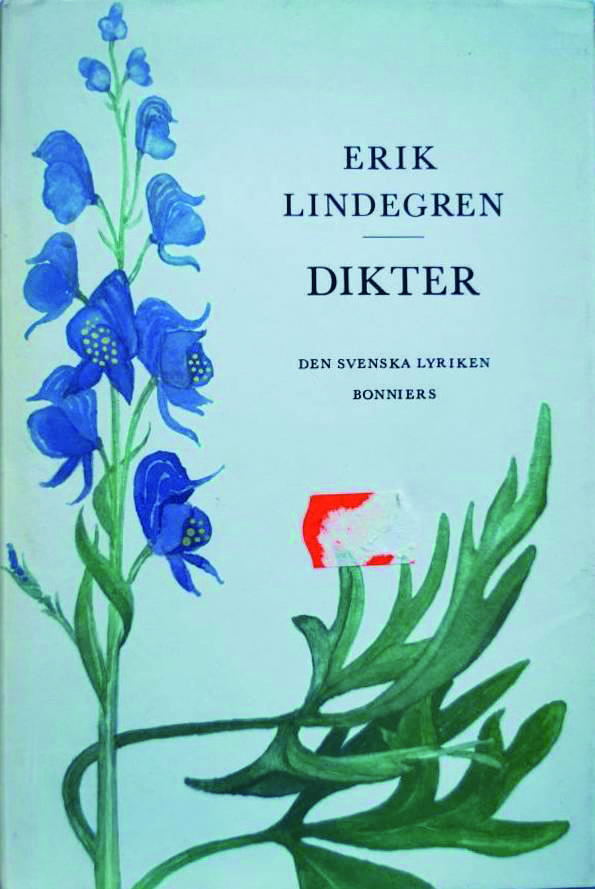这个冬天,供暖严重不足的2022年末欧洲的冬天,正以冻结的无表情,注视着林德格伦笔下20世纪40年代的迟暮欧洲。
瑞典诗人埃里克·林德格伦(ErikLindegren,1910-1968)一生只出版了四本诗集,即1935年的《遗世青春》,1942年的《无路之人》,1947年的《组曲》和1954年的《冬祭》。《无路之人》与早期斯堪的纳维亚诗歌决裂,同时继承北欧和欧洲诗歌遗产,结合20世纪上半叶欧洲实验诗歌的精髓,竖立起一座北欧现代诗歌的里程碑。其后,林德格伦逐步树立在瑞典文学界的地位,于1962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
生于北方吕勒奥的林德格伦是工程师的儿子。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学文学和哲学。处女诗集明显带有拉格克维斯特等人的影响。1937年夏游历芬兰,和那里的瑞典语现代主义文学开拓者埃米尔·迪克托纽斯等深入交流,几年后与瑞典现代派诗人阿瑟·隆德克维斯特相识并成为密友,笔下诗歌发生质变。
“无路之人”
林德格伦给出版商去信推荐自己“具有更丰富的现实和普遍人性”的新诗作《无路之人》。然而在出版方面,他没有路,只能自掏腰包。诗集问世后引起文学界关注。瑞典出版巨头伯尼尔在1946年推出第二版,掀起围绕着现代诗歌的不可理解性的激烈讨论。
《无路之人》卷首有这么几行字:“无影蜿蜒歧路/地上未知深渊/为太阳苦行的眼凝视/还有地平线的天生盲目。”歧路蜿蜒或许正朝着未知处。一轮俯视地球和众生的太阳。天上的眼是苦行的眼,地上的则天生盲目。人类孤独而无助,寥寥数语像是对无路之人类的鸟瞰图,暗合书名,透露出诗人的聚焦点。在不曾付印的序言里,林德格伦写道:“对诗歌而言,重要的是通过拒绝扭曲现在以准备未来,表达也许不受欢迎却强烈的情感。当下诗歌的特殊任务就是体验和反映时代的深渊。”
《无路之人》有40首十四行诗,以罗马字I至XL编号,每首由七节两行诗组成。前两首诗置于括号内,仿佛序曲,此外全书再无标点。除美杜莎等三个人名的头字母采用大写,其余一概小写。有五首诗写于1939年11月,其他写于1940年春夏,用林德格伦的话来说,那是“暴力、背叛和残忍庆祝和狂欢的时代”。
诗集中频繁出现眼、手、心、光、梦想、记忆、地球、太阳、生命、真理等相对抽象的字眼。抽象意味和具体意象比肩而立。第一首开篇这么写,“镜子沙龙里不单那耳喀索斯/绝望柱上无眩晕的宝座。”这样的句子无法以日常的经验、感觉和推理破解。不过《无路之人》毕竟不是大半个世纪后出现的人工智能作品,诗人自己或更能透露字里行间的秘密,林德格伦表示:“《无路之人》有某种世界末日的特性……作者希望无论内容或形式都反映出短暂而满满的时空给人类神经系统造成的大量灾难性的系列冲击,而不仅是有一个或多或少成功或不成功的时代文本,它不仅反映外部和内部混乱,也反映……人类的无能为力……形式里存在超现实主义视觉艺术和现代音乐的影响……要在现代科学世界观中表现理性与非理性的紧张关系……”
《无路之人》第9首这么写:
但首先一座饥荒之塔必须仁慈地倒塌/而距离点亮逃亡者的虚弱:/他以紫色而冰凉的洞穴雕刻眼睛/指示焦虑之滴的坠落/他对幸福的惊惧那白色而无边的手/他对生的严酷他对死的温柔/伴随无辜的永恒萌生的地平线/他以火焰之舌编成的渴望/漫不经心地在水中描画的永恒之林/而云偷偷垂落大理石的脑袋/剥落成一副措手不及的痛苦之鬼脸——/哦认出宇宙如何崩裂的一刻/窒息的黑哦迷失的春而只有/他的头盔如此平静如此耀眼地盲目
第28首有这样的讲述:
射击一个敌人以及卷一支烟/闪耀和熄灭如暴风雨中的灯塔/坐于利益之网如一只苍蝇/以为天生不幸却只是得以出生/是一切不起作用的作用/是别的什么或什么也不是/如灰石砌入仇恨之墙/可还是如帚石楠的喜悦感受石头的理解/感觉在烟雨中的所有忽视/享受燃烧的篝火的刺激/怀疑这定然是最后一回/认可一切只要它不重复/猛烈推进直至一处远景/那里闪电追猎为了替人类复仇
诗中值得玩味的细节颇多。人类经验的片段一一闪过,似有隐约可见的意义,对立的意义和图像相撞,矛盾成为林德格伦展示现代生活中诸多矛盾的方式。诗歌未停留于个人层面,而是推出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化身,这个人,在灾难与希望,在有路和无路间。
现代诗集《无路之人》论形式,敢于突破传统惯例;论内容,密布交错的隐喻和超现实元素。难怪埃凯洛夫称之为“诗人的诗”,他肯定诗集完全的音乐性,肯定它对传统的更新和延伸。他说道,当人们觉得现代诗不可理解性时,多指诗中梦一般的语言、不受控制的思绪。一首诗本质上的音乐性是诗歌本身,正如一段音乐毫无意义也仍可具有深刻意义,一首诗毋需完全得到理解也可具有深刻意义,这正是音乐性诗歌的出发点,而林德格伦的诗是其中的代表。埃凯洛夫肯定《无人之路》的哲学内容,认为它们表达了像生活本身一样变化又矛盾的情绪,时而压抑和逃避,时而狂热而反抗。虽然从诗句里,超现实主义圣手埃凯洛夫甚至看到了自己的诗对林德格伦的影响,可他还是觉得,与其说林德格伦着力于超现实主义书写,不如说是在创造个人的语言,这一尝试有时难免压抑,以至文本像一长排大小相同的窗户。
《无路之人》将沉思的象征主义、扩张的表现主义汇于一炉。炸裂的新十四行诗吸取了古典的十四行形式,抛开押韵、韵脚上的拘束,尤其是抛开了古典十四行诗所要求的形式和内容的一致性,内容失去了可预测的轨迹,情绪和主题发生着出乎意料的多重变化。各诗节构成句法单元,手稿显示,它们像积木一样有不同的搭建可能,而诗人对诗节摆放的位置颇多犹豫,位置变化让诗歌在不同版本中呈现出不同含义。编织思想、图像、感觉和声音,形式的规律性与内容的超现实主义的矛盾统一。
与同时代北欧诗歌相比,《无路之人》用典不多。与其说用典,不如说是走近《圣经》和神话,走近但丁和莎士比亚,让现代和古代平行对话。不为故作深沉,而为了将当下的转为历史的,以远古反观现代存在。这些诗在当代层面表达战争年代的集体无力感;在个人存在层面涉及生与死、爱与恨、有为与无能。正如诗中有“我”、“你”和“我们”,无路之人不只你或我,更是普遍意义上的现代人在20世纪40年代废墟化的世界里探索生存之路。在这个意义上,《无路之人》不是诗合集,而是四十首小诗连缀而成的一首长诗。诗人说过:“这些诗不过是对某些人的困境的证明,对残酷的外部事件压力下形成的现代意识悲剧的贡献。形式完全取决于未经调解的矛盾的多样性,这已成为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无路之人》摒弃小我的抒情,深思熟虑的诗句不能给出思考结果或找到道路,却提供了体验和发现宇宙和内心的过程本身。
哈姆雷特的沉思
第三部诗集《组曲》里有九组共37首诗。开篇题为《哈姆雷特的升天》:
当生命的书写与死亡的梦想合而为一
一切都披上预感之时的背叛,
于是他从心鞘上拔出刀刃
让它啜饮百合的热露
并看到人类在真实里如世界
而世界如人类在真实里,
可与这确定相对的真实是什么
那站在不确定的海中掌舵的真实?
……
第三只眼唱出灵魂的平衡动作
冻结如北国天空下的种子,
而钉出欢乐主题的大键琴
消失于夜的差异的晦暗。
……
而后他看到房子漂浮在宇宙,
露台在黑暗之隙炫目
……
《哈姆雷特的升天》让人类历史中的风景不断扫过。梦和预感都是意识。刀刃从心鞘拔出意味着哈姆雷特的意识对母亲和奥菲莉亚的威胁。纯真的奥菲莉亚如颤动着露珠的百合。人类意识因苦痛而苏醒,也因苏醒而格外苦痛。在寒冷的北欧,哈姆雷特早已癫狂并死去,却又始终活在人类舞台上。这舞台不只是戏剧的,也是现实的,哈姆雷特是世间痛苦、癫狂又高贵的灵魂寄托。意识能暴露生活的残酷。看见真实的人和世界,哈姆雷特的沉思背后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说。然而,不确定性的海洋中的真实到底有没有,究竟是什么?人类的第三只眼到底哪里,是否已冻结?晚年在伯利恒苦修的圣经学者耶罗尼米斯于410年罗马沦陷时悲叹过世界的毁灭,而哈姆雷特的嘴缝着。一首诗写着哈姆雷特和人类意识的命运。
爱的“咏叙调”
总写些含义晦涩现代诗的林德格伦竟也是一首流行诗歌作者,多数人把它读作最好的情诗。因为诗的开头写道:“在我们内部的某处,我们总在一起,/在我们内部的某处,我们的爱永不逃离/某一处/哦,某一处/所有的火车驶离,所有的时钟停下:/在我们内部的某处,我们总在此地和此刻”。这是“你”和“我”完全融合的爱的奇迹,爱超越了时钟的走动和火车的行止。这里有火热的心。
然而很快,诗中显现出惊悚的景观,出现了由学者、怀疑者和我们内在的白骨组成的干渴的沙漠景观,继而再转回爱情场景,日常的男欢女爱有了抽象的宇宙背景:
在我们内部的某一处
那里骨头已白、海市蜃楼相遇
激起远方的安全如波涛的汹涌
你映出我们的遥远像浪潮里的星
我映出我们的接近如浪潮里的星
梦总是摘下面具并且变成你
于痛苦中从我身边溜走
为了再次返回
为了再回我身边
越来越多、在我们内部,越来越多的你。
沙漠景观和瑞典诗人维克托·里德伯格的《康塔塔》有承继关系。里德伯格的《康塔塔》和林德格伦这首收入《组曲》的《咏叙调》皆以音乐术语为题,都提到了沙漠、海市蜃楼。里德伯格在《康塔塔》中借用摩西书中以色列人穿过沙漠来暗示19世纪后半期西方人的文化处境,但不同于宗教对以色列人的引领,里德伯格以为科学和哲学能引人走向正确。林德格伦是无神论者,不认同基督教,世界大战的现实也让他无法接受里德伯格的观点。骨头已变白,理想在战争中破产,爱情或为仅有的慰藉。林德格伦未将感情局限于私人领域,而是推出了宇宙。有理智的人恐怕都会觉得这缺乏实现的可能,然而诗不仅仅着眼理性和现实。《咏叙调》认定了爱的奇迹发生并永远保存之处,升华人类那可以很美好的梦想。而在另一首诗《宇宙之母》中,林德格伦写道,“在我心里/你冬街的气息/在我心里/你已是/一直是梦,一个梦,/超越梦想的山脉,/超越现实、比现实更真实,/某个我不能忘也不能记起的……它就在我体内”。与其说《咏叙调》和《宇宙之母》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联,不如说林德格伦重复表达着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期待靠近一个就在体内、就在宇宙,曾经分离却总在一起,可感知却难以触摸的“你”,那里寄托安宁的希望。这个“你”是永恒的爱人也好,是宇宙之母也罢,都不重要,都可能是一码事。林德格伦的诗为音乐,也为阐述,表达严肃的思考,绝无软弱的感伤,甚而因过于严肃,缺少更贴近生活层面的自发的书写。
结 语
如果说《无路之人》呈现了哲学思考,《组曲》则更体现美学观。林德格伦很少让纯粹的私人抒情占据主导地位,而是让多种声音、印象、回忆及世界文学的回声交响成曲,除了莎士比亚,也不难发现瑞典诗人的影响。除了诗歌,《组曲》里也有散文诗。
“太阳在处女的生命里行走/这里什么都不会迷失/血月天眼/这里什么都未迷失/夜成了心草上的星/晨与夜是同一扇门/无事需做,而一切已完成/唯整个世界迷失了”。在题为《春分》的这首短诗里,处女和太阳暗示万物孕育与生命的无限可能。“血月”提醒人生活的艰难和疯狂。“心草上的星”像爱的幻觉。晨与夜有同一扇门,一切在此比肩来又去。大梦里的癫狂是一代代人类的亲历。诗人身处20世纪40年代战争烟云下,这感触怕是尤为痛彻。也许正是这份痛彻使得他一次次将日常移到洪荒之地,把当下拉至无始无终。
值得一提的是,林德格伦还是杰出的文学翻译家。20世纪30年代,他翻译艾略特作品,40年代他诠释了里尔克和保尔艾吕雅等人的诗歌,对北欧诗人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也翻译格雷厄姆·格林等人的小说和戏剧,1944年对威廉·福克纳《八月之光》的解读脍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