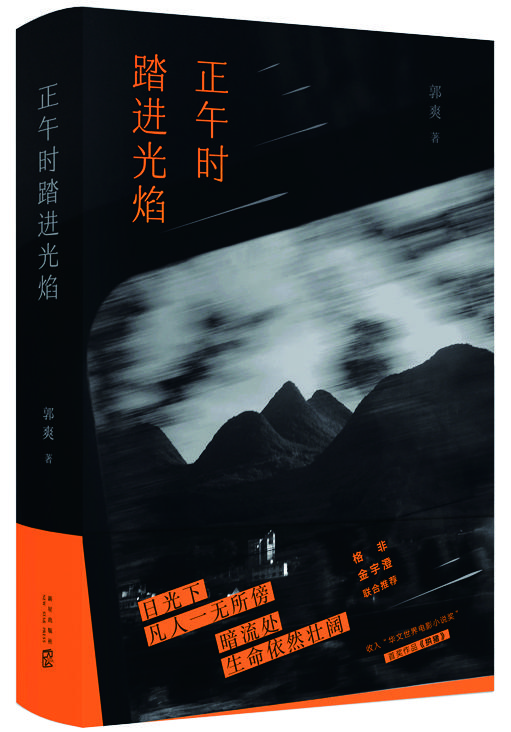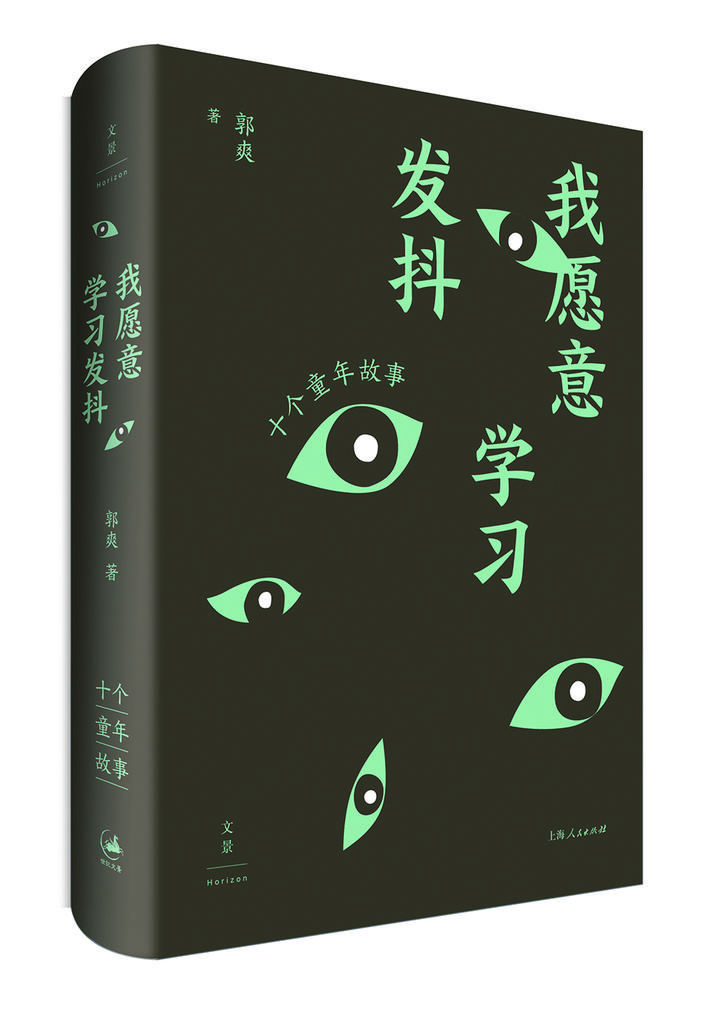作者是时空的旅人,一次次重返、创造新的讲述
郭 爽:最近这半年,我常常想起2015年7月在欧洲时的情形。那是我第二次去德国,但跟第一次很不同,那次我到的当天,第一批叙利亚难民抵达慕尼黑中央车站。德国人甚至是在庆祝难民的“抵达”。后来,比如现在,我们都知道,世界跟那时候不一样了,不只是欧洲,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而那个时间点是个拐点。对我来说,从比较小的时候开始,心里有个“老欧洲”的感受,后来也去感受过,甚至深入过,遇到、留下几个朋友。当然这个“老”对每一辈作家或者每一个人来说意味都是不同的,但我心里有这么个东西。所以当变化发生,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心里会问:就这样吗?真是就这样发生了吗?脑子里有个小声音在喊:我还没准备好,或者,这不是我期待的。但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觉得对于生活,对于很多事,我都有种后知后觉,可能这也是我写小说的原因,我喜欢环形而非线性的时间,这样我就可以一次次重新进入,去看得更清楚,去让一些变得太快的东西被定格后慢慢雕塑,我也才能看清自己。
我想问问你,2015年,你去了哪里?有什么记忆?我的这种站在历史的分界点上、回望时知道是一个刻度而且将不复重来的感受,你有类似的体验吗?
刘子超:2015年是我有工作的最后一年,去了不少地方。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个。一个是土耳其,我去了东部的卡尔斯,挨着亚美尼亚边境,也是帕慕克《雪》的发生地。另一个是秘鲁,采访一个国际美食节,因为吃得太好了,至今念念不忘。现在回看,你说的历史分界点的感觉,我也感到了,只是当时不知道而已。2016年,我在英国,正好赶上英国脱欧公投,那应该是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的先兆。我们都是受惠于全球化的一代,有机会在年轻时去世界各地走走,但细想起来,像我们这样比较幸运的一代,在中国近代史上并非主流。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会怀念那个“刻度”之前的世界,觉得好日子还没过够。我们的写作也都有基于世界经验的部分。
我想问你的是,如果这部分经验以后越来越难汲取,对你的写作会有哪些影响?你会做出策略的调整吗?
郭 爽:我是在写《换日线》这个小说的时候,很明确地感受到你说的这些,或者说起心动念写那个小说,就是感知到了非常明确的信号,想要自己在很多感觉还没消失前,把那种经验和经验里蕴含的还不能完全说清楚的东西写下来。那个小说的故事时间跨度有十几年,对应的现实时间涵盖了我们从高中到30岁这个时间段,也就是1990年代末到2015年之前。从小说标题这个意象就在提示,两位女主角在不同时区、不同国家间穿梭,这不仅是物理的移动带来的经验和际遇,更是一种精神景观或者说气象。
这个小说出来后,激起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比我们年长一些的人,比如我们父母辈的人,或者比我们年长十来岁的人看了后,都对这种几乎是随意游动的生活和所形成的精神世界吃了一惊。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每个人都说对其中透出的自由、无所顾忌、卸下道德伦理负担后的精神状态为之感动,甚至振奋。这是我没想过的。对我来说,这个小说的精神内核,像呼吸一样自然,是我日常所思所想所感的局部,不过用讲故事、虚构的方法将它写出来。但慢慢我意识到,这种我觉得的平常,其实不平常。像你说的,这种世界经验并非主流,甚至从近代史开始也并非主流。但写作这回事,我想不平常比平常好,好得多。人人可写的不必写,人人能写的也不必再写。
现在我更多会从事实层面来看待这些经验。比如说,我们是独生子女。可以从社会学、历史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它具有普遍性,但回到写作上,对作者个体来说,这是一种中性的事实。鲜活的经验、记忆、情感,这些都非常个人,也只有从个人的角度出去,从内部出去,写作才能成立。已有的经验慢慢结成体内的矿藏,随着生命体验的累积、知识结构的变化,看待这些经验有不同的视角,这对我来说是始终新鲜的。作者是时空的旅人,一次次重返、创造新的讲述。
还需要补充一点,这种“世界经验”的形成,我想阅读、观看、想象是真正的发端,早于踏出国门。不过这种早期累积的文化经验与后来的个人经验叠加,迸发出了复杂、有生命深度的内涵。
以上可能是好的、可见的方面,另一方面,2019年3月去日本九州之后,我就没有再出过国,那个以日本九州为题材的写作计划只能搁置。中间我几度试图捡起来,还去了国内一些别的地方,找材料、找对照,但都没办法,就是不够,必须还得去九州才能写完,现在的状态就是写不完。我还想去希腊,也是去不了的。这个我暂时没法解决,只能等待。
一年多前,我看到你说要去西藏待一年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是西藏?然后又想:除了西藏,还能去哪儿呢?哈哈,我能理解。但还是想听你说说。
刘子超:《换日线》和《挪威槭》我以前就有印象,最近重看了一下,觉得里面的经验有很强的辨识度,是你才会写的。所以,还是很期待你沿着这条路写下去,完成九州这篇。
我去西藏纯粹是因为不喜欢长时间待在北京,而且已经习惯了移动的、游牧的生活。在西藏一年,把下面的县几乎都走了,包括很少有人去的地方,也认识了很多人。但我觉得,如果早10年去一定更有意思。现在有时会感到,那些大山大河背后已经是空的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待在北京一年又能怎样?
完全靠写作为生的这些年,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了一套与写作相适应的生活方式
郭 爽:你觉得你这种游牧式的生活只是习惯吗,还是其实有别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支撑你?
刘子超:游牧式的生活,我觉得与之相对的是,不能自由移动的生活、被拴住的生活、被饲养的生活,这都太给人囚禁感了。我还是更喜欢做一只野生动物。以前不知道这一点,是辞职以后(虽然当时是迫于无奈)才慢慢发现的。我突然想到,我们的职业经历大体相似。你辞职后这些年是怎么过的?有觉得过得更好吗?
郭 爽:在辞职之前,有三四年的时间,我已经不太舒服了,在找各种可能的路向。差点去香港工作,考虑转行,也开始认真写作。我跟你不同,写作开始得晚,在辞职之前,也没真的想过以后就靠写作为生。不知不觉就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然后就闭着眼选了一条走下去。现在回看,从大学毕业到辞职前那十年的职业生涯,像是平行时空里的另一个自己。我觉得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时间特别艰难,如果可以,我很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过了三十岁,什么都会好的,请坚持一下。但这个“好”怎么说,不是那时候的我可以预料到的。我现在过的生活可以说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并不期待“更好”,只是看到了自己该做的事、该走的路,然后一天一天去完成。
上了那么多年班后,现在可以说,我不适合上班,这一点也是后知后觉。虽然会尽心尽力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对他人负责,但那不是完全的我。可能那样做的结果之一,是让我在物质和生活层面相对平稳,也就是说可以经济独立、精神独立,能跟父母建立一种成年后的关系。这个对我比较重要。我很爱他们,我们之间有很多精神交流,但这一点对我来说也是束缚。要独立,在陌生城市建立自己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无论如何我度过了。跟父母的关系在经历了反复的冲突、紧张、理解后,现在因为生死之隔,一切已归于平静。
从更实在的方面说,辞职后,我的身体好了很多,天天给自己做吃的,偏头痛也没有了。我喜欢植物,在广州的时候养了不少植物,到上海后老搬家,没法养,但住的附近植物很多,每天出去走走看看也很开心。我突然想起,上一次见到你,你带着笔记本随身在记,在写作上你是个自律的人吧?还蛮好奇你的写作准备阶段和实际写作阶段所占的比例的,还有你的写作习惯。另外,你真的不写小说吗?不信。
刘子超:和你一样,我也是工作后先做了10年记者。那段日子既有极端孤独、穷困的时候,也有些有意思的回忆。我做过一段时间社会新闻记者,去小县城调查过一些案子,但我还没有以那些为题材写过任何小说,主要是觉得沉淀得还不够。我后来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非虚构旅行写作也有这方面考虑——写小说是消耗性的,而旅行写作是积累性的。我想等到自己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去重新尝试小说。我以前写过小说,大概是从16岁到24岁这段时间,在《今天》杂志上发表过,后来停下来是因为意识到刚才说的问题。
看你的描述,我们辞职后的生活应该差不多:写作、阅读、做饭……我甚至觉得不会做饭的作家当不了好作家,因为做饭的创意、搭配、调味、火候跟写作太相似了,做饭的过程中我会经常想想写作的事,往往会有一些顿悟。
辞职,未进入体制,完全靠写作为生的这些年,我觉得自己最重要的写作习惯是建立起了一套与写作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从对待物质的态度、吃饭、锻炼身体到处理人际关系等等,都必须尽可能与写作这个主轴相协调。有些物质欲望必须断舍,有些积习必须放弃,慢慢习惯之后,就觉得写作是可持续的,无论书卖得如何,都不会影响这样的生活方式。
你现在住在上海,以后有什么打算?觉得哪里生活更适合写作?
另一种语言和它连带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很早就让我的世界有了爱丽丝的兔子洞
郭 爽:我一直对学语言有热情。从小学时候学英语开始就发现了,好像也没什么目的,就单纯地用另一个系统来调动思维、身体就可以让我高兴。开始学英语是一个暑假,我爸爸有个同学是师范大学英语系的老师,她办的暑期班(后来成了日常班,我在那里上了三四年的课)。课本是《玛泽的故事》,我学会第一个我喜欢的英文句子,“我是玛泽,我大。”玛泽是个绿色的、毛茸茸的外星人。我喜欢他用这个简洁的词语和发音来介绍自己。从那时候开始,我花很多时间学英文,从看绿色封皮的书虫双语世界名著系列开始。很多年后我意识到,另一种语言和它连带的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很早就让我的世界有了爱丽丝的兔子洞。我走到哪里,都背着我的蜗牛壳,壳里面装着许多东西,它们就是我的家。意识到这个蜗牛壳的存在,有一个过程,而一旦意识到它的存在和恒定光源一样的供给感,那种孤独感开始平衡,不再晃荡,也就可以四海为家了。
我朋友最多的城市是广州,所以目前广州对我来说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以后还不知道。我常常想学一种新的语言,然后去新的语言环境生活个几年,可能日常方面会艰难,但就算在听得懂每个字的生活环境里,人每天也处在误解和不被理解中吧。
说到做饭,日常的魔法真的很简单。对普鲁斯特起作用的魔法是玛德琳小蛋糕,对我来说做碗糯米饭,或者一个碱水面包圈就可以切换频道。长期写作对身体有很多需求,除了从食物上照顾好自己,我也很注意呼吸法、拉伸,每天散步。散步对我来说是最佳的灵感时刻。
你学过哪些语言?我知道有俄语,还有其他吗?我特别喜欢听别人说他们学语言的事。你住在广州的时候,有没有学粤语?
最后一个小问题关于库切。我留意到你读了不少库切的书(可能只是我片面的印象),你是对一个作家感兴趣就会把他的书都读完吗?库切书里面什么吸引你?也可以说说你喜欢的别的作家。
刘子超:你提到的那套绿色封皮的牛津书虫双语世界名著,我也几乎都看过。记得初高中有一段时间,每天捧着那套书中的一本看,打发了很多荷尔蒙无处发泄的时光(而且因为是英文的,所以不会被认为是看闲书)。还有一套书类似,是针对美国高中生的名著简写本,我在里面读到了《漫长的告别》。当时互联网尚未普及,国内的美国文学史上也找不到任何介绍。所以直到2006年,我才终于了解作者的生平。辞职写作后,我也做些翻译,前两年翻译了钱德勒的三本书。看你的信突然意识到,从小学英语还是给现在当职业作家提供了一些保障。虽然翻译收入不高,但对进账不稳的写作生活来说,多少还有些补贴作用。
我报班正经学过一阵子法语、俄语和朝鲜语。为了旅行,自学过乌兹别克语和土耳其语,仅此而已了。我认识不少语言天赋极高的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法国老头儿,我们是在土耳其东部旅行时认识的。他会说汉语、英语、西班牙语、德语、土耳其语,“文革”时在东北当过外国专家。他爷爷是维吾尔族,很早去了马赛,娶了法国女人。他旅行时带着一本厚厚的土耳其字典,走在路上就随时翻阅。后来,他说他想编一本英语-维吾尔语大辞典,我从国内帮他寄过一些资料。不知道这本书编出来没有。我在广州没学粤语,主要是因为普通话已经太普及。不过,有些粤语表达挺好玩的,比如“生嚿叉烧好过生你”之类的,很享受用在广东朋友身上的感觉。
如果我喜欢一个作家的风格,而不仅仅是某一本书,我就会通读他的作品。我觉得写出风格比写出一本好书更难,也更值得花时间学习。我喜欢库切裹着硬壳的激情,喜欢奈保尔精辟的刻薄,他俩的部分风格都来自约瑟夫·康拉德,所以我也喜欢康拉德。这几年我还通读过米歇尔·维勒贝克,他的《血清素》快出中文版了。两年前看英文版时,喜欢上了里面提到的诺曼底苹果烧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