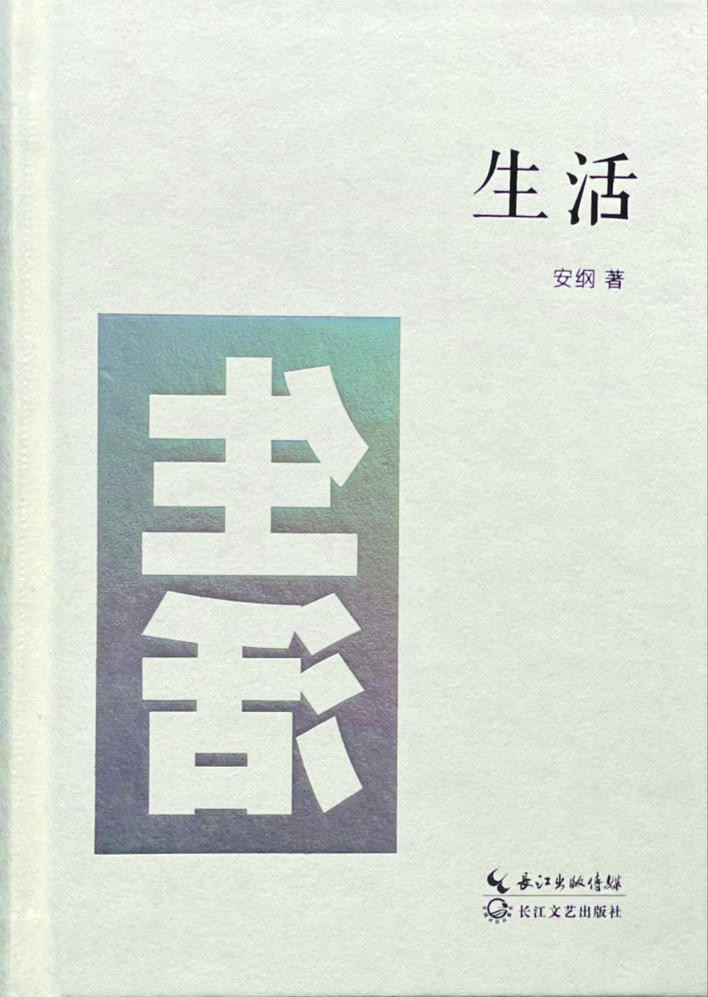安纲给我们的批评提供了难度。他的《生活》是新的,它或多或少会“冲破”我们习惯上的关于长篇小说或者长篇小说建构上的理解,也或多或少会“冲破”我们习惯上对于生活的,尤其是具有日常性的那类生活的理解。在这部小说中,我首先读出的是“溢出”,是与旧有的某些分野和不像。我赞赏这一勇气,尤其是在我们的审美和习见越来越坚固和保守、越来越有些“叶公好龙”的时候。安纲的提供是新质的,它在文本的实践中提供了“摇晃”和对抗,当然这并不意味它匮乏坚固的东西。
他的“碎片”结构让我想起唐纳德·巴塞尔姆或赫塔·米勒,而其中建立在现实基点上的突然跃出则让我想到《聊斋》和加·加西亚·马尔克斯。我并不是为了《生活》寻找什么先驱,而是感觉他们之间确有某种珍贵的“互有”,而这种“互有”保证了小说的可理解和魅力感。
《生活》有意思地标注为“长篇小说”。在阅读过程中我几次想更改掉这个标注,然后又放弃。在我看来,安纲在《生活》一书中提供的是一片一片“有意味的拼图”,每一片都具有独立性,但通读下来我们才能更清晰地意识到它的“整体性”,和这些拼图缓慢搭建而成的宽宏与重量。小说中每一片的独立都足够耐人寻味,似乎贮含着可以察觉的生长性和回声感,而等我们在阅读完整部小说的全部提供、上升到“整体俯瞰”的时候,便可发现安纲建筑起的整体丛林和建筑物的连绵,以及有效的统一。从这个意味上讲,他标注为“长篇小说”是有道理的,它也的确具备“长篇小说”本应有的整体性,尽管这种整体性是散布于每一“有意味的拼图”中的。《生活》又是一个极有意味和具有游戏感的标明,安纲提供给我们的不是(至少不只是)生活的熟稔和普遍的日常感受,而是基于熟稔而产生的想象、幻觉、梦魇和梦境,在这里想象力是它的另外支撑,甚至可以说是更为主体和重要的支撑。狡黠的安纲似乎有意指鹿为马,他故意笃定而不那么讲理地确定“这就是生活”,故意让我们在“是吗?不是吗?”之间左右为难。无论是标注长篇小说还是将小说命名为《生活》,应当都是安纲的有意为之,他试图在我们已经习惯的惯常和普遍接受的“命名”“概念”的基础上再向前一步,让我们重新审视。
写作长篇,最大的难度在于叙事张弛中过渡段落的魅力处理,许多经典名篇往往也会有“叙事疲惫”的地方,可以快速翻过的、显得冗余的地方,而安纲的“碎片拼贴”方式恰好可以绕过这种不足,他让自己所有的“叙事碎片”都保持着极佳的“魅力强度”,那些短小的篇幅始终有吸引,有抓人处和耐人寻味。它让你可以从随便的任何一个小节入手,然后读得津津有味。这是极具难度的。而在语言上,安纲却没有特别用力,他甚至有意淡化了语言的色彩感和锐利度,使用的常常是只有“黑白两色”。有意味的短制,往往会在语言上特别用力,然而在这里安纲又一次反其道而行,我想他是经历过取舍的,是想让我们更把注意力放在故事和想象的方向上的,他相信这一方向足够有吸引、有魅力。
安纲通过他“有意味的形式”凸显的是他在生活中的思考、怀疑、审视,他取的并不是生活的已有发生,而是已有发生中的贮含部分,是这种贮含的再造和追问,是透过另一种“想象的镜像”再度的逼近,颇有些哲学意味。譬如最早的那篇《妻子》,“我有两个妻子,一个高,一个矮。她们长得一模一样,穿的衣服也一样”,等等。就在我们以为它旨在提示我们“二十四种人格”的不同面影的时候,以为它会用故事的方式“证明”一种心理学议题的时候,却发现它开始变化,更为陌生,更有了含义不明的隐喻意味,譬如红色塑料桶里的鱼,“既像她,又像她”。它妙在回味,那些被捕到的困囿于水桶中的鱼与“两个妻子”的相似让人联想。更妙的是,安纲竟然至此仍不肯止歇,他还要继续再上一楼,让一个“妻子”在幻觉中继续变化,“像个溺水者一样”,而抓着她的衣服提起来的时候“她好像是空的”,等等。具有高潮感和强烈冲击的是最后一句,“我身后还站着另一个她,她看都没看她一下”。如果阐释,或者过度阐释,我们或可认为这里包含了这样的隐喻:隐喻一个人的自我分裂感,它甚至取消了某些共通性;隐喻一种彻底的麻木,“两个妻子”中的一个已蜕变成为“连自己都不爱都不在意”的人;隐喻“我”的所做在“另一个妻子”那里同样是视而不见的,一种熟悉之后的陌生,等等。安纲文字的妙就妙在你的所有隐喻性猜度都可能是他的想说,是他想说的一部分,可是每种注入都是片面的,是难以完全概括清的,更可能是“错误”的。
有一节,安纲的小标题是《我》,但通篇下来写的是在玻璃上爬行的蜜蜂,它本应叫《蜜蜂》才对,然而安纲非要将它命名为《我》。这颇让我感慨,甚至感觉胸口受到了重重一击。关于我,关于我的写作,甚至是更为阔大的我们,有时何尝不是这只“束手无策”的蜜蜂呢?感谢安纲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