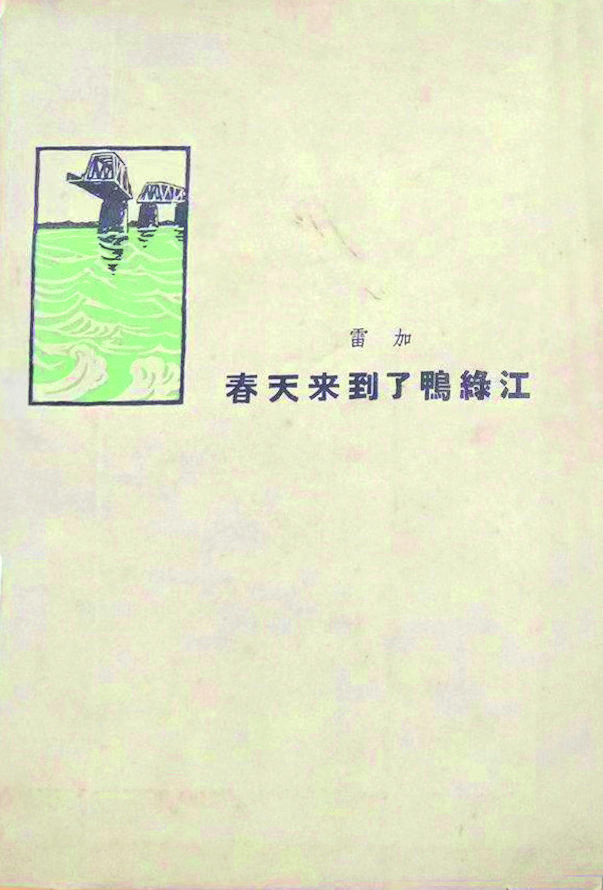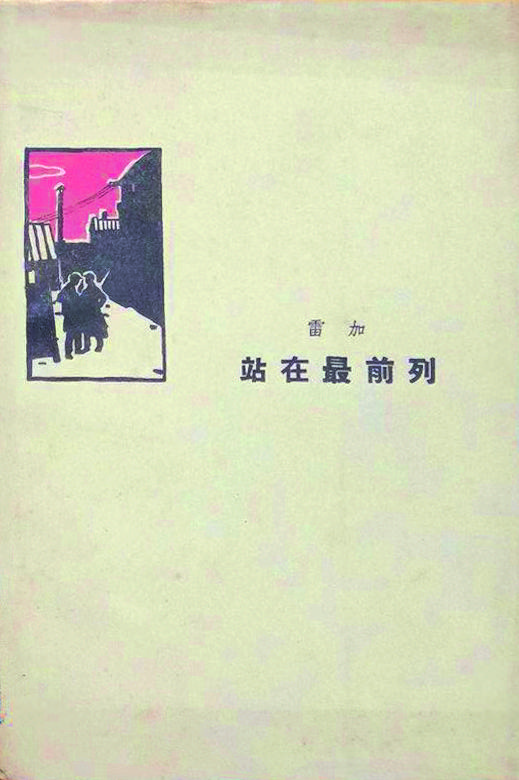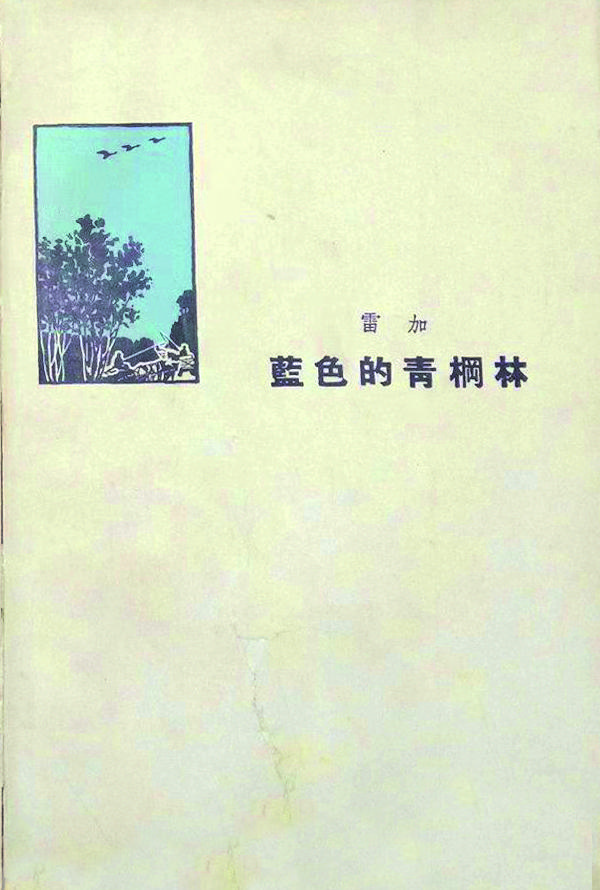《潜力》三部曲
遇见雷加
我遇见大作家雷加纯属偶然。
2008年5月,父亲因得胰腺癌需要化疗住进了同仁医院,那些日子,来看望父亲的亲戚、朋友、同事络绎不绝。
一天,我守着父亲正吃晚饭,突然看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影,头几乎是蹭着门框的上沿儿进来的。他穿着蓝格子病号服,一双手用力扶着凳子似的东西,一小碎步、一小碎步地走向父亲床前,旁边还跟着一个搀扶的小姑娘。我从未见过此人,倒是父亲见了,惊诧地“哎哟哟”连叫几声,就把已是虚弱得不行的身体从床上抽起。那人急忙拦住,嘴里说道:“您别动,我就是串个门随便来看看。”我这才看清,那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方颌大脸,鼻挺嘴阔,一双大眼炯炯有神,虽然脸上布满老人斑,但说出话来如洪钟大吕,声音响亮,底气十足,让人不能不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雷老,没想到您还亲自来看我。”父亲打过招呼后,转身向我介绍,“这就是我给你讲过的雷加,雷老,原来我们一起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
雷加!我听到这个名字一下子就呆住了。就在下午,父亲还问我认不认识雷加,我说当然认识,他是我非常崇拜的作家,在一些很有分量的文学刊物上经常能看到他的大名。父亲神秘地告诉我,说雷加也住进了这家医院,就在隔壁病房。我当时听完,既激动又深感意外,还想着什么时候去他的病房转转,哪怕只是在门口看一眼,没想到这位名满天下的大作家,如今竟然就站在面前。
“我这也是第一次串门,我是看到住院名单上有‘戴其锷’三个字,觉得眼熟就过来看看。”雷老说完就缓缓坐在父亲床边的椅子上。
“我爷爷平时很注意保养,身体一直很好,这次发现他膀胱里长了个东西,才来医院住的,准备明天去做检查。”陪同他的女孩说。看样子,她应该是雷加的小孙女。
聊了一会儿,我发现雷加尽管看着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但可能是进入垂暮之年,以前的事已记不大清楚。因此这次来访,基本都是雷加不停在问,我父亲不停在解释:他们过去一起在哪里工作,当时很有名气的作家都有谁。只是解释了半天,收效不大,父亲说话时,雷加的眼神始终是游离的,愣愣地看着前方,明显那些往事他已记不起。
几天后父亲出院,我陪他又回访雷老,父亲给他带来一个好消息,说自己已从护士那里打听到,雷加身上长的肿瘤是良性的,让他放心。那时,雷加一面睁着一双有些疲惫的眼睛,慢慢打量我们;一面告诉父亲他已获知此事,第二天也准备出院。父亲生怕打扰他休息,没坐一会儿就离开了病房。
那一次,是两人事隔多年后的再一次相见,也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要让作家觉得作协是个家”
时间回溯到四十多年前,那是1962年9月,父亲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文研班毕业,被调至市文联创研部;而雷加那时已是成绩斐然、写出过长篇小说《潜力》三部曲的老作家,他也刚离开轻工业部,成为北京文联一名专职作家。从那时起,两人就有了交集,只不过父亲还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毛头小伙,而雷加已近五十,是文学和社会经验都很丰富的中年人了,故而父亲一直以“雷老”尊称他。1963年2月,北京作家协会筹委会成立,雷加担任作协副主席,父亲也成了筹委会一名干事,因此每次开会,父亲都能亲耳听到雷加那如洪钟大吕般的声音。
北京作协筹委会的成立,极大激发出作家和喜爱文学的在职干部、编辑的热情。那一段时间,身为筹委会副主席兼作家组组长的雷加,尤其为作协的建设操碎了心。比如,面对《北京文艺》杂志当时刊发本地作家作品较少的情况,他直截了当给出意见:“《北京文艺》与作协的关系应很密切,份数应增加,然后才能加强团结作家。”在筹委会成立后的第一次理事会上,雷加又再次强调:“《北京文艺》要加强紧密联系,配合得好。杂志和作家不只有工作行政关系,而且有感性关系。”
3月14日,在筹委会办公室单独召开的会上,雷加更是针对作协即将开展的工作,向江风提出几条具体建议:
一是对业余、专业水平作者,要搞几个名单、参观访问的具体计划。二是7月份的会,具体时间地点,应办得像个样……三是事务工作要管起来,如买学习文件、票的问题等,要明确。要让作家觉得作协是个家……四是现在是小搞,还应当有个远景规划……
雷加说的7月份的会,是指作协为培养业余作者而召开的北京职工业余文学作者学习座谈会。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雷加身为作协副主席,时时在考虑作协的长远发展,真心想为北京文学事业的繁荣贡献出自己一份力。也就是在那次理事会上,雷加还针对作协如何更好地组织作家活动,提出“可以两种方式,具体的时间先要定下来。较多的,一般参观访问。较少的,写报告文学”。他还说这些事可以“和全国作协合起来做”,更特意提到韦君宜的名字。韦君宜不仅是当时的一位知名女作家,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经她之手推出过许多得过全国大奖的优秀作品。雷加提到她,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想让作协跟出版社强强联手,以便给北京作家们谋一个更好的未来。
正因为雷加不光有组织才能,还时刻想着为他人谋福利,到了1980年,北京作家协会正式成立时,他再次被大家一致推举为北京作协副主席。
紧紧抓住时代脉搏
雷加虽然在文坛上一直被委以重任,要操心的事很多,但并不妨碍他在文学上结出丰硕果实。在漫长的七十多年创作生涯中,他写出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传记、特写等上千万字的作品,可以说是我国当代最多产的作家之一。追溯这一切的缘由,非常勤奋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雷加十分热爱生活、关注社会,始终牢牢扎根在人民群众中间,因而,他才能紧紧抓住时代脉搏,用手里这支笔,写出一篇又一篇能够反映时代的优秀作品。
抗战时,雷加就写过不少抗日题材的作品,其中以他写的报告文学《国际友人白求恩》影响最大。新中国成立,雷加更是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引用雷加原话,他从1956年开始,“在三门峡待了两三年,后在轻工业部工作了两年”,直到1962年才调到北京市文联。回忆那段经历时,他是这样说的,“在三门峡挂了个名,有好处,既避免开会”,也可以“了解工人思想情况,积累材料。到轻工业部就完全担任工作,当时想一年可以下去四个月,晚上可以写写,后来不行,八小时工作完后回来就想休息了。只是从三门峡到轻工业部三个假期间,写了五六万字”。可正是这些文字,成就了他后来出版的两本散文特写集《工地早晨》《三门峡截流记》。1960年,他又跟随中国科考队到全国各地考察,把自己看到的写成一系列优美散文,结集成书后取名《山水诗话》(后改为《从冰斗到大川》)。
深入生活是他的根,也是他从中不断获取文学素材的源泉。过去是这样,成为作协筹委会副主席后,这一目标非但没变,他的灵感和热情反而层出不穷,愈加一发不可收拾。
他想过,就自己生活过的三门峡写一个中篇。他还想利用延安土地革命的材料,写一个中篇小说,“准备五月下去,十月回来写”。另外,面对当时天津港轰轰烈烈的建设,他又“想在开南北运河时附近安个点,先去天津港写写,另外在北京工厂或学校安个点经常联系。个人跑收获小,最好跟着人家组织跑,如勘察队等”。跟随中国科考队取得的满满收获,让雷加找到了生活和创作两不误的方法,他要重新出发,紧跟上那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因此那几年,经常可以看到雷加拿着一支笔、一个本在基层到处跑,有时是在大雪纷飞的北国,有时是在烈日炎炎的南疆,深入挖掘,从不懈怠。可惜的是,接踵而来的“文革”十年,使得雷加生活受挫,文笔沉寂,等到创作再一次如火山爆发,已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了。
雷加是在“文革”初期就离开作协,去“牛棚”劳动改造的;我父亲则是于1969年被下放至房山霞云岭公社,就此,两个人的生活再无交集。直到四十年后,父亲和雷加在同一家医院不期而遇,漫长的岁月加之身体的衰老,雷加已记不清过去的人事,这并不令人意外。想不到的是,我父亲出院不久,就于2009年3月2日去世;而受人尊敬的大作家雷加,雷老,也在八天后的3月10日不幸病故,永远长眠于他出生的鸭绿江畔。